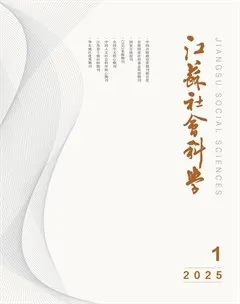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地图及其建构:政治的知识化与政治知识的结构论析
内容提要 中国政治学知识地图的建构依赖一系列前置性思考:何为政治学的“学科”?何为“中国”政治学?何为建制性概念?为何强调建制性概念?比较政治分析的框架怎样?比较政治分析如何建构政治知识地图?政治学是对政治实践与政治经验的知识论证,“现代”政治学是对现代政治经验的知识论证,“中国”政治学是对中国地域经验的政治知识论证,因此,中国政治学有“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的双重结构,政治学史研究应当从“教育史”转向“知识史”及知识的社会政治分析。政治的知识化有三重维度:第一,日常生活的意义与生活知识;第二,作为正当性论述的传播性知识;第三,作为职业分化与理论化表述的学术知识。尽管政治学是一种职业分化与理论化的学术知识,但其根源应当追溯到传播性知识以及日常生活知识,并以建制性概念作为“中国分析”的具体内容。政治知识的结构框架实质上是一种比较政治分析,以“共同体的营造”为框架,可以建构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地图。
关键词 政治学史 知识地图 知识社会学 建制性概念 共同体的营造
王向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19ZDA133)的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政治学的建制性概念及其知识地图》中,笔者梳理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形成的一系列旨在描述与解释中国经验的建制性概念,并将之纳入政治学知识地图中加以理解[1]。中国政治学知识地图的建构依赖一系列前置性思考:何为政治学的“学科”?何为“中国”政治学?何为建制性概念?为何强调建制性概念?比较政治分析的框架怎样?它如何建构政治知识地图?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再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地图及其建构。
随着“何为中国”的建制性概念的涌现,何为“政治概念”、何为“政治学概念”的基础讨论多了起来。这是中国政治学的内容建构走向深入的表现,它意味着研究者正在追问这个领域的根本性概念及其建构问题。大体来说,学界有两种思路:第一,站在理论家或学术化角度,讨论作为一种理论化知识的政治(学)概念的特征,强调它不同于生活话语与政治话语,认为它以职业化、专业化、理论化为特征,将它视为一种既定或理想的社会科学知识形态[1]。第二,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追问政治(学)知识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含义及其在历史中的知识生产或建构过程,在此分析中,并不排斥生活话语与政治话语。这两种思路,从根本上说并不冲突:前者立足于研究者自己的职业身份,强调研究材料及其研究结果的专业性与理论化;后者并不反对研究者的社会科学态度,但是,它将之推进到政治学知识的来源或知识生产的社会政治分析,这种社会政治分析的对象并不必然局限于学术史,还会深入生活史与社会史,尽管分析结果仍然是一种专业化、理论化的知识形态。进一步说,前者偏爱学术概念而本能地拒斥通俗的日常话语尤其是政治话语,后者试图通过回溯政治话语与日常话语而更深入地解释和建构学术概念。假如说,前者的共同体认同功能在于,通过寻找知识生产的分工差异,排斥传统的、非职业性政治研究者,那么,后者则超越了政治学家的身份建构与角色认同,将重心从“(专业)知识”形态转向知识社会学的“社会政治分析”。
政治学知识地图是一种解释性的概念图示,它反映了政治学家或政治研究者对周遭政治现实的认知与理解。政治学概念及其结构性关联(即一种解释或理解)并不能在其后来形态上辩论,而应当回到其生产来源及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结构。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回溯与还原,才能理解作为结果的政治学概念的意涵、知识生产方式及其组织建制方式,亦即我们所谓的学科形态。因此,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通过回溯与还原政治话语以及生活话语,建构更为合适的比较政治分析框架,从而更好地评论甚至重建政治学术概念及其知识地图。
当下的政治学概念或知识命题起自政治学的“学科”论辩,故而本文先论中国政治学史研究的双重进路,然后讨论政治现实的知识化过程及其建制性概念的建构,最后以“共同体的营造”为纲目,建立比较政治分析的框架。本文认为,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说,精致而理论化的政治学概念是政治知识类型上的明珠,而建制性概念是本国政治学的标识性内容。
一、政治学史研究的进路:从教育史、知识史再到知识社会学
政治学史研究,有两种分析进路:教育史和知识史。这两种分析进路在中国政治学史领域的运用与选择,体现在下列三组经验事实的呈现与分析过程中。
政治学史研究先要有政治学的“学科”定义。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此“学科”定义变得越来越模糊,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张力越发凸显。首先,学界常用的学科定义来自美国政治学,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组建政治研究院和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被视为政治学产生的标志,前者意味着现代大学体制中的政治学独立院系设置,后者意味着政治学研究者走向职业共同体的群体认知与社会身份。这是美国职业化社会细分的结果,美国现代政治学的早期创造者是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的“东北部士绅”[2],而专业化的政治学家则是蜗居于政治学系的工资收入者,政治学系是其职岗空间,政治学会则是其身份共同体组织。将政治学史等同于政治学系的历史,就是一种教育史的研究路径,政治学史细化为政治学系的课程、教员、发表出版、共同体组织等教育指数。在此视角下,中国政治学的起点被界定为京师大学堂的政治学门[1](1932年成立的中国政治学会却不太被强调),中共根据地的政治学院和政治学校都被排斥在政治学学科史之外。1952—1979年,政治学系被撤销,中国大学体制的院系调整被视为中国政治学的历史缺位。由此,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就有了数十年的空白以及新中国主流政治研究建制的断档[2]。
其次,虽然晚清民国在大学体制里设置了政治学系,但民国政治学家大多在贩运欧美导师的政治学知识,“中国论述”仅停留在对象层面,“中国”并未成为分析性概念;相反,根据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政治知识却是现代中国的主流政治叙事。根据地的政治教育以及新中国早期的政治课、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研究等教研组织孕育了1979年以来的大学政治学系,马克思主义、党治国家与中国共产党研究等主题和政治知识从根据地延续到新中国,且在21世纪的当下仍然是中国政治学界的主导性概念。故而,从议题结构的知识史角度看,根据地解放区的学校虽然不具有现代大学的规范形式,并不以专业发表为职岗业务,但是其政治教育在教学过程中传播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核心议题及知识论述,训练着作为转型期中国权力中轴的党员干部。虽然1952年院系调整撤销了政治学系,但是普遍开设的政治课完成了政治知识的社会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等领域的研究创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学。中国政治教育的政治学形态固然不同于专业化知识生产的政治学形态,却与本国政治实践紧密相连,正如美国建国政治学一般。因此,政治知识与政治进程的互动是政治学史研究的关键视角。
最后,假如说西方政治学起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不完全是一种现代知识分科的结果,那么,“政治学”一词更多是形式化的语词符号,不涉及具体历史。相应地,传统中国数千年的政治知识论述,不但有独立的建制性概念,例如“道统”“政统”“治统”“大一统”,秦汉郡县官僚制替代了封建贵族制,在后来的朝代中不仅形成了完善而成熟的官制与史观叙事,而且形成了以经学为核心、史子集为配套的知识表达系统以及身体力行的士大夫群体。21世纪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似乎表明在现代化的总方向之下,传统政治遗产和概念得到了极大的延续和挖掘,例如“大一统”概念在众多学科领域的复兴[3],显示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4]。放宽历史的视野,假如作为知识的政治学是指“对政治实践的知识论证”,那么,伊斯兰世界从古希腊开始就与西方并行,甚至一度在地域竞争中处于上风,谓其没有“政治学”便如同视他们仍然处于裸猿期一般,尽显意识形态的知识霸权意味。
在上述三组经验事实面前,我们看到,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存在作为大学院系设置的“高等教育史”和现代国家知识论证的“知识史”两种研究传统。仅以“政治学系”来定义政治学学科过于简化,这样的历史研究属于“高等教育史”而非“知识史”。即使从1979年政治学系恢复后观察,中国政治学的“五路大军”——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部队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党政部门研究机构——也非仅由高校政治学系代表,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和《政治学研究》杂志在中国政治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某种程度上说,知识社会学能够很好地融合“教育史”与“知识史”两种传统,它旨在探讨知识的产生和对社会存在的构建。在西方哲学领域,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探讨充满争议,尤其是主客体二元论所引发的认识论困境。现象学通过搁置对本体的预设,专注于意识如何呈现事物,试图解决这些困境。我们无意于介入此中讨论,只是接受舒茨的现象学及由其发轫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即将现实(reality)悬置,仅仅论述人类如何“理解”(understand)现实,并通过人们创造的知识(knowledge)建构社会实在(society/social reality)。因此,与其说世界是本体的,毋宁说世界是人类“理解”的产物,人类的理解与知识受制于自己生活的历史时代与地域空间。同时,由于人类理解的理性或反思能力,知识社会学中的“理解”便有普遍与特殊、本质与形式的分野,亦即超越(超越时空乃至自身)与禁锢(受制于时空而狭窄化自己的理解)的差异。作为知识之一种的政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可以由此得到界定。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对政治学的界定是一种“元问题”,是一种回到根本,去除时空具体形态的普遍性提问方式。从对知识的界定来看,政治知识是我们理解并用文字呈现所见政治实践的一种知识体系。如果将政治学视为解释和论证政治实践的学科,则它主要有两种形式:比较政治学和本国政治学。任何知识体系都是对特定地域生活实践的反映,故而是本国的政治学。然而,比较是识别事物的关键:地域之内,政治实践有别于生活实践或经济实践,当下与过往之间也有差异,地域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实践也各有特点;因此,政治学就是“比较”政治学。即使对于某国(地域)政治学而言,比较视角也是其寻找差异而建构自身的重要机制。外交上的敌我之分塑造了美国政治学的议题结构[1]、美国例外论以及导向自然进程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2],而自由民主与美国政治学价值取向[3]更是学界熟知的观点,至于后发国家的政治学,例如日本政治学,则要“面向美国政治学”才能获得其志向性[4]。更有学者指出,虽然学科概念以人们熟知的西方学科体系的面目出现,但是“任何一门学科所包含的那些基本活动,没有一个是只局限于欧洲的,也没有一个是只限于当下世界的‘先进的’产业社会的”[5]。
中国政治学同样遵循“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的双重结构,它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进行知识解释和理论化。中国的“现代”政治学不仅涉及中西比较,也包括现代与传统中国的对照,以及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差异比较,中国政治学的美国“映像”就是这个议题的反映。作为具体内容,“中国”政治学或中国政治研究是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形成的,产生了一系列现代中国的建制性概念。中国政治学的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常被视作相互独立,实则相辅相成。一方面,比较政治学应与中国政治研究相结合,而非仅停留在中国之外的纯外部研究;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研究应当有其超越地域性的比较意义,否则它就是例外论、目的论,陷入知识生产的掩耳盗铃、画地为牢。
总结一下,百年来中国现代政治学或现代中国政治学(这意味着还有一个古代中国政治学或中国的古典政治学),以“中国缺位的比较政治学”为开场,中经以非职业分工和非理论化为旨趣的、以教学与传播为指向的政治学校与政治训练,最后在社会结构理性化与大学体制内形成了一套“以中国为对象与方法”的专业化、理论化的中国政治学表述,其标志性成果便是一系列建制性概念的涌现。
二、语词的诞生与政治的社会建构
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认为,“现实(reality)是社会建构的,而这一建构过程正是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对象”[1]。在他们看来,“现实”与“知识”实则理解的两端,不同群体对待“现实”有不同态度:普通人将现实视为理所当然,哲学家时刻考问现实,社会学家则研究这种知识或观念是如何被理所当然地接受,如何在这些社会中得到维持,以及又如何在个体或整个机体那里失去它的“现实”属性。换言之,社会学家关注知识语词的诞生及其社会建构过程。
正如学者们指出的,舒茨的现象学接续马克斯·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它关注行动及其意义,从理解而不是客体角度去解释人们的行动[2]。因此,现象学将分析起点落在日常生活而非单纯的理论家叙事。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认为知识不能等同于思想,“思想史不应成为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思想史的研究者只是社会中关注理论解释偏好的少数人,然而所有人都生活在某种世界中[3]。与“思想”相比,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才是知识社会学的焦点,正是这种知识构成了所有社会赖以维系的意义之网。
常识性知识的单元是语词,即事物的名称。这些名称并非自然存在,而是人为赋予的,其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世界的内在时间和意义的理解。而意义的问题与内在时间意识相关,即个人对自己生命经历的感知[4]。因此,赋名本质上显示的是对个体生命流程的反省以及由意义交换而形成的客观性认识,如舒茨所说,“每一个作为记号对象的行动对象都可以回溯到行动流程”[5],它虽是人造物,但具有客观性。
舒茨列举“一同看到小鸟飞翔”说明两个主观意义的理解如何形成共同的认识[6]:即使我们不能确定彼此对飞翔小鸟的体验是否完全相同,只要我们意识到对方也在观察同一现象,我们的生命流程同步前进着,就可以说我们共同见证了这一事件。现象学让我们以悬置主客体的方式,通过各自的主观意义脉络实现理解的交换,只要各自的内在时间与生命体验同步进行,就可以将共同看到的事物视为具有客观性进而赋予其名称。因此,基于主体间性,我们就能从各自的自我理解与主观意义出发,建立外部世界的客观意义,进而给外部世界赋名,并由此形成表征外部事物的语词。
语言最初是口头的,源自面对面的互动。在面对面的情境中,语言保有一种内在的交互性。作为符号与象征系统,语言具有客观性。经过语言的分类,经验被匿名化了,它能够超越时间、空间和社会等多个维度,超越“此时此地”,在日常生活现实的不同部分之间搭建桥梁,实现“在地化”,从而将不同时空的经验和对象整合为一个意义整体。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构成语义场的组织规则,经由不断积累而形成社会知识库,为常识世界中的人们所共享。
回到源始的方法,使我们认识到,“学科”概念与其说是自明的,不如说是由不同研究个体的生命体验在历史过程中逐渐丰满与完善的,它更强调学科的形成过程或踪迹而不是倒放电影式地从过去寻求后来标准的起点[7]。学科知识概念由一系列成熟了的知识点(语言或语词表征的现实的具体名称)组成,而这些知识点的形成是人们理解外部世界并赋予意义的关键。知识概念的形成过程像一个黑箱,隐藏着从自然存在的reality(存在、现实、经验)到文化符号的秘密,并以名称(name)定格。因此,“理解对象”成为探究概念黑箱的核心机制,“理解方式”奠定了认知的结果与概念的名称,也落实了概念所蕴含的意义、价值或意识形态。
进而,在个体生命体验的基础上,语词形成并建构出我们的现实。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指出,社会的客观现实是通过“制度化”和“正当化”来构建的,而个体对社会结构的认同是通过“内化”来实现的[1]。这种过程使得客观现实的社会结构与主观现实的个体经验相一致,形成了具有客观性的对社会结构及其所属个体的内在认可。
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稳定秩序的共同体,这种秩序的稳定性正是源自制度化。活动通过不断重复变成惯例,这些惯例使人们能够相互预期进而简化互动。主体间性的交互性与惯例的类型化使制度具有客观性,使其仿佛是一个独立于个体偏好和生命的客观事实。然而,为了让制度得以延续,它还需要正当化。当制度传递给新一代时,它必须被解释、被证明,以说服新一代接受。在这个过程中,新一代通过社会化学习正当化的知识,从而被纳入并认同制度秩序。
正是在说服新一代的过程中,制度秩序分析的关键落脚到知识的社会分析上。在个体生命体验外化得以生产客观世界的时候,知识提供了“程序化”的通道,借助语言和以语言为基础的认知工具,知识将外部世界客体化。因此,由于以语言和知识为中介的客体化,现实被新的个体理解,同时现实被不断再生产出来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中国政治学的百年发展是一个将政治实践知识化和正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政权更迭,形成了自由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政治知识体系,正当化论证方式也随之变化,经历了解释、理论假设、明晰理论和象征认同的阶段。这正是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所说的正当性程序[2]。
首先,中国现代政治学是从比较政治学开始的。近代中西遭遇,传统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被敲碎装入现代学术分科的筐子,随着古今汉语的变换,尤其是现代汉语的流行,传统中国的主体性概念或建制性概念渐被抛弃,代之以现代西方政治概念,比如主权概念取代了“天下”,“德先生”“赛先生”取代了伦理政治观。“打倒孔家店”的去封建化过程,进一步抛弃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概念,民国大学体制下的政治学在接轨世界的同时,“中国论述”只发生在对象层面,中国并未作为分析性概念使用。在比较政治学的框架下,“中国”失落了。
其次,“中国论述”在根据地与中国共产党人中逐渐发展起来。中国革命在根据地的发展,催生了一套解释性政治话语,比如城乡社会革命下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政党替代传统士大夫成为政治权力主体、党的文献取代传统经学成为政治正当性论述、政治学校的干部训练取代传统科举制成为政治精英选拔机制、党军关系取代传统的文武关系。这些中国近代转型的政治命题在延安整风时期已经确定,然而,命题的正当化论述并没有遵循美国政治学的职业化和理性化路径,而是通过根据地的政治教育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课程,促成民众对新政治秩序的认同和内化。如此制度化与正当化过程,既导致了1952—1978年中国政治学的“政治学系缺位”,也可以解释何以中国政治研究并未消失。
再次,1978年后,随着欧美政治学的专业化和理论化论述的引入,中国政治学开始将根据地时期形成的,“中国”政治转型的日常和政治语言进行学术化和理论化处理,进而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建制性”概念。比较建制性概念的政治学论述与政治文件表达,我们发现议题及其结论并无二致,但是论说方式却大为不同,研究资料的经验化、论证过程的逻辑性、理论解释的变量特征尤其是经验研究之“理解之同情”贯穿始终,由此形成一套职业化、理论化表述的专业知识特征。
最后,象征世界通过一套概念装置,实现解释(explanatory)和训诫(exhortatory)[1]。最朴素的概念装置是神话,随后是神学与哲学,最后是科学[2]。只不过神话的创制主体是大众,神学、哲学和科学则更多由专家供给。专家专事概念生产,日益远离日常生活的实用需求,并由他们生产纯理论。从原则上说,终极正当化的限度与官方指定的“现实定义者”即“司正者”的理论雄心和理论创见是正相关的。当然,正当化专家既可能是现状的理论卫士,也可能是革命理论家,故而,1949年前后的政权争夺也是两种政治知识体系与两种正当化专家的斗争。
通过官方指定的“司正者”或“现实定义者”以政治宣传、政治教育与理论宣讲等方式,将由政治领袖言论、理论家论述的政治表述完成了的关于现代中国的知识解释与知识论证,构建成为一种“寻求富强”和“民族复兴”的象征观念系统,并经由象征世界的规范化和秩序化,形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制。上述正当化程序并不完全是一种历史对应,在每个历史阶段都产生着上述四种程序或面向,只不过其知识论述的质量与层次不同罢了。
上述客体化过程是通过内化而被个人接受与认同的。接受与认同的过程也是通常所谓的社会化的过程。除了生活角色,社会化也会赋予个体特定的社会角色,例如官员、教师、专家,这些角色知识学习环节更复杂,尤其是环境激励带来的现代职业身份认知变化,也会使其认知行为与社会行动发生变化。1978年以后中国政治学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张力之中,因此,政治学家的知识生产尴尬与内在理解掣肘也就在所难免了。
不管怎样,通过客体化、制度化和内化,赋名的政治语言建构出一个所谓的政治现实,政治学的学科认知正是此种社会建构的产物。由此,现代中国政治知识的产生也必须被置入政治进程的建构过程之中加以理解。在此建构过程中,培养政治精英(干部)的政治学院与大学内的系科建制都是政治知识的制度化形式或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它也内化成为指向不同的专业政治学家的学科认知,形成了相应的学科认同。故而,政治学与政治学史的名实之辩,实则是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的知识与社会建构的辩证法,它必须进入名称之下的政治进程的内在时间中才能准确确定其所指及其内容。
三、政治知识的类型与建制性概念
不同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所指的“知识”类型是不同的。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讲的是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的学科知识,“开放社会科学”的意思是要开放学科边界,进行跨学科的研究[3];舒茨现象学中的知识来自人们对自我行动的“意义”的“理解”,最后落脚到专业理论家的理论行动;伯格和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对知识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作为客观现实的社会”的正当化论述,更关注知识的功能而非类型。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知识类型:作为生活语言的日常知识或实践性知识、作为正当性论述的教学或传播性知识、作为职业分工或理论化的专业性学科知识。
首先,日常知识或实践性知识,指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语言,其基于我们对现实(reality)的“意义”(meaning)的理解而形成。它有以下几个特质:第一,自我能够在内在生命流程中感受到自己行动的意义;第二,自己能够理解他人行动的意义,他人也能够理解自己行动的意义,产生意义的主体间性和客观性;第三,这种意义的理解并非仅以文字形式达成,目不识丁者也能实现无障碍交流;第四,它以理念型抽象为语言形成机制。因此,日常知识更多是“语音或语义性知识”,而非“文字性知识”。
日常知识的适用空间,按照舒茨的说法,包括直接接触的周遭世界(生活世界)和间接接触的共同世界甚至包括前人世界(历史)和未来世界[1]。在共同世界中,它所呈现的对象不限于具体存在的个人,政府、企业乃至记号规则、法律规章、行为规范等都被包括在内,因此,它依赖知识作为中介联结不同的个体,大家都基于共同的知识/理解而共享客体化。不同的社会主体具有不同的知识范围与层次,社会的知识库由普遍知识与特定角色的专属知识两部分构成。具有特定功能或社会角色的他人或诸如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的社会集合体意味着一种特定角色的专属知识,这是一种知识的社会分配[2]。
其次,作为正当性论述的教学或传播性知识。正当化指人的观念建构起制度化的社会结构(客观社会)之后,为了论证其合理性而形成的解释与证明。因为正当化的目的在于论述一阶客体化(制度化的现实社会),故而采用知识社会化的方式,它分为四个层次[3]:第一,人类经验的语言客体化系统被传递给社会,最初的正当化就开始了,语言作为“是什么”的表述而存在,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样子,这个“是”表明知识先于价值,这一过程标志着知识对社会现实的初步解释和确认;第二,由一些已具雏形的理论假设组成,在这里会出现一些对客观意义丛不同的解释图示,这些解释图示与具体行动直接相连,表明具体行动之所以如此的缘由;第三,明晰的理论或“纯理论”,它通常由特定个人通过正式的传授程序进行传播;第四,象征世界,即世界的符号化过程,而不是日常经验的符号化。
假如说第一个层次是舒茨所说的生活世界的知识,第三个层次是理论化社会科学的“纯理论”,第四个层次是固化的意识形态,那么,第二个层次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虽未形成但“作为正当性论述”的知识教学或传播。在这个阶段,存在不同解释图示的竞争,也是不同意识形态为正在进行的制度化现实的正当性解释而进行的权力之战。正因为此,教学、传播而不是职业化、理论化研究成为其主要知识表达方式,与其说此时存在超越而独立的理论家,毋宁说知识生产者与知识传播者相交织。这一时期或维度的知识任务是普及而非精致化,只需解释图示,而无须深入少数精英的审美层次,无须提供一套精致的、理论化的知识表述。简言之,此时传播的政治知识只不过是日常语言的升级文字版。至于说经由概念装置而实现的象征世界,则更多是专业理论家的知识生产结果。
最后,作为职业分工或理论化的专业性学科知识。这是一些以理论表述为业的专业人群以“理论家”自居,以科学为准绳,以专业术语为表述单位,以理论化为表述旨趣的知识生产行为。舒茨专门列出一章讨论共同世界中不同于参与者的观察者,即“社会科学家”及其社会科学研究[4]。从职业分工角度说,它是社会中的少数人,19世纪末形成的现代学术分科体制,正是通过将专业性学术期刊作为“理论化”的知识把门人,将传统政治研究者排斥在外。从某个角度说,这种精致而深入的知识表述,更像一种审美活动,只有圈内人能看懂和理解,圈外人只能看个热闹。
因此,回到政治学的“概念原点”,即政治的知识论证,我们会发现政治研究实质上经历了三重发展:第一,生活或实践层面的政治知识生产,主要由普通人、政治领袖等非专业研究者开展。他们的身份和活动甚至与教育无关,知识生产方式也非正式发表。第二,正当化的传播性知识生产,这一过程通过政治学校、政治学院等教学机构,以及社会化媒体,将知识广泛传播,并由此形成制度化的社会结构。第三,职业研究者进行的专业性研究与知识生产。在知识纯度方面,专业学会和期刊作为把门人,确保了知识的高标准,但在传播范围和社会政治影响力方面,这种知识往往作用有限,有时甚至沦为圈内人的“职业游戏”和知识壁垒,研究成果的传播也多限于学术圈内部[1]。
如伯克所说,区别于传统的一般性知识,现代知识出现了日益体系化的分类特征[2]。自中世纪到16世纪,一个关键隐喻是把知识体系想象成一棵树。17世纪,出现了一个更为抽象的术语——“系统”来取代“树”的知识组织结构。而这一知识体系化是通过大学、课程、图书馆、百科全书进入实际应用中的,换言之,学术知识有了它的外部规定性。“课程”一词源于古典时代竞技运动的“跑道”,如今它是学科的制度规定,是“科系”的配套措施;图书馆书籍的分类体系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知识索引方式,它不同于乾隆皇帝《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也不同于伊斯兰法学家伊本·贾马的等级制书籍排序法;百科全书是按照主题或学科领域分类,最后发展为按照字母顺序分类,这也不同于中国明清时期百科全书基于经史子集等传统架构的独特编排。
在伯克看来,政治学以及稍后起步的政治经济学的兴起,都源自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的需要。政治学不再被视为一门从实践中获得“艺术”的传统研究,而更像是一门被系统化并以学术方式进行教学与研究的科学,在科学笼罩知识建制的启蒙时代,欧洲也用起了“政治科学”(science politica)一词,而政治经济学则由家政管理发展而来,它把国家看作一个庞大的家庭[3]。知识总是充满地域特征。伯克认为,现代知识的延展既是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瑞典、俄国等帝国扩张的先决条件,亦是其扩张所带来的必然结果[4]。知识与帝国的兴衰荣辱相互交织,在不同地域文化与政治格局的碰撞交融中,不断衍生出新的内涵与形态,深刻地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与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诉求。
知识的地域特征决定了基于地域理解的知识单位,即建制性概念(constitutive concept)。建制性概念是“如何理解自身”的认识论结果,也是回到研究者自身实践过程的“反身性(reflexivity)分析”,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自觉”[5]。建制性概念指向两个维度:第一,它是对特定地域共同体的理解;第二,它是一种特定的认识论方式。就前者而言,它是对此时此地而非彼时彼地的地域共同体的认知与理解;就后者而言,它意味着从现象学的视角,共同体成员从自己内在生命流程中体验共同体,并为之赋名的行动,故而我们用英文constitutive(西方意义上的宪制)而不是一般所言的fundamental(基础、基本)或established(已经建立的)来表达实践者对共同体的根本性认知与赋名。因此,它符合前述现象学对知识或语言发明的适当性解释,即概念建构的机制是回到初始和内在时间,通过个体行动的意义理解而赋予其名称,这个名称是类型化或理念化的结果,在现实中并不完全能够找到对应物。最后,它遵循适当性而非结果性论证逻辑。建制性概念实则经历了三种形态:第一,日常生活中的记号与赋名,无论是否识字都知道其意义;第二,制度或社会结构及其正当性论证中的概念;第三,走向知识的最高形态,即理论化的概念。
从上述界定看,现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建制性概念从何而来?首先,它来自“中国”这一地域性生活空间(舒茨所谓的“生活世界”);其次,它来自“现代”而不是古代中国(舒茨所谓的“共同世界”而不是“前人世界”或“后人世界”);最后,它是一种高度专业化与理论化的知识形态(特殊的、高度职业分工而来的理论化的知识形态,舒茨所谓的“社会科学”知识)。笔者试以“中国共产党及其党治”为例说明此种建制性概念的生产过程。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的核心词之一,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播带来的建党、根据地的革命实践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统治乃至当下的执政,它是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日常现象,“我”能够清晰地理解它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角色及其行动的意义,“你”也能理解此种意义,“我们”都能理解此种意义,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客观现实。换言之,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认知,无论老弱妇孺,还是士农工商都能准确地理解它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角色及其行动的意义,这是一种“共处其中”的理解与意义网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党治国家的政治学论述,由职业政治学家完成,而其要为大众所理解则不得不通过某种转译(学术科普和政治宣传)才能实现。
因此,以政治实践的知识层次而论,政治学可谓政治知识类型上的明珠,它将政治知识专业化与理论化了。同时,建制性概念是政治学的标识,它将专业化与理论化的政治知识论述抽象为标识性概念,而不再是冗长的理论表述,进一步说,它将理论符号化,使之具有象征意义。
四、共同体的营造与政治知识的结构
作为学术分科之一的现代政治学,是一个很明确而较狭窄的知识门类。按照华勒斯坦的说法,它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论证,在国家需要内在知识支持时才发展成一门学科[1]。这套知识滥觞于19世纪末的欧洲,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历史性。例如,现代西方政治学更多是一种政体研究,其政体取向来自古希腊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民主化研究。它最早研究古希腊的两类六种政体,一直到近代君主制被废弃后,讨论更多的是共和政体,再往后是美国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制政府,法国大革命后民主制逐渐超越了传统共和制的主导性话语。到了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采用了民主共和政体的复合性表述。进而,在二战的背景之下形成了民主和极权二元对立的政体类型,并在随后的“东亚奇迹”经验解释中发展出介于极权和民主之间的威权政体类型。我们看到,西方政治学在讨论国家或政治形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政体角度出发的。政体的现代实体是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沉重肉身。
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不是如何建构民族国家的问题,而是如何把传统中国的大一统共同体顺利地带进现代世界的问题[2]。可以说,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民族国家实体带来概念外部性的历史困境。现代民族国家是对1500年以来的西方世界的描述,那么1500年之前的西方是怎样的?古希腊会用国家或民族国家来表述雅典城邦吗?封建制时期会用国家或民族国家来表述领主庄园的集体生活吗?此外还有空间上的困境,欧西之外的那些地域,也没有使用“国家”一词,比如说古代中国有用“国”和“家”的单字表达不同的空间生活,但没有“国家”这样一个复合词表述。在今天看来,人类政治生活中至少存在三种相对独立的制度化的集体生活的经验,即以城邦为中心的古希腊、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西方以及晚清以前的传统中国。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建构一个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的人类集体生活的概念。古希腊雅典时期的生活、封建制下的生活和传统中国的生活都是人类的集体生活,这种集体生活用什么语词描述?我们试图用“共同体”概念描述不同地域人类的集体生活,并用“共同体及其营造”作为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共同体的营造”仅仅是一种形式化理论,它去除时间、地域等具体要素,而具有分析维度,能够涵盖有史以来的所有共同体的政治实践经验,尽管其笼统性特质带来的麻烦可能比带来的便利更大。
从发生学角度说,共同体营造的元问题,包括以下3类11项:第一类,人与政权或统治合法性问题。①人是什么?人如何与外部世界(自然、他人、群体)相处?因此有共处与超越的考虑。②为什么我们需要营造以及如何服从于一种集体生活?权力这种纯粹的物理力量如何从属于统治而非滥用?这是政权或统治权的合法性追问与论证。③统治权的外在结构表现为政权结构,同时它也包括统治机制或决策的运行。第二类,共同体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供给问题,即治权及其展开。共同体由人构成,其有衣食住行的公共产品需要,应建构一套精致而完整、以绩效能力为标准的政府结构以供给这些公共产品。为了实现这一供给或治理目标,它需要④政府权力在横向上的制度安排(政府形式),⑤政府权力在纵向上的制度安排(中央与地方的结构),以及⑥掌管治权的事务官员产生,公共政策的形成与执行。第三类,共同体结构的维系与再生产,这是可持续的问题。它包括⑦共同体内部是否需要以及怎样进行沟通与交流。首先,沟通是否必要?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沟通?以竞争还是合作的方式进行沟通?其次,以何种社会载体或行动单位进行沟通?传统的家族、现代的政党与社团在沟通中发挥着怎样的政治社会功能?⑧小型共同体如何实现自治?多大空间范围内可以自治?怎样的人群可以自治?自治所秉持的社会机制是什么?打破血缘的市场经济所能发生的自治适用于哪些空间(社区)或社会组织(行业组织)或人群(次血缘群体)?⑨共同体是否会病变、解体,如何实现维系与变迁:共同体维系的深层文化因素有哪些?为什么会“南橘北枳”?共同体依信仰而凝聚,那么,这种信仰必须是组织性或强制性的吗?没有组织性、强制性与教化是否以及怎样形成信仰共同体?神秘的自然力量与地方文化在共同体信仰中有着怎样的功能?⑩共同体会发生怎样的腐坏与病变?共同体又会发生怎样的变迁或革命?〇11共同体之间如何相处?是和平相处还是依丛林法则?
这些元问题构成了“共同体营造”的普遍性问题,并以“问题树”形式呈现了“共同体营造”的一般逻辑,有主干,有支脉。在比较维度上,以古希腊为起源的传统西方、近现代西方民族国家、伊斯兰世界、传统中国以及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与地域性经验都是对上述问题的具体回应与地域表现,各自政治形态的差异实质上是回应内容或表现形式的差异。围绕这些元问题及其时代回答,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社会政治知识谱系,经典著作均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具体知识回应。中国政治学只有在“共同体营造”的元问题上,才能重建比较政治学,走向国际社会科学。
这是一个常态政治的分析框架,也是一个比较分析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可以形成一系列基于中国经验的建制性概念。当前中国政治学的建制性概念主要是从常态政治角度建构的。比如传统政治概念“大一统”在今天的重新发掘与阐释,它并非革命中国的建制性概念,革命实践排斥大一统(宁可选择联省自治或民族自决),但是,它又保留了转型政治或革命实践的经验,尤其是作为近代政治权力中轴的革命党及其政治形态概念(即党政体制)。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说,政治学知识是政治知识类型上的明珠,建制性概念是政治学知识中的标识。政治学概念可以通过回溯政治生活概念和日常生活概念而得以被发现并理论化。由此,可以有两个推论:第一,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学科”,学科建制是知识建构现实的社会化形式,它受制于权力、地理、传播、历史等因素;第二,从理论化角度看狭义的“中国”政治学,它已经开始新的概念建构,但远未完成。在我们建构政治学的知识地图的过程中,只有回到历史、回到比较,才能找到世界的确定性与未来。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可以从“寻求差异”的学科身份意识开始,思考政治学如何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现代政治学如何与传统政治研究不同,从而建构中国政治学的现代内容。
[1]王向民:《中国政治学的建制性概念及其知识地图》,《学海》2023年第4期。
[1]朱光磊、王智睿:《中国“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与社会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郭台辉、乡智洋:《政治与政治学的概念互通:必然障碍及可能路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郭忠华:《政治概念移植的现实基础和形变模式》,《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5期;郭忠华、任剑涛、肖唐镖等:《中国政治概念研究的反思与展望》,《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
[2]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王楠、刘阳、吴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94—95页。
[1]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页。
[2]参见王向民:《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文献与问题》,《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期。对根据地政治学的研究,参见王向民、王钰鹏:《中国政治学的苏联传统及其实践》,《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王向民、王钰鹏:《政治教育与政治知识生产: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另一起源——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中心》,《江海学刊》2024年第2期。
[3]王向民、陈立业:《“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4]王向民:《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6期。
[1]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王义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19页。
[2]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王楠、刘阳、吴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27页。
[3]詹姆斯·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内田满:《面向美国政治学的志向性:早稻田政治学的形成过程》,唐亦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序”第1—6页;内田满:《早稻田与现代美国政治学》,唐亦农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第1—6页。
[5]G. E. R. Lloyd, Disciplines in the Making: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Elites,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72.
[1][3]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第19—20页。
[2]理查德·J.伯恩斯坦:《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黄瑞祺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舒茨代表作《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导论”部分也是从“韦伯的意义行动概念”入题。
[4][5][6]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4—15页,第164页,第228—229页。
[7]王向民:《回到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政治学史研究的概念建构》,《理论月刊》2024年第10期。
[1][2]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页,第117—121页。
[1]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6页。
[2]恩斯特·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赵海萍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28—132、246—249页。
[3]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3页。
[1][4]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99—201页,第313页。
[2][3]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9页,第117—121页。
[1]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章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6—47页。
[2][3][4]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100页,第108页,第125页。
[5]罗祎楠:《反求诸己:历史社会科学的实践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49、57页。
[1]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4—215页。
[2]王向民:《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6期。
〔责任编辑:史拴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