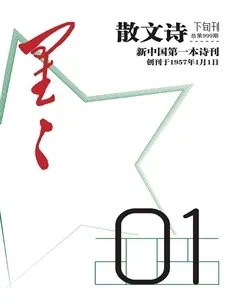羚羊城(组章)
从河州前往羚羊城
刚刚经过的百里沃野,古人称她枹罕。
刚刚目睹的商业大地,今人叫她河州。
这片古雍州之域,听说曾经被吐蕃统治,而今,早就不是我能安放灵肉的桑烟袅然升腾的番城了,我也只能从一些地名中嗅闻先人逸散几世的气息了。
我只是路过,要穿越土门关,前往雪山之下的羚羊城:也在甘肃之南,在海拔更高的地方。
远远地,我似乎能看到那高耸的土门关了——“火尔仓香告”,藏语里这么称呼。
《河州志》中说,这是陇地二十四关中规模最大的关隘。
但我已不在乎规模大小,我只知道:过了这个关口,当经幡渐渐拔高地势,在那云端,就是生我养我的亲亲的故乡了。
立秋日
羚羊城郊外。
在当周林卡里,他们吃喝,热舞,间或大笑一阵。
他们离我很远,但他们的声嗓离我很近,他们声嗓里的欢乐离我很近。
似乎只有我是伤感的,在山坡上起身,扭头四顾,想找到秋已到来的蛛丝马迹。
我找到了——
那个厨娘自林卡里出来,去了对面山坡。
她的背影孱弱,如蝼蚁在蠕动。
她的背影里,有少女的沉默?有老妪的孤独?
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死水微澜般的忍辱偷生?
阿妈呀,不知为什么,这一天,这一刻,我忽然就想起了您。
马家烧烤
炭火正烈,穹庐般的烤板上,切割成条状的肥牛嗞嗞冒烟,焦味在平民的天花板上游走,这焦糊的香味打开了我们的饱腹之欲……
我和他边动手边聊天,说起小时候的饥寒交迫,说起一块巴掌大的牛肉硬生生地被切割成三十五块,每一块只有指甲大小,整整品尝了一周之久。
我和他边聊天边动手,用生菜卷了熟肉,蘸上调料,一团又一团地送入幽深的食道。
炭火正烈,当穹庐般的烤板上只剩下夜的寂寞,我和他——这个名叫拉栋的屠夫,在羚羊城的马家烧烤店里,逗留了太多的时间。
现在,我们做好了回家的准备。
我在羚羊城
夜晚到来,黑暗悄然形成,然而不久,又被城市灯光蚕噬了完整的躯体。
这长街灯光,似乎又能把羚羊城重构。
我清清楚楚:当路灯突然熄灭,那鱼肚白的黎明,则会慢慢出现,羚羊城,则会以光的方式,再次将我容纳,恰似丰乳肥臀的女人容纳她的孩子。
这孩子或许会被赞美,或许,会在母爱里渐渐沉沦。
打工者归来
摊开手掌就会发现:
命运只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那些事业线、婚姻线和命运线,清楚地标示出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
是啊,总有很多命定的事时时发生,比如:我们在想念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想念着我们。
但只要一个女人带领着她的孩子们,等候在星光下的羚羊城路口,等候亮着大灯的客运车缓缓到来,我们就能知道——
她和孩子们的梦想,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