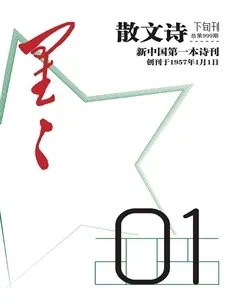每一口古井都虚怀若谷(组章)
一口古井,押中了时光旋转的韵脚
携一缕暗香远去。荷塘边,小路悠远,伸向田野的尽头,山的那一边。
双井,从传说中直起身来,多情的眼睛忧郁:还有什么在渐行渐远?
祖辈们的身影迷失在蒸气的朦胧中,煤油灯下的寂寞,是磨坊写出的又一曲哀怨。被磨亮的明月,曾照见小村女子的背影,捣衣声此起彼伏,替古井说出过现实。
天再干而井不干,雨再大而井不满。
肩挑手提的生活在过去里渐渐沉默,文脉的轮廓在时代的情怀中不断成长。面前的庄稼一茬茬收割,养育身后的村庄一层层长高。洗脚上岸的青年,背着行囊出发,目送的古井伫立成乡愁。
此刻,谁在古井旁聆听,听被井水洗过的乡音——那些押韵的方言,为生活描绘出又一条走向春天的路径。
曾经,它喊回过一棵树的魂魄;把高于流水的鸟鸣从夏天的干燥里救起;目睹过一位母亲从雨中的泥泞中挑回一担隐忍……现在,它把一切都收了回来:阳光的热情、屋顶上的火苗、季节的另类……从清朝凿开的文脉开始,一步一步,走出百年,走进岁月里既定的一行。
时光还在流转,以村之名,以路之名,以田野之名。双井岿然,不偏不倚,押中了小村时光旋转的韵脚。
沉醉的人还未从活用的词性中醒来
是你独拥的汪洋。
它是平面的,也是立体的。它在你眼前,也在你身体里。它叫鄱阳湖,也叫大宗三眼井。
一只眼打量世界,一只眼反观内心。那第三只眼呢?
一定有更多的秘密等待发现。
曾经,你发现身体里有暗流涌动,荡涤着朝代的秘史,时光简史。民间有无穷智慧!你用粗糙的肉身摁住了汹涌。拥挤的生活越过等待,你用平静安抚了七上八下的吊桶,安抚了一小片烟火人间。
现在,你发现一个被传说勾引的人,在章节里烂醉如泥。最是一口井的牵肠挂肚,让他从故乡来到异乡,又仿佛从异乡回到了故乡。这样的千回百转!他沿古老纹路彳亍回走,又从唐风宋韵的高贵中挣脱出来,在思想的宣纸上解构现实的微澜。
多少曾经抛弃了现实。多少现实被诗意的字词敲打。是什么被搬上舞台,红进绿出。花期如潮,湮没了荷塘。青苔与衰草努力让时光倒流,而一座村庄已脱胎出三座……
所有的经历都写意成曾经,万物都在现实的工笔里瘦身。青山、秀水、白云、候鸟挤进同一个画框,悬于炊烟的旧址,醉了人间。
夕阳西下,沉醉的人还未从活用的词性中醒来。你仍在心灵的一角隐居,古老成色偏安了大宗村整个春色。
每一口古井都虚怀若谷
大地辽阔。古老的词语色彩缤纷,为辽阔大地画像。
什么才是古老?村庄,河流,山冈……所有被时光做旧又被时光保鲜的,都在给我感动:大地辽阔,只有我最渺小;万物古老,只有我最易朽。
是什么创造了古老?比如一口井的诞生,让古老有了深意。定居,是井创造出的又一个感念的词,它系住了生活跋涉的脚步,有着与河流截然不同的生命朝向。
每一口井都虚怀若谷。它可以选择天涯,却甘愿据守眼前。它本可高于人间,却甘愿生活在低处。它是平静的,又是沸腾的。它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它是村民的孩子,也是村民的祖先。
我愿是井水的一滴,被沉默的水桶提起,升腾新生活的炊烟。也浇灌从朝代里走出的诗行,沿着浅浅深深的韵脚,走进一张新时代的纸,随春风荡漾。也有见到光的欢愉,那一刻,星星、太阳、月亮都是神明,给我指引,在去处验证来处。
具体到一个村庄,我爱一个叫安山村的地方。爱它的一口井,养大一个村庄;爱它的许多口井,养活一代代村民;爱它斑驳井栏,生活册页被时光磨出的毛边;爱它古老方言,被井水洗亮,在漫长故事里映出乡村底色。
此刻我或已成为一口井,站在安山村的某个角落,看炊烟再起,听云淡风轻。时光如流,我却心如止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