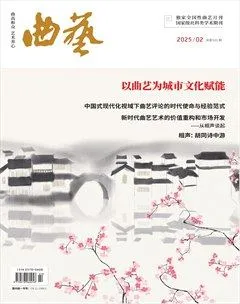数字人文视角下的同里宣卷档案资源开发实践路径研究
2020年,《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通知》强调了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性,提出分类采集梳理文化遗产数据,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奠定基础。随着大数据、知识图谱、深度学习等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其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传统人文学科领域并催生出数字人文理念,数字人文将计算机学科与人文学科紧密结合,通过数字技术深度开发档案资源,为传统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使传统人文学科研究的方式维度以及传统人文精神的视野语境发生了改变。
近年来,数字人文理念应用于档案学领域,通过数字技术深度开发档案资源,使档案资料从文件级转化为数据级,从单元信息转变为知识节点,实现了档案数据的拓展与延伸,改变了人类知识发现、注释、引用和展示的方式。同里宣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档案资源涵盖曲目创作、舞台演出等多方面,具有极高的艺术与研究价值。文章聚焦于同里宣卷档案资源的数据采集、关联及故事化呈现模式,旨在拓宽其开发思路,丰富数字人文在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理论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创新利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一、数字人文与同里宣卷概述

(一)数字人文的定义与特点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又称计算机人文,作为计算机学科与人文学科的深度融合产物,其以数字方法与档案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的交叉领域为研究对象,系统阐述数字方法与人文学科交叉融合的普遍规律及应用方法。相较于传统人文研究,数字人文更加关注信息检索与聚合能力,一是其研究对象实现了从传统纸质文献向数字化资源的转变。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等人文资料和文献档案,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数字资源或衍生性数字资源,拓宽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二是数据在数字人文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信息,它仅作为实体存在,数据的价值在于其被整理、联合并解读的过程中,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因此数字人文不仅强调数据的收集,更重视数据的处理与解读能力。三是数字人文采用计算性方法进行数据的查找与提取,如运用专名识别、正则表达式等技术手段。同时,它还运用数字技术、数据管理、分析、可视化以及VR/AR、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结合文本、内容、时序、空间、社会关系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可视化手段创造新的信息,为人文学科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视角与路径。
(二)同里宣卷的历史与特点
同里宣卷又称宝卷,其起源于唐代的变文“俗讲”与宋代的佛教“说经”,至清代逐渐演变为一种说唱艺术,主要流传于江苏南部的吴语地区,尤其是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同里宣卷综合了文学、音乐与表演艺术,采用吴江或同里方言进行说唱,韵散结合,包含说、噱、弹、唱、表、做等多种表演手段。表演团队一般有3到8人不等,一人主宣,一人或两人应和,其余人员则以磬子、二胡、三弦、扬琴等乐器伴奏。
同里宣卷经历了由“木鱼宣卷”到“丝弦宣卷”的演变过程,“木鱼宣卷”阶段,表演团队人数较少,曲调简单,文本多改编自佛道经文故事,如《妙英宝卷》《观音宝卷》《目莲宝卷》等。“丝弦宣卷”阶段,表演团队人数增加,曲调更加丰富多样,借鉴吸收了苏滩、江南小调、锡剧、越剧、评弹等艺术形式的营养,同时,宣卷内容也增加了民间传说、小说神话、同里宣卷故事和当代时事等,更具时代气息,如《洛阳桥》《玉佩记》《白兔记》《黄金印》等。近代同里宣卷产生了大量的表演卷目,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民间艺人,形成了以许维钧为首的“许派”、以徐银桥为首的“徐派”、以吴仲和为首的“吴派”和以褚凤梅为首的“褚派”等四大流派,这些流派一脉同源,又各具特色,具有丰富的流变性和稳定的精神内核,是传统文化的文献宝库和活化石②。目前,同里宣卷仍活跃在乡村庙会、农家婚庆、寿诞、迁居、婴儿剃头等礼仪场合,成为当地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同里宣卷档案数据采集与关联
(一)数据采集:构建多元化档案资源收集机制
首先,联合多元主体。传统同里宣卷档案资源的收集主要依赖于档案馆和博物馆等官方机构,这导致了档案资源结构的单一性,尤其是照片、声像等多媒体档案的数量严重不足。为打破这一局限性,需积极联合地方政府、档案馆、博物馆、教育机构及文化公司等多元主体,共同构建一个更为丰富和全面的档案资源收集体系。通过访谈同里宣卷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一艺术形式的内涵与价值,从而更准确地指导档案资源的收集工作。
其次,拓宽收集渠道。在构建多元化收集机制的基础上,还应积极拓宽档案资源的征集渠道,除了传统的征集方式外,可以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兴平台,广泛征集与同里宣卷相关的各类档案资源,同时加大对与同里宣卷相关专业档案的征集力度,如剧本、演出记录、道具图片等,以确保档案资源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最后,实现档案内容多元化。加强对同里宣卷档案史料、音像档案和口述档案等的收集工作,特别是口述档案,作为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对于还原同里宣卷的历史面貌、传承其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加强对同里宣卷热点新闻、政府公开信息、重大活动和展览等录音录像的收集,并进行定期剪辑和归档,做到应收尽收、应归尽归、应管尽管。
此外,推动档案管理向数字化转型,强化档案与信息科技、新兴设备的融合应用。如利用光盘检测仪等专业设备对光盘档案数据进行定期整理、检测与翻刻,确保信息长期保存;借助开源AI智能软件对老旧音视频档案进行修复优化,提升其质量;通过统计分析工具对存量和增量数字化档案进行归档、对比、检索与核查,确保电子数据与实体数据的一致性。
(二)数据关联:可视化构建同里宣卷档案知识图谱
1.知识图谱整体架构
知识图谱在同里宣卷档案资源的可视化表达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其架构由模式层与数据层共同构成,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知识图谱的构建与功能实现。模式层是知识图谱的骨架,它负责定义档案资源中的各类实体、概念及其属性。这一过程确保了档案元素描述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为数据的后续处理与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深入分析同里宣卷项目、传承人及相关地点等档案资源,模式层采用统一标准对这些资源进行描述,并建立起实体间的关联,从而全面揭示了档案资源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揭示不仅提升了档案资源的可视化程度,更为深入研究同里宣卷等文化遗产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数据层则是知识图谱的血肉,它以事实三元组的形式存储具体信息,实现了数据的有效组织。在数据层中,每一个事实都由一个实体、一个属性以及一个属性值组成,这种结构化的存储方式使得数据易于查询、分析和利用。通过数据层,用户可以快速获取到与同里宣卷相关的各类信息,如节目名称、传承人姓名、演出地点等,从而更加直观地了解同里宣卷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及文化价值。
2.知识图谱构建流程
知识图谱构建技术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可视化处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同里宣卷档案资源为例,其构建流程可精炼地划分为数据定义、聚类分析及模型构建三大核心阶段。
首先,数据定义是知识图谱构建的基石,此阶段需深入挖掘档案资源中的文化记忆,筛选出关键记忆实体、概念及其相关属性,构建模式层框架。对于同里宣卷档案而言,需基于其多维度特征,明确界定节目、来源派别、主要角色、扮演者等核心记忆实体,并补充这些实体间的语义联系,不仅为后续步骤提供了坚实的数据与理论基础,还确保了知识图谱构建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③。
其次,聚类分析是知识图谱构建的关键步骤,这一阶段需要对已定义的档案数据进行细致分类,并确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分类体系框架。针对同里宣卷档案资源的特性,可构建以“派别—主体”为核心的分类体系,即以流派创始人姓氏命名,将同里宣卷名家作为主体,对相关档案数据进行聚类处理。通过聚类分析,能够清晰地勾勒出数据关系图谱,有效梳理数据层关系,为后续模型构建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逻辑依据。
最后,基于数据定义和聚类分析的结果,构建同里宣卷档案资源的可视化知识图谱模型。考虑到同里宣卷档案资源的独特性,可围绕同里宣卷名家这一核心主体,设计包含“主体—节目—地位”三层结构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同里宣卷名家作为核心主体,能够全面涵盖档案资源;节目则代表了档案数据的来源关系,凸显了同里宣卷的艺术特色与内涵;地位则体现了档案数据的证据特性,彰显了同里宣卷档案资源的独特价值与重要意义。通过这一模型,可以实现对同里宣卷档案资源的形象化、全方位描述,从而实现对档案知识的有效组织与延伸。
三、同里宣卷档案数据的故事化呈现
(一)故事化组织的界定与平衡
首先,受众的多样化需求是故事化组织的重要考量。同里宣卷档案数据的受众群体包括从艺人员、文化爱好者、培训教育机构人员等,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知识需求和兴趣点。因此,在故事主题的选择上,应综合考虑这些受众的需求,形成全面的用户意向知识集。例如,对于从艺人员,可以聚焦演绎辅助的主题,提供与表演技巧、曲目创作等相关的档案故事;对于文化爱好者,则更注重文化普及,讲述同里宣卷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等;而对于培训教育机构人员则可能更关注寓教于乐的故事,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激发学习者的兴趣。
其次,叙事主题的界定还需考虑同里宣卷档案资源的特点。同里宣卷档案资源涉及范围广、载体形式多样,包括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多种类型。因此,在故事化组织时,需要根据已确定的叙事主题,对档案资源进行时间与空间范围的进一步限定,以便深入挖掘与主题相关的档案数据,构建全面的用户意向知识集。
(二)故事化设计的构建与逻辑
故事化设计的核心在于精准提取故事元素与巧妙搭建故事结构。提取过程需对同里宣卷档案数据进行深度整合与加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通过可视化图谱技术可以将人物、作品、时间、情节转折点等相关主题元素提取出来,并建立详尽的数据库。这一步骤深受“Data Storytelling”理念的启发,实现了数据与叙事的完美融合,特别是在处理同理宣卷艺术家个人档案时,能细致梳理其生平、代表作及艺术成就等故事元素。
在故事结构设计上,需兼顾受众的知识需求与叙事的艺术性,在传统框架中融入人文视角,使同理宣卷档案数据相互关联并形成有机整体。采用主题与时间并行的叙事策略,依循情节线索铺陈故事,同时确保核心主题的突出与一致性。通过强调核心情节的亮点与意外转折,显著提升故事的吸引力与说服力,使同里宣卷档案的故事讲述更加引人入胜,深刻展现其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
(三)故事化表达的多元与互动
随着档案发展社会语境的多元化,档案学者需多角度研究档案文化资源,挖掘其利用潜力。针对同里宣卷档案数据的故事化表达,不仅要使受众接纳故事,还需从多元视角提炼文化精髓,引导受众在故事中探索同里宣卷文化,强化文化自信。
在呈现方式上,可借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互动游戏等数字人文技术,通过交互技术提升受众的参与感与沉浸感,使其在欣赏故事的过程中深入理解同里宣卷文化,如开发基于同里宣卷档案的互动游戏,让受众在游戏中扮演角色,体验宣卷的表演场景和历史背景,增进对宣卷文化的理解和共鸣。此外,还可以结合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将同里宣卷档案数据的故事化成果进行广泛传播和推广,利用分享故事、互动评论等方式吸引更多受众关注和参与,进一步扩大同里宣卷文化的影响力。
四、结语
同里宣卷档案数据的故事化呈现是数据组织、设计与表达的综合过程。在数字人文视域下,通过明确受众需求、界定叙事主题、提取故事元素、设计结构并选择呈现方式,能充分挖掘其档案资源价值,为受众提供多元知识服务。这有助于同里宣卷文化的活态传承,并最大化实现档案资源的历史文化及教育价值。展望未来,档案资源开发应积极探索和实践故事化呈现等创新方法,以更好地服务于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推动档案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利用。
注释:
①王思琪、黄钟雨、付亚楠等:《数字人文视域下戏曲档案资源开发路径探析》,《北京档案》,2022年第2期,第26—28页。
②黄亚欣:《民俗文艺实践主体在民俗活动中的功能阐释—基于同里宣卷艺人的考察》,《民族艺术》,2023年第2期,105—115页。
③华林、张富秋、刘菊等:《数字人文视域下馆藏清代土尔扈特档案文献可视化开发》,《山西档案》,2024年第3期,第74—80页。
参考文献:
[1]张斌、李星玥、杨千:《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历史脉络、研究取向与发展进路》,《档案学研究》,2023年第1期,第18—24页。
[2]曲春梅、胡雯嘉:《数字时代的文化记忆: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的研究图景与展望》,《北京档案》,2024年第4期,第41—48页。
(作者:孙媛媛,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王玉明,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琪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