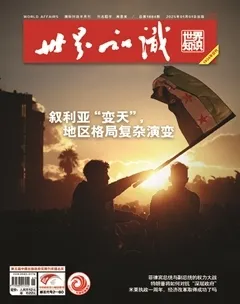美国汉学家眼中的儒家人论
西方个人主义和东方(尤其是儒家)社群主义之间的对比一直是比较哲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近几十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对儒家思想提出了原创性解读,以解释其社群主义的倾向。在这些美国学者看来,东西方社会关于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不同倾向,可以用不同哲学传统所隐含的人论来解释。而所谓人论,就是关于人之为人的理解与阐述,涉及人、个体或自我的概念。不同文化传统对人的理解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人论或人之范式,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政治传统和社会形态。儒家对人的理解因而成为西方解读儒家社群主义的切入点。
“角色人”与“社会关系人”
美国两位汉学家对儒家人论做出的诠释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首先是美国汉学家、马里兰州圣玛丽学院哲学教授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提出的“角色人”理论。罗思文在《权利个体与角色人》一文中指出,西方个人主义传统所隐含的人论认为,人是自由选择、独立自主、理性自利的个体。西方哲学从人身上抽象出某种纯粹的认知行为,将这种脱离肉体的“心灵”对逻辑理性的运用看作是选择、自主个体的实质,并认为这种“抽象人”在哲学上比“具体人”更为根本。这种“抽象人”通常也被认为拥有独立且先于社群的个体利益;他是理性的,拥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意愿,并通过理性选择来最大化自身利益。然而在罗思文看来,西方传统所预设的这种自主理性、自利、孤立的人之概念,尽管极大地维护了人之尊严,但“或许不是最合适、最好或最人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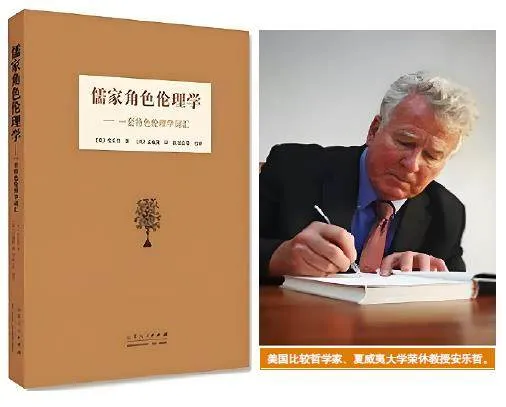
罗思文指出,与西方的人之概念形成对比的是儒家对人的理解。在他看来,儒家从来都不认为人是孤立的。由于儒家认为人的品质形塑于与他人的交往之中,所以儒家从人与人的交往或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并定义个体。在与他人的各种特定交往关系中,个体拥有各种角色,比如丈夫、父亲、兄弟、朋友、老师、同事等。这些角色为个体“织就了个人身份的某种独特模式”,使其被视为一个独特而完整的人。因此,在罗思文对儒家人论的诠释中,不存在独立于社群及其文化的、可被抽象认知的自我,“我”完全由角色及其相互关系而定。这种“角色人”概念与某种“语境化个体”概念相类似,即认为个体在某种重要意义上是社会语境之产物,不存在独立于社会语境的、孤立的、先验的自我。
与罗思文有着类似观点的是美国比较哲学家、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安乐哲(Roger T. Ames)。根据安乐哲对孟子的诠释,人是不断变化的各种关系的综合体,正是这些关系在人的一生中定义着人的本性。安乐哲认为,“礼”在儒家社会中有着类似权利在西方社会中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功能。通过礼仪熏陶,人们能够了解所继承的文化和价值,提高自己的身心修养,和谐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安乐哲认为,儒家如此注重个人修养和自我完善,以致认为个人实现与社会实现、政治实现之间有着某种关联性。在儒家看来,人性并非先天固有、静止不变,而是个人修养不断进步的成果,而这种修养大多涉及如何与他人相处。安乐哲暗示,正因为受到孟子的这种人性“不定论”的影响,儒家传统中并不存在无法转变的“分离的个性”,人也没有“独立且先于社会的利益”。在他看来,儒家传统中的人是社会性的而非个性的。
罗思文和安乐哲对儒家人论的诠释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当他们以“角色人”和“抽象人”概念来总结东西方人之范式时,两种哲学传统在倾向上的差异得到了清晰呈现,儒家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理解人之本质的特点也得到了凸显。然而,这种诠释却并非简单地强调人的某方面特性,而是有着本体论层面的哲学涵义。罗思文的“角色人”或安乐哲的“社会关系人”论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本质和存在意义的根本理解:人的本质是通过其在社会中的角色或关系来构建的,其存在价值是通过履行各种社会化角色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的。人是社会关系网中的节点,不存在独立于社会的个体或个体意志。
两种过度诠释
虽然罗思文和安乐哲对儒家人论的解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儒家社群主义倾向,但不得不说,罗思文的“角色人”理论和安乐哲的“社会关系人”论恐怕暗含了两种关于儒家人论的过度诠释。第一种涉及“仁”的范畴。儒家教义虽然强调角色和关系,但也对超出角色或关系的领域给出指引。虽然大多数儒家教义都在教育人们如何处理五种基本社会关系,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以及朋友,但将儒家人论解读成一种“纯粹的以角色为基础的道德观”恐怕过于极端。这种道德观暗示,个体与他者的道德关系——比如责任和义务——全都以角色为基础,从而排除了独立于角色的、与陌生人的道德关系。儒家思想虽然强调个体特定的角色和社群关系,但并没有完全回避个体与陌生人的道德关系。比如,儒家关于人的最重要看法是,人是能够实现“仁”的道德行事主体。儒家许多经典案例都表明,“仁”的对象并不只局限于与自己有私人关系之人。孔子解释仁就是“爱人”,即爱所有人,并教育弟子要“泛爱众”;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我们对他人的困难都有体恤之心,这里的他人当然也是指所有人。正因为我们对所有人都有仁爱之心,所以才会在看到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孺子”“将入于井”之时,有“怵惕恻隐之心”。
更重要的是,仁之对象的广泛性恰恰是儒家政治理想的要求。《礼记·大学》中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几千年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所尊崇的信条,也彰显了儒家思想所希冀达到的最高境界。这一理想以自我修养为起点,将仁爱由里往外推,从私人关系逐步推广至没有关系的普天之下所有人,儒家学说也因此被公认为“内圣外王”的学说,即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虽然儒家仁爱的对象是四海之内所有人,但其更加强调对诸如父子、夫妻等私人关系的仁爱也是事实。儒家将私人关系作为实现“仁”的首要方面。爱与自己有亲近关系的人要比爱他人更自然、更符合逻辑。如果个体对有着深厚情感关系的亲人都无法关爱的话,又怎么可能对没有任何交情的陌生人施以仁爱呢?不可否认,儒家学说对私人关系乃至社群关系的强调与其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有关。儒家学说出现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在当时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终身可能都生活在父母、丈夫、妻子、兄弟、姐妹、乡党等所组成的关系网中,很少有机会将仁爱推广至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只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的流动性、活动性大大增强,过去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社会,被由自由且陌生的个体所组成的公民社会替代,人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孔子、孟子或荀子生活在现代,他们或许会更多地探讨在没有私人关系的陌生人之间如何表达仁爱的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的公平或平等原则、赋予所有人“权利”是否与“仁”的思想相符。
关于儒家人论的另一种过度诠释涉及人的自主性问题。在罗思文的解读中,角色并不是构成人的身份的一部分,而是构成了他的全部。罗思文认为,对儒家来说,“我就是我的诸角色”,不存在独立于这些角色的、可为自主理性提供支撑的“心灵”或者意志。这种以角色或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对人的诠释,将儒家人论解读成了一种极端观点,即认为人完全是由其生活在其中的角色、所处的特定社会语境所决定,不存在独立的自我意志或品质。这种解读暗示了对人的自主性的全盘否定,认为人是一种完全被动的“牵线木偶”,服从于周遭人事环境的牵引。
这种对自主性全盘否定的解读与儒家教义并不完全相符,尤其从道德自主性的角度来看。在政治哲学中,道德自主和个体自主是两个既相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个体自主是指人对自己生活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个体自主注重选择自由,反对针对个体选择的外来干预。从个体自主的角度来看,传统儒家强调对君主、父亲、丈夫等权威的服从性,确实大大削弱了个体自主性,如果不是完全否定的话。道德自主是指人对自己道德生活的掌控权。如前所述,儒家视人为可以实现“仁”的道德行事主体。儒家对仁者或“君子”的阐释,恰恰说明儒家的道德自主性起码包含了两个相关要素,即个体对道德伦理的自发认同与接受,以及个体在道德生活中的实践与反思。因此,儒家教义非但没有全盘否定道德自主性,反而相当注重它,认为它是培养儒家式完美人格和实现儒家式政治理想的必需和关键。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两位美国学者对儒家学说的当代诠释,促进了我们自身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讨论,推进了中西方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比较、相互交融,也必将增进彼此的认知和理解。
(作者分别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