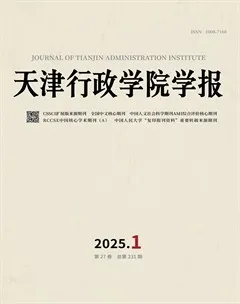从“摆平”到“规则之治”: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制度化转向与嵌入性审视
摘 要:制度化本质上是规则之治,实现制度化治理是当下我国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对于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制度化转向,现有研究尚侧重于整体、宏观向的考察,既缺少对制度化转向具体表现形态的梳理,也忽视了制度化转向在宏观制度环境中的嵌入性问题。X市A区矛调中心的治理实践在“结构—机制—行动”三个维度呈现了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制度化转向,具体表现为治理结构的一体化、治理机制的程序化与治理行动的规范化。从制度嵌入性的视角来看,这一制度化转向受到群众路线、政治压力与监督问责等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须不断调适优化。这表明,对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制度化转向的关注不应仅停留在制度建构这一层面,还应当将注意力适时放在影响制度存续与绩效产生的宏观制度环境上。
关键词:矛盾纠纷治理;矛调中心;枫桥经验;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25)01-0066-09
一、问题的提出
从微观层面与中国现实语境来看,社会矛盾纠纷主要是指由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和社会转型过程引起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对立、摩擦与冲突,强调的是一种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成员往往能够遭遇或切身感受到,如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信访矛盾纠纷、借贷纠纷、物业纠纷、征地拆迁纠纷等。近年来,我国矛盾纠纷数量持续高速增长[1],并呈现出经济性、复杂性、对抗性、多变性和危害性等特征[2],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的安全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并要求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3](p.5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织密社会安全风险防控网,切实维护社会稳定[4](p.16)。显然,如何以“枫桥经验”为统领,推动实现社会矛盾纠纷有效治理,有效应对托克维尔所言的社会发展悖论的挑战——“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远没有使人民乐其所守而到处滋生着一种不安定情绪”[5](p.175),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进行了诸多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创新实践,例如,“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以下简称“矛调中心”)既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载体,也是一种周密的正式治理制度设计。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安吉县矛调中心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让老百姓遇到问题时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并指出安吉县的做法值得推广[6]。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考察社会矛盾纠纷治理,便会发现,以矛调中心为代表的一系列治理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制度转型特征[7],即通过构建常态化、规范化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以法治化、程序化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化解矛盾纠纷与满足民众合理合法诉求。换言之,当下社会矛盾纠纷治理更加倾向在制度化渠道内解决问题。那么,对于这一治理转向,其在治理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态是什么样的?又遇到了何种问题?这些均有待进一步回答。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受到学界高度关注,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从治理现状来看,我国形成了行政机关主导模式、法院主导模式和检察机关主导模式三种调处机制类型[8],但具体治理过程则面临着治理主体单一与化解程序随意[9]、调处方式供给不足[10]、纠纷解决模式分流不畅[11]、智能化处置能力不足[12]等多重困境。在应对策略方面,一些研究指出,在面对群体性事件等矛盾纠纷时,地方政府并非以法律或制度为逻辑起点,而是以拖延、收买、欺瞒、要挟和限制自由等制度框架外的“摆平”方式来控制问题[13]。这种“摆平”方式常常表现为“政府兜底”,即地方和基层政府通过给予冲突方好处和利益来化解矛盾,而不是依照法律、政策、规则等行事[14]。例如,普通物业纠纷往往需要上级权力的直接介入才能最终解决,而这种解决方式很容易脱离规则治理的框架[15]。依靠“摆平”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迅速解决矛盾纠纷,但其治理过程与结果往往缺乏必要的制度依据,在限制与侵害群众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使基层政府陷入了“维稳怪圈”[16]。
为有效应对上述困境,除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外,学界还提出了构建诉讼与调解相融合的纠纷解决方式[17]、建立社会矛盾跨域联调行动规则体系[18]、加大协商民主应用与推广[19]、坚持法治化路径[20]等各类政策建议。与此同时,现有研究围绕地方治理实践相继提炼出“网格+调解”[21]、社会组织介入[22]、以“矛调中心”为代表的系统集成[23]等模式。这既进一步刻画了治理创新的运行机理,也为推进有效治理提供了路径指引。
已有文献及经验表明,随着我国社会治理总体趋向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和法治化[24],社会矛盾纠纷治理也正经历着深刻转型,地方政府围绕此议题进行了大量实践创新,不仅治理思维与治理过程更为精细化,对治理手段的应用也更为规范,更加强调在制度框架内依法依规解决问题。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从整体上增进了学界对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发展趋势的认知与理解,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背景性知识与大量经验素材。不足之处在于,现有研究虽敏感捕捉到了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制度化转向趋势,但尚侧重于整体、宏观的考察,既缺少对制度化转向的具体表现形态的梳理归纳,也忽视了制度化转向在宏观制度环境中的嵌入性问题。因此,本文以X市A区矛调中心的治理实践为切入点,对其制度化转向形态展开考察,并探究其制度建构在当下治理环境中的嵌入性问题。
(二)“结构—机制—行动”的分析框架
在通常意义上,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25](p.3)。制度的建立固然重要,但是其发展、完善、巩固与持续的过程与状态,即“制度化”的过程也同样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强调的也是要及时将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的重要原则、规则和规律加以制度化乃至法制化[26]。关于“制度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新制度主义形成了三种典型的分析流派与范式[27]: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视为政治体制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规范和实践体系,着重探讨制度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与非预期后果;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坚持理性人假设,强调战略信息和行为在制度产生和变化中的作用,将制度起源归因于行为者之间的理性设计和自愿协议;社会学制度主义将制度化视为特定文化活动与实践的历史积累,并认为组织对制度形式与程序的采用是出于合法性考量,遵循的是社会适应逻辑而非工具逻辑。由此可见,制度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我们很难用一个特定的理论视角完全清晰地阐述说明。
但从内容与功能来看,制度化具有一些普适性意涵,是指从规则到行为等一系列社会中的范畴、现象实现规范化、常态/持续化、通约化的一种历时性过程[28],是各类行动者为实现自身目的而进行政治努力的产物[29](pp.102-104)。进一步来看,制度化既可以在工具层面表示减少工具理性色彩并推动行为模式常态化的过程,也可以在规范层面表示达成共识、获得规范的过程。例如,现有运动式治理的研究即将制度化视为建立和形成稳定治理结构、组织和机制的过程[30]。由此可见,制度化与规则、主体行为、组织结构等要素息息相关,体现为一个包含主体认知与行为、规则制度、组织结构等在内的动态实践过程[31]。结合上述研究与治理实践,本文以结构、机制、行动作为关键分析要素,搭建一个基于“结构—机制—行动”的制度化分析框架。其中,结构是指治理主体间关系所呈现的“制度化的权力安排和互动模式”[32],机制是“做事的制度以及方法或者是制度化了的方法”[33],行动则指向“制度框架内行动者行为的模式化”[34](p.63),意味着治理主体的行为遵循制度的原则与要求,受到正式法律规范的约束。
如前所述,以矛调中心为代表的治理模式就是一种正式制度设计,这一分析框架可用于考察其运行要素与机理,并以此探讨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制度化转向形态。具体而言,治理结构界定了各治理主体的权责与常态互动;治理机制以更为细化的规则制度为主要内容,为治理行动提供遵循与约束;治理行动是在结构、机制的框架下对矛盾纠纷施加的治理活动,对机制与结构具有反馈作用。由此,本文将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制度化定义为:在清晰明确的规则文本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完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使治理主体的治理行动在制度框架内有序展开,以实现治理的稳定性与有效性,最终使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制度趋向成熟和定型。
三、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制度化转向
的考察分析
近年来,X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国首创集调解、信访接待、诉讼服务、法律咨询与援助、心理疏导等功能为一体的市、区、街(乡镇)三级矛调中心,形成了“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矛盾纠纷化解模式。X市A区矛调中心在市委市政府统筹部署下于2020年5月开始运行,下设办公室与接待组,现由区委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协调、区信访办负责日常保障、区司法局负责“大调解”工作统筹指导,区网格中心负责督导街道中心开展工作。自成立以来,A区矛调中心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创造了良好的治理绩效,A区也因此而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基于在2024年3-5月对X市A区矛调中心所开展的田野调研,并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我们将具体分析A区矛调中心的制度化实践。
(一)治理结构的一体化
在以往横向部门“单打独斗”与上级部门向下卸责的分散型矛盾纠纷治理情境下,各职能部门之间往往联系松散且难以统筹协调。而A区矛调中心围绕矛盾纠纷化解这一议题,以自身为治理平台,对纠纷高频常发领域的部门进行综合集成,通过部门常驻、轮驻、随驻以及邀请第三方参与等方式打造治理体系,构建起了一体化的治理结构。同时,该区矛调中心还将区网格中心也纳入进来,以方便借助基层网格的力量进行矛盾纠纷排查。在结构运作中,矛调中心通过统一、协调的方法组织入驻部门共同开展调处工作,使治理界面得以精简,降低了部门间协作成本,同时也确保了治理资源有效利用、治理信息传递流畅与目标一致性。其原因在于,“政治势能”赋予了矛调中心足够的协调能力,主持矛调中心日常运行的信访办主任同时兼任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和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能通过“党的领导在场”消除社会矛盾纠纷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进一步优化统筹部门间资源,增强协调过程的权威性。
从治理结果来看,以往A区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力量分散、衔接不畅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且治理绩效的产生又再次强化了以矛调中心为平台的一体化治理结构的稳定性。针对复杂矛盾纠纷,矛调中心协调指导入驻部门对当事人展开调解,并召集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专项研讨,共同制定化解方案,一站式联合接待与调处,防止当事人因情绪失控而对正常社会秩序造成破坏。例如,为解决始于2011年的某社区拆迁矛盾,区矛调中心对接市级中心,首先通过“吹哨报道”召集市规划局、市土地利用中心、市高级法院等部门明确拆迁所涉土地性质,其次通过发挥自身综合协调作用,推动区司法局、区规划局、区住建委、区法院、区房建公司、区城投公司先后召开十余次专题协商会议,最终拿出了合法合理的化解方案,有力推动了事项的化解。
(二)治理机制的程序化
制度化涉及约束机制的建构与形成[35]。在社会矛盾纠纷治理中,约束机制意味着治理过程的程序性安排,强调将制度建构贯穿、覆盖治理的全过程。就A区而言,其非常重视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的建立,并强调通过矛调中心来承载与运行这一机制。可以说,矛调中心本身就是一种机制安排。具体来看,A区矛调中心以解决问题和高效运行为导向,制定《矛调中心工作流程管理规定》《矛调中心各派驻单位工作责任制度》等工作制度,按照受理、分流、调处、回访、考核的治理流程构建了“一门受理—分类办理—限时反馈—群众评价—考核问效”的全链条闭环治理机制,并以事项受理、落实直报、分流办理、联调联处、督办落实等具体制度作为支撑,基本实现了社会矛盾纠纷的程序化与层级化治理。
概括而言,矛调中心对于矛盾纠纷事项采用一站式接收、七日内答复、二日内回访评价的工作模式。中心受理矛盾纠纷后,根据其类别与性质,实行就地化解、转交化解或联调联处。一方面,中心进驻人员为入驻部门主要负责人,代表本部门直接进行接待调处,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化解,若矛盾纠纷涉及尚未入驻的部门,中心则会将其转交属事部门或调解组织;另一方面,若矛盾纠纷过于复杂,中心会通过专题协调会的形式推动多部门联合调处。在事项办理中,矛调中心采取发函、约谈等方式进行督办,对推诿、拖延以及因化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影响的部门和个人,交由区纪委监委进行问责。从矛盾纠纷化解情况来看,其基本行进在程序化的闭环治理机制中。例如,对于信访矛盾纠纷,矛调中心联合属事部门启动信访经历调查机制,对历史档案、问题线索进行再梳理,推动事项在闭环治理机制中再次化解。同时,A区以市级先后两次部署信访矛盾纠纷专项治理行动为契机,对闭环治理机制进行再完善,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的若干措施》,持续推动制度化建设。
(三)治理行动的规范化
制度与行为不可分割,治理行动在制度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长效性。在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制度化转向中,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设为治理主体基本框定了规范化的行动框架。随着自上而下对社会治理制度化、法治化、精细化的强调,治理行动的展开均以法律规范、政策方针等正式的制度性资源为基础。这既增强了治理主体间行为的一致性,也有效抑制了拖延、收买、欺瞒等策略主义行为。结合具体案例来看,A区矛调中心以及属事、属地两方面的治理行动呈现出明显的规范化特征。
首先,治理行动的标准得以明确。标准设定为治理行动奠定了规范化的基调。针对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区矛调中心将“办理程序和处理文书规范”与当事人“事心双解”作为化解成功的判断标准。对于最为棘手的信访矛盾纠纷,区矛调中心则按照“三到位一处理”原则进行化解。在信访矛盾纠纷化解中,标准的设定极大压缩了当事人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空间,也有效防止了工作人员在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范行为。正如区矛调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所言,“现在大家做工作心里也都有个‘尺’,就是依据法条、标准来”(访谈记录20240311)。例如,在区矛调中心成立后,一些以上访为生、具有丰富信访经验的“专业”上访户以此为契机提出新的诉求,对此,矛调中心与属事部门共同研判,以法律法规为基准,认定其为无理诉求,不再予以受理,改变了以往“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的化解策略。对于诉求过高的信访事项,工作人员一方面依法依规给予适当帮扶,另一方面通过不断的政策解释降低其诉求,保证矛盾纠纷在制度框架内解决。
其次,治理行动的透明度有所增加。增加透明度是政府治理行动规范化的主要表现之一。一方面,区矛调中心引入矛盾纠纷“四方”调处机制,增加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调解员等多方力量,在矛盾“双方”的基础上增设事项“相关方”“观察方”“主持人(方)”,以凸显调处化解的公开、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群体上访事项,区矛调中心转交街道办事处,推动其召开群众代表见面会,并协调属事部门对群众关切的问题进行记录、解答。这些做法有效增加了矛盾纠纷解决的透明度,防止了因信息差而造成的误解、不信任等问题。同时,按照上级部署安排,区矛调中心推广使用矛盾纠纷调处信息化系统,在推动实现事件调度、事件调处、事件督办、分析研判等功能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透明度,当事人可通过APP在线上报矛盾纠纷事件、查询历史上报矛盾纠纷事件情况和矛盾纠纷评价等。
最后,治理行动的回应性有所增强。回应性是政府行为规范化的内在要义[36],回应性的增强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矛调中心按照“一类一析”的标准牵头组织专题会议,同属地街道和相关职能部门共同会商研究化解方案,并邀请当事人进行沟通、面谈,综合运用情、理、法等多元手段,及时回应民众诉求。而且,利用“吹哨报道”机制,街道办事处可召开由市级、区级职能部门共同参加的联合接访会,进而增强治理回应力度。另一方面,矛调中心推动建立人数规模较小、运转更为灵活的、由部门内部或街道办事处骨干人员组成的工作专班。该专班负责当事人接待、政策解释、情绪安抚、纠纷化解等工作,并通过进行深入的沟通在较短时间内充分了解当事人诉求,进而集中注意力与资源实现问题的快速反应与处置,防止矛盾纠纷演化升级。
四、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制度化
转向的嵌入性审视
制度创新与变迁无法离开现实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资源所能提供的条件,即任何一项制度终归要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与环境之中,否则不可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效益与长久稳定[37]。也就是说,任何制度都嵌入更大的制度、结构乃至文化当中,在更大的制度环境中运作,我们必须关注制度嵌入性的重要意义[38]。显然,对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制度化转向的研究与反思,离不开我国独有的制度架构、政治体制与治理实践经验这些更大的制度环境。在前述分析制度化转向具体表现形态的基础上,本文将这一制度化转向纳入我国整体性的宏观制度情境中进行嵌入性审视。
(一)“制度规则”与“群众路线”之间的治理张力
随着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格局的巩固与完善,作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群众路线”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原则。以群众路线为根本遵循,党在当代中国革命和社会治理中形成了以心换心、以情换情、以德报怨、以情感人的情感治理实践模式[39]。从治理绩效来看,在社会矛盾纠纷治理中,以群众路线为根本、情感治理为表征的治理形态在密切党群关系、回应群众诉求、抑制官僚主义、提升政治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结合治理实践来看,在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制度化转向的过程中,制度规则的建构与上述治理形态在纠纷受理、办理等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紧张关系。
一方面,矛调中心受理了不少涉法涉诉类矛盾纠纷,有悖于自身的制度功能定位。从制度建构上看,矛调中心的定位是接收家事纠纷、邻里纠纷、普通信访矛盾纠纷等适宜调解事项。X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即规定,矛盾纠纷化解应当遵循“和解、调解优先”原则,更强调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纠纷,且从国家对涉法涉诉类纠纷尤其是对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纠纷的规定来看,应当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此类问题。但在实际运行中,群众路线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尽可能地“关心、爱护老百姓”,并“在某种程度上认可突破科层制与法治程序主义而回应民众的各类诉求”[40]。由此,A区矛调中心吸纳了大量涉法涉诉类纠纷,甚至包括一些法院已经明确判决的事项,但以和解、调解为优先原则的矛调中心并无能力也无太大意愿处理这类纠纷。有工作人员表示,“我们也不想给老百姓拖着,但这些事更适合通过诉讼渠道解决,咱这里主要是发挥调解作用”(访谈记录20240320)。对于A区矛调中心的劝导或分流,一些群众又往往不理解,并冠之以“拖延推卸”“不负责任”等负面评价,矛调中心因此陷入两难境地——群众工作思维要求其应收尽收,但在制度设置上,其并无能力或职责处理涉法涉诉类纠纷。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纠纷受理与办理中的“倒金字塔”现象,与“就地化解”“属地管理”等制度设计与要求相抵牾。对于高层级政府而言,其扮演着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制度设计者与治理结果裁决者的角色,往往将矛盾纠纷走访排查、下访接访视为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而在“差序政府信任”的格局下,群众又往往对高层级政府更为信任和期待,更倾向于将自身矛盾纠纷遭遇反映给高层级政府,以求能迅速获得关注并解决问题。这种走群众路线的方式虽能在较短时间内缩短沟通层级[41],却与当下制度建构产生了一定张力: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强调“就地化解”与“属地管理”,防止矛盾纠纷上行是基层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但从实际调研来看,群众更倾向于向市级中心反映诉求,区级其次,街道最次,而市级或区级中心往往需要将受理事项再次分流,以实现分级调处。例如,在专项治理行动期间或敏感时期,A区矛调中心往往需要在市矛调中心设置工作站,安排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接待本辖区矛盾纠纷当事人,其工作重心也从“化解”变成了“劝离”,这导致既无法有效实现就地化解,也增加了工作人员工作负担。
(二)政治压力、监督问责与制度化消解
在压力型体制下,政治压力与监督问责是推动社会矛盾纠纷治理走向制度化的有力工具。例如,在三级矛调中心组建之初,时任市委书记便前往市级中心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推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规范有序运行,并要加强督办落实。显然,一把手的表态能够迅速推动相关工作的展开。但是,较强的政治压力与高密度的监督问责反而也容易消解科层体系将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制度化的努力。在自上而下塑造基层治理统一规则体系的过程中,顶格管理、强化监督问责成为其中的突出现象[42]。在关涉社会安全稳定的矛盾纠纷治理领域,上述现象同样存在。就A区治理实践而言,时任A区区委书记在召开相关专题工作会议时多次强调,要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到人,对于群众反映事项较多、矛盾纠纷化解不力的部门,区委主管领导要约谈“一把手”,进一步压实责任。事实上,在综治维稳工作仍实行“一票否决”的背景下,基层政府与属事部门主要领导承担着巨大考核压力与问责风险。在敏感时期,区委书记、区委常委等主要领导又常常前往区矛调中心与信访办进行指示督导,进一步将领导个人权威与政治压力传递给工作人员。尤其是一些疑难信访矛盾纠纷极易催生越级访、集体访、进京访等突破正常信访秩序的行为,矛调中心工作人员往往因此而面临极大压力,“有些事项化解难度很大,我们压力也很大,一到‘两会’,当事人可能就去越级访、集体访,深入追究下来,可能就要问责了”(访谈记录20240325)。
上述现象从两个方面造成了制度化转向中的困境。一方面,为避免被政治问责以及缓和来自上级的压力,且受制于治理能力与资源约束,以A区矛调中心为代表的治理主体在具体治理工作中留下了大量调解文字记录、图像记录等,以凸显其工作的合法合规和所做出的努力。但一些矛盾纠纷事项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而是困在“受理—分流—化解—反馈”等流程中,矛盾纠纷治理出现了“制度仪式化”或“制度空转”的问题。也就是说,强政治压力与高密度监督问责引发了治理主体的避责倾向,虽然治理主体做出了一系列符合制度要求的“规定动作”,但其目的却是“规避责任”而非“化解矛盾”。另一方面,为回应上级政治压力并加大矛盾化解力度,区矛调中心与属地属事部门通常选择“领导包案”这一治理方式。结合案例来看,尽管X市印发有《党委和政府维护稳定工作领导责任制规定(试行)》,且领导包案能够“运用领导权威将原有科层制治理资源重构,向社会重点及疑难治理事项倾斜”[43],但其也存在过分倚重领导个人意志、盲目介入纠纷事项等弊端,往往会在无形中对制度化产生一定侵蚀与冲击,并不一定利于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较大政治压力下,作为个人权威意志的体现,领导包案往往容易越过现有流程与制度规范行事。对此,有工作人员认为,“领导包案、领导批示确实比较容易推动事项解决,‘官大一级压死人’嘛,就像市里让区里干活儿,区里肯定得干,但是很容易就不那么讲究法律法规了”(访谈记录20240325)。
五、总结与讨论
制度建设居于国家建设中的首要位置,走向制度化治理是我国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44]。基于对X市A区矛调中心的考察分析,本文从结构、机制、行动三个维度探讨了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制度化转向趋势,对其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制度化转向受到“群众路线”、政治压力与监督问责等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在形成治理张力的同时也易侵蚀制度化的成果。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揭示了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制度化转向的具体形态,并由此考察了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治理过程;另一方面,对制度化转向的嵌入性审视有助于为深化社会矛盾纠纷治理领域的制度建设提供整体性知识。总体来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自上而下持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开始从“摆平”应对转向具有普遍主义的规则之治,其以明确的制度规范与政策文本为治理依据,有效抑制与减少了变通性、权宜性等策略行为的使用,具有规范化、清晰化的治理运作特征。这对回应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但也需要看到,社会矛盾纠纷治理正处于转型过程,在治理实践中既有强调依法依规调处的正式治理,也存在一些策略主义行为。在一些复杂性、不确定性与应急性的治理情境中,“人盯人”“收买”等非正式治理机制仍会被用以解决矛盾冲突。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关乎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与国家政治制度的感知和认同,属于于细微处见宏观的日常生活治理。未来,应在持续减少策略主义行为的同时,着重探讨制度化治理如何走深走实,以使其更好地嵌入宏观制度环境之中。对此,我们应在治理前端做好矛盾纠纷事项的制度化、规范化分流工作,根据矛盾纠纷的性质与类别妥善有效地向更适宜的调处机构进行分流,避免涉法涉诉类纠纷流入矛调中心与信访渠道。同时,在具体治理过程中,应当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就践行“群众路线”发展出更具可操作性的中观理论[45],并与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制度化相衔接。此外,各地还应把握好监督问责的标准与限度,处理好监督问责“过软”和“过度”的关系。结合A区的治理实践不难推测,一旦监督问责有所弱化,社会矛盾纠纷治理非制度化的行事空间便可能被放大,但当监督问责持续强化并超过基层所承受之限度时,避责现象又会出现,致使制度化治理“有名无实”。显然,如何找到监督问责与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制度化的平衡点,仍是一个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摸索和反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荆龙.周强就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N].人民法院报,2021-10-20.
[2]陶林.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基层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机制构建[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7,(4).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4]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5][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N].人民日报,2020-04-02.
[7]温丙存.我国基层纠纷治理的制度转型与创新发展——基于2019—2020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分析[J].求实,2021,(4).
[8]杨林,赵秋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研究——基于三种实践模式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2,(6).
[9]张文汇.法治化语境下的基层矛盾化解路径选择[J].东岳论丛,2019,(5).
[10]郭志远.我国基层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机制创新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11]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践困境与路径探析[J].中国应用法学,2017,(3).
[12]郑长旭.新时期大数据赋能多元矛盾纠纷治理:实践驱动、问题挑战与机制优化[J].中国行政管理,2023,(3).
[13]郁建兴,黄飚.地方政府在社会抗争事件中的“摆平”策略[J].政治学研究,2016,(2).
[14]杨华.“政府兜底”:当前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的现象与逻辑[J].公共管理学报,2014,(2).
[15]汪仲启,陈奇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困境的成因和破解之道——以一个居民小区的物业纠纷演化过程为例[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2).
[16]金太军,赵军锋.基层政府“维稳怪圈”:现状、成因与对策[J].政治学研究,2012,(4).
[17]郭星华,任建通.基层纠纷社会治理的探索——从“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5,(1).
[18]黄科.社会矛盾跨域联调:行动逻辑、情境检视与实践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23,(1).
[19]卢芳霞.协商民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功能与实现路径——基于浙江基层协商民主经验的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4).
[20]孙培军,丁远朋.以法治路径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一个三维逻辑分析框架[J].理论视野,2019,(4).
[21]陈辉.“网格+调解”何以化解基层矛盾?——以南京市为例[J].行政论坛,2023,(3).
[22]张帆,田毅鹏.社会性治理技术:社会组织对社会矛盾的化解之道——以J市信访法律事务服务中心为例[J].河北学刊,2021,(4).
[23]曹海军,鲍操.系统集成与部门协同: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流程再造与治理效能——以浙江省A县“矛调中心”为例[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0,(6).
[24]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辨析[J].社会学评论,2014,(3).
[25][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26]王名,李朔严.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系统观点与美好生活价值观[J].中国行政管理,2018,(3).
[27]Hall P A,Taylor R C 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J].Political Studies,1996,(5).
[28]郁建兴,秦上人.制度化:内涵、类型学、生成机制与评价[J].学术月刊,2015,(3).
[29]Dimaggio P J.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C]//Zucker L G.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Cultures and Environment.Cambridge,MA:Ballinger,1988.
[30]向淼,郁建兴.运动式治理的长效化:短期性中心工作何以嵌入长期发展战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4,(1).
[31]向玉琼,李清.环境风险治理的制度化与“制度化自反”[J].行政与法,2024,(1).
[32]王臻荣.治理结构的演变:政府、市场与民间组织的主体间关系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4,(11).
[33]范如国.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14,(4).
[34]Kratochwil F V.Rules,Norms,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35]付建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36]姜士伟.论政府行为规范化[J].行政论坛,2007,(4).
[37]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38]顾昕,方黎明.自愿性与强制性之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嵌入性与可持续性发展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4,(5).
[39]唐亚林.人心政治论[J].理论与改革,2020,(5).
[40]刘睿.群众性与法治化:信访制度改革的张力及其反思[J].政治学研究,2020,(5).
[41]刘明.互联网时代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的若干思考[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8).
[42]仇叶.行政权集中化配置与基层治理转型困境——以县域“多中心工作”模式为分析基础[J].政治学研究,2021,(1).
[43]王印红,郝本良.领导包联制:基层疑难事项治理的逆向发包——基于Q市L区积案化解工作的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3).
[44]丁志刚,于泽慧.论国家制度化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45]李贺楼.信访制度改革中的两难问题:实质与解决方向[J].中国行政管理,2018,(4).
[责任编辑:贾双跃]
From“Brutal Enforcement”to“Rule of Law”: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Embedded Examin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Pang Shangsha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Achieving institutionalized governance is a crucial task in advancing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China.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institutional shift in manag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remains insufficient.Th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the mediation center in District A, City X, demonstrate an institutional shift in manag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structure integration, mechanism proceduralization, and action standard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this shift is influenced by the mass line, political pressure, an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within the macro-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is highlights that the focus on institutionaliz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governance should go beyo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o include the broader institutional context that affects sustainability and performance.
Key words:governance of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the mediation center, “Feng Qiao”experience, social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