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湖东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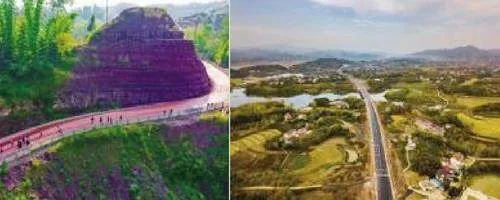
一条城市道路如果驻上一支部队,它跟其他道路又会有什么区别呢?自然的,会多了进进出出的军车,和列队行进的绿色队伍。会时不时传出嘹亮的军号,依着号音,你能准确判定里面一天的起卧作息,进而也随之很有规律地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
在某些特定的日子,会有一波接一波前来慰问的客人,“军民鱼水情”呐,“军地一家亲”呐,形成特别热烈的气氛。会骤然响起震天动地的锣鼓声,“送战友,踏征程……”,空气中飘荡着一遍又一遍催人落泪的《驼铃》曲。
积雪的道路会最先被清扫。营门哨兵威武挺拔的身姿会引来好奇的目光,他们就是用这种无声而又特殊的语言与市民交流,让走过这条道路的人们感到心里踏实。有位老者给部队领导写信:“我在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看了几十年,看到营门哨兵就像看到家人一样亲切。年轻的卫兵就像一棵棵黄山松,是这条路上最美的风景!”
有时,道路交通会暂时封闭。警灯闪闪的前导车引导着长长的车队,一辆接一辆急速驶出营门。运兵车厢低垂的后帘,特种车裹着的炮口,透出一股大战在即的气息。市民们纷纷驻足猜测:“怎么了?这是去演练,还是哪里有情况了?”
一支部队就如一只秤砣,让这条城市道路的长长秤杆儿,陡然增加了分量。还有就是,它会把这条道路的记忆装进许多年轻人的脑海里,带到四面八方,让这条道路在不同地方、用不同口音得到宣扬。而这个记忆也是绿色的。
一支部队与一条道路、一个城市,会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城市学的理论想必不会研究这样的问题,而军人情感学的书目里,却一定会是一个别有兴味的话题。因为,驻扎过的每一条城市道路,最后都像一根根骨头长进了我们的身体里,撑起了我们饱满的军旅生活。它浸着血,包着肉,藏着我们走过的所有日子,以及日子里的风霜雨雪、苦辣酸甜。在暗夜忆起这些道路,就如抚摸自己隆起的胸膛。
所以一条路也是一本军人辞典、一段兵旅日志。走进这些路,就是走进了往昔岁月,走进少有人知的情感世界。恰如犁铧犁开了秋天的田野,深埋的作物从田垄中起出,累累叠叠翻晒在阳光下。一条路不啻就是一个巨大的情感容器。
算起来,我在合肥环湖东路工作的时间有18年!那是一个孩子从出生可以长到成年的时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那段年华。从八楼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向左可以看到大蜀山电视发射塔的尖顶,向右可以望见董铺水库上空的烟云。
现在,我离开那儿已经很多年了,但这条路长长地横亘在记忆中。我想念这条路,尤其想念在八楼一起工作的宣传处同事们。在我任处长的四年多时间里,我们就像家人一样朝夕相伴,亲密相处,共同经历了许多个加班熬夜的艰苦日子,共同完成了许多个值得自豪的重大任务,合心合力取得了一件件漂亮的工作业绩。离开这条路愈久,对他们的思念之情便愈加浓烈。我常常有为他们写一篇《战友颂》的冲动。这是一群平凡而可爱的人。
与我相处时间最长的副处长,在我离开后,接任了处长之职。说起来,还是因为我老不进步,没有早点腾出位置,多多少少耽误了他的进步。每每面对他真诚的笑脸,看到这位当年一头黑发的大学生干部,因不断掉发干脆理成了光头,我的心里总是充满愧疚和自责。好在他当了处长后干得很好,工作上常有创新之举,生活中也不断有喜事传来,家属从异地调进了省城,终于结束了十多年两地分居之苦。
在单位,这位兄弟素有“拼命三郎”之称。我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搭档,会比他配合得更好。那种境界和担当,那种坦率和纯净,那种吃苦的精神、补位的意识,那种敏捷的思维、宽泛的知识面,都堪称副处长的典范。我们俩心气相通,心领神会,合作流畅得犹如在跳一支优美舞曲,这种工作中的过瘾和幸福难以言表。
他干事从不分分内分外,最重的活主动扛,最难的事主动担。跟他,你根本用不着去分派什么任务,因为他早已干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活,而且不光干得漂亮,再苦再累也从无抱怨。记得有段时间连续加班,他劳累过度,在深夜回家的路上,面部受了风寒,造成面瘫,整个脸扭曲变形,看了十分吓人。在医院里住了几天,没等痊愈,他就回到办公室投入工作,怎么赶都赶不走。他说:“处里任务重,多个人多份力量,我现在身体不碍事了,注意一点儿就行了。”这股犟劲,真让人又心疼又无奈。
我们俩密切协作,连续四年组织总队参赛选手参加武警部队“四会”优秀政治教员比赛夺得“十佳”,两次承办武警部队教育试点和军师职领导干部理论读书班,创造了许多总队历史上的第一。这是一段干起来激情燃烧、想起来心潮澎湃的难忘岁月。小小的宣传处就像一个偌大的绿茵场,我们拼命奔跑冲杀,享受着射门的快乐,挥洒着青春的豪情,忘记了时光的流逝。
当我来到新单位时,我常常在想,我要当一个怎样的领导干部,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位兄弟给我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一个集体里,我们都曾作过部属,也可能会成为某些同志的领导。部属和领导,相互成全,也相互影响。一个好的部属就像一本教科书,能够教会你许多东西。不但让你更加自信地开展领导工作,有底气面对各种困难挑战,而且能够让你反躬自省,净化心灵,从这面好的镜子中看到自身不足,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对得起“领导”这个称呼。所以我总认为,与其说领导培养了部属,还不如说是部属托起了领导。离开部属的支持,我们能做的其实很有限。
还有一位处里的小兄弟,我们相识十分偶然。那时我还任新闻站站长,一天,有位戴学员牌的黑脸小伙推开我的房门,自我介绍是某单位的新闻报道员,考入合肥指挥学校,想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到站里实习,恳请给个机会。我奇怪地问:“好不容易放个假,你为什么不回家呢?”他踌躇片刻,告诉我实情:“父母都去世了,只有一个哥哥远在广东打工,暑假没地方去了。”我心里一震,就报告首长把他留了下来。
将近一个月,他就睡在办公室。每天工作分外勤快,更让人满意的是,写的稿子也像模像样。他的到来,让我们多了一份新闻报道力量,少了许多工作上的压力。我打心眼里喜欢上这个勤奋朴实的农家子弟,在他毕业时想方设法把他挖了过来。成为宣传干事后,他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紧接着又考取了计算机二级、中级人力资源师和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每个假日,不是去图书馆学习,就是到附近的大学蹭课旁听。
有一次“五一”假日,我见他报的休假去向是金寨,好奇地问他:“你在金寨还有亲戚吗?怎么从没有听你说过啊。”经不住我的一再询问,不会撒谎的他吐露了真言。原来他在结对帮助一名家庭贫困的孩子,平时每月寄几百块钱,放假时就赶过去谈谈心、辅导功课,这样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看着他厚厚的嘴唇,突然觉得眼前这个熟悉的青年,变得陌生又高大起来。
每个部属都像一本书,看起来熟悉的封面,打开来读,却越读越深邃。2015年,他去安庆执行抗洪抢险任务,又悄悄结对了两名当地贫困家庭的孩子,每月从工资中挤出几百元资助他们,几年来从不间断。他自己,不抽烟,不讲究穿着,靠工资养活一儿一女,一家四口活得知足而快乐。
我经常在思考,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幸福的生活?这些终极的人生问题,在我的这位小兄弟身上,能够找到很好的答案。我很高兴地得知他被评为“安徽好人”,家属被评为武警部队“十佳军嫂”。我为曾有这样一位战友、同事而感到光荣和骄傲。
如今,这些同事大多也离开了宣传处。有的走上了师团职领导岗位,有的转业到地方工作。一起奋斗的日子,成为历史,化为记忆。有次我梦见自己又回到环湖东路,回到那个熟悉的八楼,与宣传处的同事们一起挑灯夜战,为一篇稿件撰写唇枪舌剑,为一项紧急任务摩拳擦掌,错过饭点就举行方便面“会餐”,工作累了就拼上桌子痛痛快快地打上一场“掼蛋”……
人生的路百转千回,每个人的路都独一无二,无可替代,不可复制。我们就是这样带着浓浓的战友情谊,走过一条条城市道路,从冬春走到夏秋,从过去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