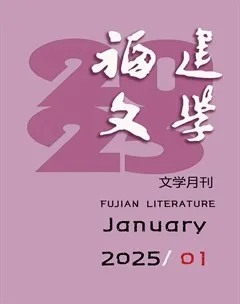建西小火车
我沿着枕木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这条南方最长的森林小铁轨复建了一段,从贮木场到林业中学,一段1.7公里的小铁轨穿过镇区壕沟,重现在眼前。
枕木像一把平放的梯子,向着远方延展。
深入大山的小铁轨,曾经是森林小火车驰骋的疆场。
在大埠岭中心,人们挖出了一条深深的壕沟,在壕沟里铺设小铁轨,以便小火车径直穿过。壕沟上架设一座高高的拱桥,锁着一分为二的山岭。两条小铁轨安静地卧着,静候小火车的来来去去。沟上一茬一茬的房子生长了出来,直至小铁轨被密匝匝的楼房俯视。有些村民站在自家的房顶,就可俯瞰壕沟里小铁轨的全貌。在那火热的年代,这条小铁轨从不曾冷清过,小火车一列接一列,呜呜的汽笛声,哐哐的轮轨相击声,不绝于耳。林区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聒噪,他们笑谈:“晚上睡觉最好的催眠曲,就是小火车的汽笛声与钢铁撞击声的合奏。”
30年后的今天,小铁轨只剩下空荡荡的路基。沟坡上的野草丛和小竹丛,或许它们长久盼不来小火车,便暗中较劲,一个个默不作声地扩张自己的地盘。沟上人家的屋脚也偷偷地侵占过来,我想,若再过几十年荒芜,壕沟里就要被站满的屋脚遮盖得暗无天日了。
站在壕沟里,恍惚间,就像寂静的黑暗的舞台,强光亮起,音乐声响起,锃亮的小铁轨突然又出现了,沟上人家侵占轨道的屋脚不好意思地缩了缩;沟坡上的野草、竹丛探出头来,用微弱的心跳感应我的心跳;草丛里不知名的不断鸣叫的虫子、翻飞的蝴蝶被我的脚步声惊动,扑腾着从一处跳飞到另一处。
四周阒寂。崭新的小铁轨即将等来崭新的小火车。
时光倒带回去,我还是那个7岁的小男孩,渴望着一次小火车远途。
1
我搬把靠背小椅子,坐在建西森铁处山头宿舍的最高处,俯瞰山脚下的森铁处和大埠岭车站。大埠岭车站,是个开放式的车站,铁轨旁有一座“铁路制式”青砖红瓦房子,是车务处办公室,有个卖票的窗口。曾经有个候车室,因在铁轨下方,人们大多选择或蹲或站在铁轨旁场地等车,不久,这个候车室隔成小间用作职工宿舍了。
我的眼睛盯着看那一节节、一列列的车厢进进出出,编组作业,一派繁忙却井然有序。小铁轨从深山出来,穿过壕沟后在大埠岭车站散开七股轨道作业线,然后又合拢成伸向不远处的贮木场,贮木场枵场有接鹰厦铁路的大铁专用线。从壕沟钻出来的可能是一节节满载着伐木场砍伐的木材、蛇纹石矿开采的矿石的平板车、矿斗车,它们像一条黑龙,吐着浓浓的长烟,直接奔向贮木场。而在清晨或黄昏,钻进或钻出的就会有耀人眼的绿皮小客车厢。傍晚时分,“呜呜呜”随着汽笛声响,我终于等到一条绿色长龙从大埠岭的腹部钻出来,它们身后挂着5节绿色的客车厢,1节平板车,1节行李车。小火车缓慢地在大埠岭车站停稳后,便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从车厢蜂拥而出。绿皮小火车在不通公路的年代,是大山深处沿线伐木工人、铁路职工和林区的人出行的唯一交通工具。
我在人群中搜寻母亲的身影。母亲是小火车上的列车员,每天都要上班。小火车每日往返一趟,母亲早上6点出发,傍晚6点才能到家。我被托付给外婆照看,就这样天天坐在小椅子上等待母亲回家。
那年夏天我已经7岁了,每天看着车站热闹的景象,生出坐一趟小火车、来一次远途的渴望。但不管如何软磨硬泡,母亲就是不同意我跟着去坐一趟小火车。
初夏的一天清晨,母亲出门后,一夜警醒的我也悄悄起床,跟在母亲身后。我心想,母亲不让跟着,大不了自己买张票。当时的车票从1角5分到8角不等,大埠岭车站到终点七道车站票价8角钱,我事先已偷偷攒好了钱。此时是凌晨5点多,朦胧晨色中,急着赶时间的母亲并未发现身后的我。
一会儿工夫来到车站。母亲进了车务处,我站在外面,抬眼望去,车站人山人海,挤满或站或坐焦急等车的乘客。
当我从乘客的交谈声中得知当天恰逢是大历镇五天一次的传统赶圩日,乘车的旅客比平时增加了好几倍,顿时蒙了。
我一路小跑着直奔售票窗口,刚走过去,大吃一惊。只见售票窗口外人头攒动,买票的队伍排成一条长龙。吵嚷声、尖叫声、抱怨声此起彼伏。
小小的我排在队伍的最后面,长长的队伍缓缓地前移,我时不时探头往前观望,喃喃自语:“咋这么慢呀,咋这么慢呀,要赶不上了呀!”
我抓耳挠腮,身子扭来扭去,四处张望。
正在这时,眼尖的我看见一位在拥挤的人群里不停迂回穿梭的人,兴奋地大叫一声“张叔叔”。张伟叔叔是小火车副司机,上海人,和我父亲的关系好。他听见叫声,转身看到我,挤出人群,朝我走过来,“你怎么在这里?”“张叔叔,您能不能把我捎到车上?不要告诉我妈妈。”张伟叔叔看到我焦急渴望的眼神,秒懂我的意思,“跟我来。”
此时,一条绿色的长龙已整装待发静卧在铁轨上。那车头黑黝黝的,上面的路徽是变形的“森”字,含义为“森工”或是“森林铁路”。突然小火车发出“呜”的一声巨响,这声音穿透力太强了,清脆震耳。
小火车7点整出发,上车的时间到了。安静的站台顿时热闹起来,乘客在列车员的指挥下从各节车厢的入口持票涌入。碰上赶集,提着或挑着土产山货的村民很多,大的行李放在行李车上,有些小点的鸡笼、鸭笼什么的,村民遮掩着偷偷往上带,什么味道都有。
我跟着张伟叔叔突破重围,也挤上了车。一进车厢就感觉到十分的压抑,车上的人越来越多,车厢里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空气闷得要死。挤进人群,身体便不由自主地随着人群移动。车厢已经严重超员了,窄小的过道上,人们摩肩接踵,挤得跟黏豆包似的,里面充满了各种味道和声音。我吃力地向车厢中部挤去,每挪动一步都无比艰难。突然看到一个空位,我兴奋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坐下去。
随着悠远的汽笛声响起,哐当哐当,轰隆轰隆,小火车缓慢平稳地驶离站台,驶出大埠岭。
正在这时,前面车厢不远处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我下意识地抬眼,只见车厢接口处缓缓走过来一位好看的阿姨,手里还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她们走到我的跟前。
我起身让座,并帮助阿姨把身上的背包放到座位上。小女孩圆嘟嘟的脸,一双眼睛像黑葡萄一样晶莹透亮,此时正静静地看着我。我注意到小女孩手上拿着一把竹子制作的精巧的小凳子,凳子腿上还系了个红色的小蝴蝶结,她把小凳子放在母亲脚下,就安静地坐下。这让我非常羡慕,想着以后也要让父亲做一把这样小巧的竹凳子。
阿姨看我紧盯着小凳子,就抱起女儿,把小凳子递给我,示意给我坐。我说,阿姨,不用。但阿姨坚持把小凳子递给我,我只好接过来,坐在小凳子上。
坐在小凳子上,看不到窗外的景色,我又站起来,身子紧紧靠着阿姨座位靠背,脱下鞋子站在凳子上,以便看清窗外。第一次出远门,我兴奋又期待,紧张又焦虑,孤独又无聊。站在拥挤的过道上,左瞅瞅,右看看,四下张望。
我看见阿姨在小餐板上摆放着一只白色陶瓷茶杯,杯身刻着“建西森铁赠,一九七二”两行醒目的楷体大红字,瞬间引起了我的好奇。听美丽阿姨和邻座聊天,我才知道原来她是插队到闽北的上海知青,在岚下中心小学当代课老师。老公在建西森铁处工作,夫妻两地分居,天各一方,昨天恰逢两人结婚周年纪念日,于是就特意带着女儿来建西探亲,今天必须返回。
我在旁边专注地倾听,听得一脸神往,虽然他们好似牛郎织女难得相会,但言语间听得出他们感情好。
小火车开足马力,不间断地加速,一股又一股的凉风不时从车窗外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咔嚓,咔嚓”,车轮驶过铁轨的缝隙,发出音乐般的颤声。小火车穿过一片绿树林,顿时车厢漆黑一片。小火车晃晃悠悠开动,如同一个超大的摇篮,起早的人们难免昏昏欲睡。
小火车沿着山路盘旋向前,一会儿在山脚下,一会儿又在山谷中,远眺似被山峰挡道,驰近又豁然开阔。不经意间就钻进了绵延的大山。这里人迹罕至,显得格外幽静。过了安下村、下坑村两个站,小火车即将进入大历车站,火车头骤然响起震耳欲聋的鸣笛声,仿佛号角吹响般划过天际。
距离站台一箭之遥,火车司机紧急刹车减速。这当儿,司机打开车门快速跳下车,行动敏捷地跳上车头跟车厢的交接处,动作麻利地打开车头连接车厢的挂钩。随着惯性,脱挂的五节绿皮车厢缓缓地滑进了大历车站,完美地停靠在站台上。
大历车站有岔路,一路去岚下,一路去高阳方向。大历车站是建西连接岚下、高阳方向的中转站。支线逢双开一班客车,在大历口站分岔,从大历口站至岚下、夏墩、连墩站点,而后折返到大历口站,再由从正线返回的客车机头重新编组后,一并回到大埠岭车站。
大历车站一下子下去了很多乘客,使得原本拥挤的车厢如同泄了气的皮球,立马显得空旷了许多。我恋恋不舍地看着阿姨和小女孩下车,阿姨说把小凳子留给我,我推辞不了,小凳子就留在我身边了。小女孩下车前回头看了我和小凳子一眼,那眼神让我难忘。
小火车车厢像电影里看到的绿皮大火车一样,有座椅、行李架、窗户,只是车厢略显小了点,座位小,过道窄,没有座位号,没有餐厅,也没有卫生间。人们上卫生间必须等到大点的站,下车到车站的厕所解决。路上小车站到下一个车站的时间往往只有半个小时,甚至只有10—20分钟就到站了。小火车有点像以前的班车、现在的公交车,乘车的人上上下下,因为车票没有座位号,上车有空位就坐下,没位置就站着。
小火车在大历站停留大约20分钟,这期间,车头掉头变道,车厢重组整合,一连串连贯性规范动作操作完毕,小火车静卧站台等待出发。
我下车上了趟厕所,上车找了个空位坐下,把小凳子藏到座位下。闲来无事,把头转向窗外,形形色色的人在站台上忙碌着。戴着红袖章,拿着小红旗,口里含着哨子指挥乘客的工作人员,喘息着从楼道口急匆匆出来赶车的人,蹲在站台上抽旱烟解瘾解闷的闲人。站台上,一帮身材魁梧的森林工人正将工作器具装到平板车上,或许他们是要到深山里施工。一个比我略小的鼻涕虫小男孩,挣扎着挤出围观人群,抬头呆呆望着我,任由鼻涕拉成一条晶莹长线,也许他正在羡慕坐在车上的我。我们这里十里八乡流传着“高阳杉,岚下笋,大历蔗糖最有名”,因此大历站有很多农民将甘蔗削好,截成一尺多长蔗段,装入木制勾桶,“一段一角钱”地叫卖。我口袋虽有八角钱,那是我积攒来的压岁钱,不舍得用,只能咽下口水。
不知不觉中时间到点,列车员吹着哨子提醒大家上车。随着小火车一声鸣笛,还未上车或到车厢外休息的人们一拥而上,嘈杂热闹地开往下一站。
车轮一动,风就徐徐从车窗外吹进来,瞬间感觉如同妈妈温柔的手轻抚着我的脸庞,真是美妙极了,舒服极了。
小火车在山林间穿梭,在群山之间绕行。车头顶上的烟囱时不时蹿起一根根黑色气柱,随风飘散在空中。这当儿,车身下面不间断地暴射出一道道浓郁滚烫的烟雾气流,吹得路边的树木东倒西歪,像要被连根拔起来似的,那场面十分的壮观,也着实让我吓了一大跳。
转眼间,眼前就是大武岭隧道。说时迟那时快,火车头“呜”的一声钻进了隧道,像个潜水员扑通一声猛地扎进黑暗的深海里,憋了老半天又从另一头慢慢地钻了出来。
车厢里没有安装电灯,经过隧道要十几分钟的时间。暗黑的车厢里,就有一位工人师傅拿着一个大大的手电筒,站在车头,打出一束长长的强光,穿透一列长车厢。
滚滚浓烟在隧道飘散不出,空气中细小的煤渣粉尘打在脸上生痛,一粒粉尘吹进我的眼睛,我难受得流出了眼泪。
小火车像个迟钝的赖猴,慢吞吞地停靠在大武岭隧道洞口绿荫下等待加水,车头裸露在洞口外面,车厢隐藏在隧道里,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当儿,火车头底盘下面不停地排泄出燃烧未尽的滚烫煤渣。
大约过去一袋烟工夫,小火车添加了燃料,加水完毕。
汽笛声呜呜响起,小火车缓缓启动,微风过处,山花飘飘。
加水处有个小站。我把座位让给旁边刚上车的一位大爷,我对大爷说:“爷爷,您来坐吧。”大爷眉开眼笑地说:“谢谢你了,小伙子!境界噌噌升华,车厢顶都挡不住了。”
话音未落,逗得车厢里的人哄堂大笑,大爷幽默的玩笑话羞得我满脸通红。
我探出车窗看车头,车头就像一只大黑狗,长长的铁轨就像一根油光发亮的硬骨头。小火车很快驶进一片峻岭密林,这里群峰耸立,林木葱茏,偶尔还能看到清澈的溪流和山间的小屋。前面是一段上坡路,上一秒还牛气冲天的蒸汽小火车,下一秒车速锐减,如一条扭动的黑鱼挣扎着往上蹦。火车头吃力地喘着粗气,车头顶上愤怒地吐着发亮的火星,冒着滚滚的浓烟。
没过多久,小火车如同蜗牛爬行,每爬行两步倒退一步,每爬行三步倒退两步。
我在心里为小火车使劲,真是恨铁不成钢,站在车上干瞪眼。
穿过一山又一山,爬过一坡又一坡。
终于听到列车员沙哑地播报七道到站。当时小火车没有播音喇叭,报站靠列车员播报。不知不觉小火车已停在七道终点站。此时大约正午12点,在七道车站停留一小时后,小火车将折返大埠岭车站。
七道车站比大历车站还热闹,站在车站看村民叫卖馒头、油饼、芋粿等食品,我的小肚子也禁不住咕咕咕地叫起来。在车上我一直躲着母亲,只要母亲过来车厢巡视查票或让中途上车的乘客买票,我就蹲下来躲在大人身后。大人们看到我的举动,以为我没钱买票,都有意无意地掩护。我长得瘦小,忙于工作的母亲没发现我。此时我故意现身,让母亲发现,母亲大吃一惊,狠狠批评我一顿。那天中午,母亲给我买了馒头和油饼,让我喜出望外。这些食物平时她是不舍得买的。计划经济年代粮食紧张,食品都要用钱和粮票才能买得到,馒头5分钱2两粮票,油饼1角钱1两粮票,芋粿7分钱1两粮票。
那把绑着蝴蝶结的小竹凳子,我珍藏着,散架了也不舍得扔。那个小女孩,我也没再见到,我总想她是不是回上海读书了。
2
不知从哪日起,森林小铁轨一段一段被拆除,直至全部消失。起初看到一段铁轨被拆除,我们心中是震惊的,不可接受的。父亲回家发牢骚,这些败家子,不是自己亲手修建的,不知道心疼!可是钝刀割肉、文火煎心,慢慢地大家似乎都麻木了,直至全线拆除,林区人都默不作声。但从小铁轨被全线拆除后,父亲突然有了傍晚散步的习惯。每到傍晚时分,父亲就沿着鸬鹚溪旁原先的小铁轨路基,慢慢踱步到鹰厦铁路建西火车站。我喜欢陪在父亲身后,看着父亲走一段停一段,四下望着,不时陷入沉思。有一次父亲给我讲故事,说从前这里山上树木密集,一只闯进去的狗被活活夹死。我还没见过那样茂密的树林,枝丫纵横交错,藤蔓攀缘而上,蜘蛛网一样在林中缠绕,每前行一步都要费老大劲。
我们走过贮木场,来到鸬鹚溪口。弯弯绕绕的鸬鹚溪终于从这里流入富屯溪。在此,鹰厦铁路建桥跨溪而过。铁路桥下,鸬鹚溪口东岸,富屯溪绕出个小小的河湾,一座小庙——白马寺立于一侧。在大、小火车没有开通之前,这里是捎排的码头,主要是水运木材和毛竹,木排既是运输工具,也是运输对象。
我和父亲顺坡走进那座破旧的白马寺小庙,小庙勾起了父亲的回忆。父亲陆陆续续和我说起往事。我从父亲那有一搭没一搭的话语中梳理着他的故事。
1958年初,年轻的父亲从富屯溪下游对岸的南平市峡阳镇江汜村被派来支援建西林区建设,被安排在林业工程队。其年,“中央林业部建瓯西部林区筹备处”(简称“建西林区筹备处”)成立,准备开发鸬鹚溪、高阳溪流域的森林资源。同年,建西林区筹备处18名干部、医生进驻大埠岭,成为开发建西林区的第一户。林区中心设在鸬鹚溪畔的大埠岭上,“大埠岭”是一座距离鸬鹚口村2公里的小山丘。
父亲来到鸬鹚口村报到时,筹备处工作人员就居住在鸬鹚口村的这座小庙里,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厨房。父亲和其他附近村子被派来支援林区、熟悉当地的林业工程队员,和“林区第一户”一起开始动手割茅草、砍毛竹搭工棚,用茅草盖棚顶,在竹棚上糊上黄泥巴挡风寒。没有床,把毛竹剖成两半,平铺开来当作床板,铺上稻草就是暖和的床。最先在丘顶上搭了筹备处的办公室、宿舍和食堂3幢简易茅草平房。
后来陆续迎来了福建沿海县(市)和上海、山东、安徽等地一批支援林区建设的知识青年和农民。第一批上海知青们报到后被立即组织起来,和工程队工人一起上山砍毛竹、割茅草,忙到天黑才建好临时简易茅草宿舍。父亲教知青如何砍毛竹割茅草,以及如何生火烧水煮饭。当时条件很是艰苦,晚上蚊子、白天小黑虫,骚扰成害,大家睡不安稳,食不定时,有些青年水土不服,染上疟疾,病情严重的,只能离开。
沿着大铁轨前行,不一会儿我们来到建西火车站,父亲望着北上的铁轨,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知道,父亲在这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战友,他在怀念着他们。父亲说,有一段时间,这里每天都有一趟上海始发的绿皮专列停下,“上海支闽林工”经过历时两天两夜的车程,抵达建西,之后就被分配到林区各地。当时筹备处分配给父亲的任务,就是每天来火车站迎接这些支闽林工。父亲悉心照顾这些刚离开大城市、奔向大山而来的年轻人,帮助他们尽早适应深山生活。这其中很多人都和父亲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其中就有我称为“上海叔叔”、特别疼爱我的张伟叔叔。张伟叔叔告诉过我,当初刚18岁的他来大埠岭的第一个晚上,睡不着觉,走到草棚外掉眼泪,黑暗中父亲走向他,塞给他一个烤熟的土豆,虽然父亲什么话也没说,但他一下子感觉温暖,就擦干眼泪回草棚睡觉了。我记得我们家只要有什么好吃的,父亲总会叫上张伟叔叔。下河捞到大点的鱼,父亲就让我去叫张伟叔叔来喝鱼汤。秋天采到鲜蘑菇,父亲就会把偷偷养在菜地篱笆里的大公鸡杀了,炖上一锅鲜美的鸡汤,也一定会叫上张伟叔叔。冬天时,即使只是在家里炸一锅油饼打打牙祭,也是要叫上张伟叔叔的。张伟叔叔也特别疼爱我们家孩子,每次从上海探亲回来,总会带回来一大袋泡泡糖给我们。这在当时的大山里是稀奇物,给我们带来大大的惊喜,我在上学路上边走边神气地吹着泡泡糖,让同学们羡慕得眼睛都看直了。有同学出钱向我买,最后出到一颗5角钱,我小小地挣了一笔。
当铁道兵X部队一批官兵和技术人员志愿队伍随后赶来时,这个山丘就变得热闹非凡,森林小铁轨也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建设。
也是在1958那年深秋,父亲站在数千名铁道兵战士和林业工程队职工队伍中,参加森林小铁轨施工。施工时,父亲他们随身只带着饭团,饿了就吃冷饭团,口渴了就喝一口山涧水。当时机械设备很少,他们需要用斧头砍树,用柴刀砍毛竹,用锄头挖土石,用土箕挑土。在日复一日的跋山涉水中,父亲的鞋子破了,用布带绑一绑,继续穿;肩膀磨出血,继续挑,血把衣服黏在肉里,晚上脱衣服时,父亲先用热毛巾捂住肩膀上的衣服,软化衣服,再慢慢脱,还是忍不住连连倒吸凉气。建西林区森林小火车,1958年开工,至1964年才全部竣工、全线通车。他们就是这样用鲜血和汗水硬是在林区的崇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便捷的木材通道。我想父亲的高低肩,就是在小铁路建设中落下的,日复一日的肩挑背扛,让父亲的右肩斜了下去,从此再也没挺立起来。后来的日子,瘦弱的父亲就这样微微倾斜着肩膀为工作、为生活忙进忙出。
总长142.66公里的森铁建设用了整整6年时间,1960年开始陆续营运。“森林小火车”,这个“呜呜叫”的林区运输骄子,带来了建西一个短暂的辉煌时代。
1964年初开始有传闻在林区秘密流传,刺激着人们兴奋的神经。人们用压低的声音在传一件件极其神秘极其重大的传闻。关于电影《青山恋》的拍摄公映,关于建西林区将要建县的决定,都让人们兴奋不已。《青山恋》讲述了一群上海知识青年来到建西参加林区建设、成长的故事,当时在建西林区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剧本改编、取景拍摄,于1963年底杀青,1964年在全国热播。张伟叔叔得意地和我说,当时拍摄《青山恋》时,有一场戏是英姿飒爽的女主角徐英开着小火车运输木材,正巧碰到了想要做逃兵的男友寄望,这一幕是有过加工的。建西的蒸汽小火车,必须有3个人同时进行才能启动,司炉、副司机,还有司机。所以剧中的徐英其实并没有驾驶小火车,而是剧组找来了两位身形相似的男司机拍摄后,进行剪接。这两位司机之一就有张伟叔叔。张伟叔叔感叹,在上海20多年,都没看见本土名导演赵丹,如今却在这深山里遇到了。
果然,在一场又一场传闻风暴过后,1964年建西林区真的建县了。而且与大兴安岭一样,获批铺设300多公里的小火车路,这在全国仅有大兴安岭和建西林区。这之后建西林区就有了“林海新城”的称号。这又成了林区人骄傲地宣扬的一件大事。听着张伟叔叔眉飞色舞的讲述,我被感染,自豪地抱着张伟叔叔转圈圈。在我心里,从大上海来的张伟叔叔就像神话里的英雄,在大山里开疆辟土。
后来张伟叔叔要回上海了,我们都为张伟叔叔能回家乡高兴。张伟叔叔离开那天,我们全家一起送张伟叔叔到大火车站,张伟叔叔一步一回头地上了火车,我看到父亲笑着挥手和车窗里的张伟叔叔道别,看着渐渐远去的火车,眼眶红了。
3
在我们家的一个上锁的抽屉里,珍藏着母亲售票后对账用的小火车车票票头。能当上一名小火车上的列车员,是母亲一生为之自豪的事。
18岁的时候,她还是鸬鹚村际头自然村里胆小羞涩的姑娘,上过两年小学的她已经看到了鸬鹚河畔翻天覆地的变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山外面世界的精彩,她的目光被深山里正在修建的森林小铁路牵引。1960年经人介绍,她嫁给了在建西工程队当工人的我的父亲。
建西始建,随着森林小铁路的建成使用,一个个林业系统单位成立。工程队要做的事可多了,一座座苏式风格建筑陆续在山岭上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地修建。这座以林业为标志的新县城到处都有林业的印记,贮木场、林机厂、森林铁管处、林业招待所、森工医院、林建路、森铁路。山丘上小小的县城呈“毛”字型排开,密密麻麻地挤满银行、邮局、学校、医院、电影院、体育场等机关单位。每个单位都有围墙,都有一个铁板大门,形成一个个的“包围圈”,这也是建西城区别于其他老县城的特点之一。
父母结婚时,住的是茅草棚,只有一张单位分配的竹片床和一张木桌子,这样的条件甚至不如当时的农村。
但是母亲被心中的信仰和热情鼓舞,参加工作的热情高涨,先是在林业局工会图书馆上班,后来森铁处客运小火车通车,又当上了客运小火车的列车员,这一干就干了一辈子,直到小火车停运。至今母亲还清晰地记得大埠岭车站至七道车站各个小车站的票价。
彼时父亲也调到森铁处小火车站工作,当现场员,负责管理下面各车站的木头小票和矿石的小票。木头、矿石从里面各站运到建西车站的时候,车长就把木头和矿石的小票交给现场员,父亲查验无误后,再按时和贮木场签收组办公室交接。小火车将木材从深山运到贮木场,再由大火车转运出山。
森铁处“山头”职工宿舍大都是一层一间半的房子,一间大点的是卧室,另半间是厨房,我们一家8口人就住在这一间半屋子里,父亲将厨房往外延伸出两个小间,还将屋外芦苇丛开荒出来种菜,家里孩子多,住房、用度都紧张。
从前孩子多,大人要上班,孩子是放养着长大的。那时的建西,不管是山上还是小河里,到处都有孩子顽皮的身影。我记得有一个深夜,父母回来后,在床尾摸着孩子们的脚数着,这是父母每晚的习惯。当时人们下班后常常还要开会学习,晚上回来孩子们都已上床睡觉,数数孩子的脚,就知道孩子有没有全部回家。其实那晚哥哥贪玩,半夜才回来,也许父母太疲劳,没有发现脚数不对,就把门从里面闩上了。哥哥回来后怕父母责骂,不敢敲门,就缩在门边,在寒冷的夜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外婆早起做饭,一开门吓了一大跳。虽然皮实的哥哥被父亲痛打了一顿,骂他小兔崽子,冻不死你,但后来父亲夜里就不再闩门了。
大人们禁止孩子们在小火车开来时在铁轨旁玩耍,但是小火车一来,森铁处的孩子们还是蜂拥着跟在小火车后面,甚至爬上尾车一路跟随到贮木场。木头一卸下,他们不顾贮木场工人师傅的驱赶,等不及工人师傅扒树皮(木材要扒完树皮再装运),就爬上随时可能摇晃滚动的木头堆,抢先用锉刀剥树皮,高高兴兴拖回家当柴火烧。
记得还有一次,一列从山里运输出来、整整一节平板车都是用麻袋装着的地瓜米,停靠在车站,准备第二天转运出去。这一夜工夫,我不想否认,在夜色的掩护下,我加入了一支“小老鼠”队伍,窸窸窣窣把那列平板车上的麻袋用锉刀或削铅笔的小刀挖出一个个大洞,把地瓜米掏出来直接塞嘴里吃,并装满了口袋和书包。一直到上夜班回来的工人叔叔晃着手电大喝一声,我们才惊慌地四下逃窜。
第二天早上,车站负责人看到一片狼藉,叹息一声,处理好地瓜米客户的追责,没有追究孩子们的过错。
上中学后,由于家和林业中学分布在镇子的两侧,我和伙伴们经常穿壕沟走铁轨去上学。如果碰上进山拉木材或矿石的小火车经过,我们会跳上车尾,扒个顺风车,当小火车行驶到学校的路口时,便会熟练地跳下来。我们身轻如燕,好像铁道游击队,活跃在铁轨上。
建西县昙花一现,建县6年后撤销了,并入顺昌县,成为林业文化小镇。现在进入建西小镇的山口路基按国道标准降低拓宽,不再高高低低颠簸,宽阔顺畅。小镇镇口三岔路的三角区,建设有火车头广场,花草树木簇拥中,森林小火车雕塑高昂着火车头,在蓝天下耸立着,车头下的基座雕刻着四个红色大字“林海建西”,分外醒目。
来到老贮木场工人俱乐部广场,森林小火车站台已人头攒动,大家有序排队检票,体验“大埠岭—幸福里”小列车再次出发。我看到很多游客在独具年代感的站台和铁轨上拍照打卡、合影留念。这列崭新的绿皮小火车,火车头后是一节装满杉木的平板车,随后是两节客车厢。我随着人流进入崭新的车厢,空气里散发着好闻的木头香味,车厢相比从前的小火车更美观舒适。一声汽笛缓缓启动,我坐在车上,耳听着车厢里着装整齐的服务员叫卖着“花生、瓜子、爆米花、可乐、矿泉水”。终究还是不一样了。窗外的绿色一闪一闪地晃过去,窗外的楼房一晃一晃地老去。啾啾的鸟鸣声,在时光的两端有着一样的清脆鲜亮。
当小火车行驶在小镇壕沟时,迎面看到鸬鹚村拱桥,我把手机伸出窗口,拍下了拱桥上依然存在的四个红色大字“林海新城”。
责任编辑 韦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