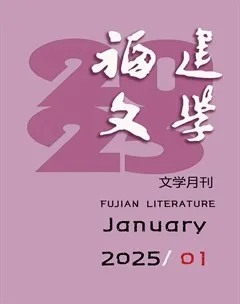苏轼上乞
乞,乞求也。语气中带着卑微。苏轼这样一个才气纵横、气节高洁的人,在面对左右人生命运的皇帝那里,也一样要乞求的。当然,他的乞求一点都不“奴颜婢膝”,相反,苏轼的上书乞求浸透着他的风格和气节,也洋溢着他独特的思想及人格魅力,展示出他的执政理念和为国为民情怀。从苏轼文集看,第一次直接用“乞”开头上表的是《乞医疗病囚状》,后有《乞常州居住表》《乞罢登州榷盐状》《乞赐州学书板状》《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等。苏轼上乞大抵分为以下四类,一是为自己职位去留的恳请,二是为他人的请呈,三是为百姓民生福祉的呈谏,四是制度建设或治国策略等。苏轼的“上乞”,才气、胸襟、格局、情怀、思想跃然纸上。
愿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
《乞常州居住表》算是苏轼为自己的去留上的一道折子。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又因黄州坐废五年。朝廷在政权更替中,才想起苏轼“人材实难,弗忍终弃”,于元丰七年(1084)四月,诰下黄州,授苏轼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从嘉祐元年(1056)苏轼入京,举进士试及第,名满京城,国士待之算起,到诰下移置汝州,已过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时间里,苏轼经历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也经历了昏暗与无助的岁月。苏轼上乞的开头那句,虽说套话,却也是磨难后的至理名句:“臣闻圣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虽甚,而归于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谴子孙,鞭挞甚严,而不忍致之死。”雷霆、鞭挞,都“欲其生、不忍致其死”,何况苏轼已漂流弃物,枯槁余生。“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二十几口人无居无食,怎么生活下去呢?苏轼只好乞求皇帝准许其常州居住。为了得到皇帝的许可,苏轼还说“罪戾之余,稍获全济,则捐躯论报,有死不回”“至南京以来听候指挥”。在生死未卜面前,在饥寒无助面前,苏轼的上乞,读来情真意切。朝廷准许了苏轼的请求。
此身已觉都无事,但在朝廷的更替中,像苏轼这样的大文人,不会只身安于薄田耕作的,历史终究会将他推到更显赫的位置,让他在风云变幻中书写人生的篇章。元丰八年(1085),苏轼复官朝奉郎,后回京,名为礼部员外郎,寻迁起居舍人。越明年,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改赐银绯,寻迁中书舍人。元祐二年(1087),命兼侍读,苏轼、苏辙同侍迩英殿讲读,以其学识、思想、政见,培养幼主,让己见成为而后皇帝亲政、施政之策略。后又权知礼部贡学,主省试,“坐阅诸公半廊庙,时看黄色起天庭”,“半年之间,擢臣为两制之首”。从黄州以来,自己的仕途就像过山车似的,从低谷中崛起,但能不能享晚节闲适之乐呢?身在高处,高处不胜寒。耿直的苏轼,越是在中枢,越是招来嫉妒,也是得罪于人。时苏轼因台谏,与洛学弟子、司马门下官僚等政见不一,发生冲突。上下相忌,身不自安,于是苏轼上《乞郡札子》,希望求外一郡,以远中枢,避怨仇,得安宁。
郡县治,天下安。历朝历代,都视郡县为治理之根基,也是官员为民情怀最好的试验田。不过,《乞郡札子》一文侧重讲述自己是如何忠诚于朝廷,又是如何招致诽谤的。为了不至于诽谤累积,希望皇帝能给一郡,措之不争之地,保全自我。宋之党争,历来明显,层出不穷。熙宁、元祐间都兴盛朝野,你唱罢我登场成为常态。至苏轼显赫朝廷时,就有三个主要派系:一是司马门下官僚集团,人称朔派;二是以洛学程之为主的洛派;三是籍属西南的朝士,即蜀派。苏轼也自然成了蜀派的领袖。各派之间相互讥讽,甚至诽谤,想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只是这其中有程度的差别。比如苏轼平时对程颐就相当厌恶,司马光去世时,由程颐主祭,一切遵行古礼。苏轼见程颐用锦绸做囊,把遗体装在囊中为敛。苏轼看不过去,就指着锦囊说,还欠一物,当写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程颐听后,气急败坏,认为苏轼戏谑了他。苏轼确有笑戏的性格,说幽默也罢,说戏弄也罢,但凡才气者,偶有幽默调侃,在别人看来,就语涉讥讪了。这大抵是他的性格所致,但就苏轼的品行而言,他还没有置人于死地的阴谋。在这样的环境中,苏轼选择求一郡,远离中枢,保全自我,大体也体现了宋朝文人的致仕情怀。在多次乞求外放后,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授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开始了他二度仕杭州的外放岁月。
苏轼勤勉于工作,与百姓息息相通,不管是在什么位置上,都把百姓放心间,多做惠及百姓的事,这是他为官之道的根本。就从他知杭州可以看出大概,在杭时,治六井,开西湖,建南北长堤等,造福一方百姓。越二年,苏轼知颍州、扬州。至元祐七年(1092)九月,以兵部尚书兼侍读,重新回到了朝廷中枢,“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当年那种兴奋、热忱早已消失殆尽了。“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的性格,决定了苏轼在中枢必定待不久。苏轼地位显赫,除兵部外,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又守礼部尚书衔。在党派斗争中,洛党稍衰、川党复盛之论渐起。时有御史董敦逸、黄庆基等弹劾苏轼,指苏轼引川人和亲戚入朝为官,培养个人势力。面对指责,苏轼虽然做了必要的辩驳,但想来无趣,再度上乞,乞求外放越州,即有《任兵部尚书乞外郡札子》《辞两职并乞郡札子》等。
“伏乞检会累次奏状,除臣知越州一次。”“而荣名骤进,两职荐加,不独于臣有非据之羞,亦恐朝廷无以待有劳之士,岂徒内愧,必致人言。伏望圣慈特赐追寝,仍乞检会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无阙,乞自朝廷除授。”苏轼一再上乞,希望去显赫之职,求外放,甚至说,可除一重难边郡,“令臣尽力报称,犹可少安”,以保边郡安民,宣朝廷之威。元祐八年(1093)九月,苏轼罢礼部尚书任,以两学士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出知定州军州事。苏轼履定州,非他本意,其间,他还上《乞越州札子》,希望能知越州。“……盖为臣从仕以来,三任浙中,粗知土俗所宜,易于为政。又以老病日加,切于归休,旧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久荒不治,欲因赴任,到彼少加完葺,以为归计。越虽僻陋,在臣安便。……若辞定乞越,于义无嫌。伏望圣慈察臣至情,特赐改差臣越州一次。则公私皆便,臣不胜幸甚。”但这岂是苏轼可以自行决定的呢?在苏轼看来,越不如定,无拣择之嫌,但朝廷就是不肯下诏,苏轼也无可奈何。好在苏轼大多能顺应环境,知定州后,竭力整顿军务,卓有成效。
时,朝廷政权更替,幼主哲宗登位,小人围绕。约莫半年,在近臣的不断谗言下,苏轼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以左朝奉郎责知英州。英州是个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广州英德,但在宋时,英州与中原路途遥远,是边远的蛮荒之地。苏轼前行至滑州,天气渐热,路途漫长,如何才能到达呢?在这时,苏轼上《赴英州乞舟行状》。这篇上乞,写得感人至深,读来让人为之动容。“近准诰命,落两职,追一官,谪守岭南小郡。臣寻火急治装,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闻命已来,忧悸成疾,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童齿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长。……臣窃揣自身,多病早衰,气息仅属,必无生还之道。然尚延晷刻于舟中,毕余生于治所,虽以瘴疠死于岭表,亦所甘心,比之陆行毙于中道,藳葬路隅,常为羁鬼,则犹有间矣。恭惟圣主之德,下及昆虫,以臣曾经亲近任使,必不欲置之死地,所以辄为舟行之计。敢望天慈,少加悯恻。”一个有着八年经筵之功的大臣,远赴他乡,陆行不得,可能中途客死他乡,欲乘舟前行,都要上表乞求,想来也是悲凉无助,人生何处话凄凉。好在,苏轼有“暴雨过云聊一快,未妨明月却当空”的气概,弱缆能争万里风,万里行役,何惧之有。
愿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一颗明亮之心的苏轼,为自己的仕途职位上乞起于《乞常州居住表》,最后又以乞仕常州而终结。知英州途中,几度更改诏令,苏轼最后以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在惠州三年,再贬海南,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直到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任便居住。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行,至真州,瘴毒大作,泻痢卧病,随后至常州。在常州上《乞致仕状》,乞求告老:“……臣人微罪重,骨寒命薄,难以授陛下再生之赐……今已至常州,百病横生,四肢肿满,渴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余日矣。自料必死。臣今行年六十有六,死亦何恨,但草木昆虫贪生之意,尚复留恋圣世,以辞此宠禄,或可苟延岁月,欲望朝廷哀怜,特许臣守本官致仕。”月余,苏轼卒。
苏轼为己上乞,或任职,或去职,或诉情,或恳呈,行文字语间,多尊上。上下尊卑,在苏轼这样的文人中,是再自然不过的。同时,苏轼也坦诚真切,不做媚态的表达,其尺度拿捏得较好。这大抵是苏轼这样的文人应当有的气节和品行。当然,就苏轼为自己的事情上乞的文本中,我们看到的多是真切的请求,多是事情的陈述,是具体的“己事”,其格局、思想上还有欠缺,或者说,这部分的上乞,还远远不能看出苏轼高远的思想、品格和朴素的为民情怀、为政之道。
不独为忠义之功,亦以广文武之用
元祐元年(1086)七月二十三日,苏轼同胡宗愈、孙觉、范百禄等状奏《乞留刘攽状》,这是苏轼为他人上乞的状奏之一。时刘攽,起居襄州,入为秘书少监,旋以病,乞出守蔡州。攽为人疏隽,不修威仪,喜谐谑,数招怨悔,终不能改。但苏轼以为,刘攽文章尔雅,博学强记。刘攽与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作《东汉刊误》等,为人称颂。所以,苏轼望圣慈留攽京师,更赐数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过人。
苏轼为攽说请,一者与刘攽有私交,知刘攽才情,为可交之人;二者确为朝廷用人所需,当留京师。刘攽与苏轼一样,属于性情中人,好谐谑。苏轼也大抵是这样的性情,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性情、意气相投。同时,苏轼等上乞陈诉十分在理,没有隐瞒刘攽好喜谐谑的不足,说刘攽在外,为朝廷所惜,当留攽京师,为朝廷所用。苏轼等上乞所言实事求是,其后不久,刘攽回京师,出任中书舍人。
《乞加张方平恩礼札子》是苏轼为张方平礼遇上的一道乞状。张方平乃宋时名臣,苏轼早年在成都时,曾求教于张,二人相见恨晚,终生以师生之谊相待,情逾骨肉。“……张方平,以高才绝识,博学雄文,出入中外四十余年,号称名臣。”接着苏轼列举了张方平于仁宗、神宗等四朝之功业,希望朝廷给予加恩劳问,以示朝廷贵老尊贤之义。苏轼所呈,虽有其与张方平之间的情谊成分,但其所表,也“为天下所服”。
苏轼的性情耿直,为他人乞求去留,乞求恩典,乞求职务,写得入情入理,掌握的火候十分到位。比如他在《乞加张方平恩礼札子》中,不仅列举了张方平的才识、博学,尤其抓住了张方平首建和戎之策、首论安石变法不可用等,更是说方平与彦博、范镇齐名,而彦博在廷、镇亦复用,现在就剩下方平了,理应给予方平恩遇。这样的陈述,少了个人情谊的说请,多了从社稷之益出发的厚重。
不独为忠义之功,亦以广文武之用。朝廷在于用人,苏轼在元祐年初,居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兼侍讲,位置显赫。经历了人生颠簸的他,或许知道人才的难得,也知道何为忠臣义士,因此在这过程中,就主动上乞,推荐他人充任要职。《乞录用郑侠王斿状》于元祐二年(1087)三月上乞。“……臣
等伏见英州别驾郑侠,向以小官触犯权要,冒死不顾以献直言。而秘阁校理王安国,以布衣为先皇帝所知,擢至馆阁,召对便殿;而兄安石为相,若少加附会,可立至富贵,而安国挺然不屈,不独纳忠于先帝,亦尝以苦言至计规戒其兄,竟坐与侠游从,同时被罪。……今来朝廷赦侠之罪,复其旧官,经今逾年,而侠终不赴吏部参选。考其始终出处之大节,合于古之君子杀身成仁、难进易退之义。朝廷若不少加优异,则臣等恐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则有识必为朝廷兴失士之叹。至于安国,不幸短命,尤为忠臣义士之所哀惜。臣等尝识其少子斿,敏而笃学,直而好义,颇有安国之风,养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圣慈召侠赴阙,并考察斿行实,与侠并赐录用。不独旌直臣于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气于当代也。”在苏轼看来,国之兴衰,系于习俗,“或风节不竞,则朝廷自卑”,像郑侠、王安国(延伸至其子王斿)这样自重之士、风节之士,朝廷当以录用,必厉士气,以“养成礼义廉耻之风”。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赠刘景文》)刘景文即刘季孙,乃名门之后,其出任两浙兵马都监期间驻扎杭州,与同仕杭州的苏轼往来密切,友谊长青。苏轼于元祐五年(1090)上《乞擢用刘季孙状》。擢用,意为提拔任用。这在苏轼上乞中,似乎是仅有的三份之一(其余两份为《乞擢用程遵彦状》《乞擢用林豫札子》)。“……今臣所与同僚西京左藏库副使权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兼东南第三将刘季孙,则平之少子。笃志力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虽文臣亦未易得。况其练达武经,讲习边政,乃其家学。至于奋不顾身,临难守节,以臣度之,必不减平。今平诸子独有季孙在,而年已五十有八。虽备位将领,未尽其用。伏望朝廷特赐采察,权置边境要害之地,观其设施,别加升进。不独为忠义之劝,亦以广文武之用。”刘季孙承家风,练达武经,又重义轻利,当除边境要塞予以擢用。这不仅是彰显忠义之功,也是朝廷用人所需。后刘季孙知隰州。至元祐七年(1092),刘季孙卒于官所,家徒四壁,灵柩无法安葬,苏轼甚是伤哀,上《乞赙赠刘季孙状》:“……家无甔石,妻子寒饿,行路伤嗟。今者寄食晋州,旅榇无归。臣等实与季孙相知。既哀其才气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义死事,声迹相接,四十年间,而子孙沦替,不蒙收录,岂朝廷之意哉?……欲望朝廷特诏有司,优与赙赠,以振其妻子朝夕饥寒之忧,亦使人知忠义死事之子孙,虽跨历岁月,朝廷犹赐存恤。”为忠义之后、为重义者奔走乞赐。
重才识,重品行,重节气,崇情怀,崇情义,怀悲悯,这是苏轼浸透在骨子里的为人之道、为官之本。不管是为刘攽、张方平,还是为郑侠、王斿、顾临、刘季孙上乞,其根本都在于苏轼以为这些人是值得尊重,值得录用,值得礼遇的。唯才是用,唯德执政。苏轼上乞,为他人说请,自然有其情感的亲疏,但基本言之成理,举贤不避亲,意在朝廷重视人才,为国效力。这也是他为官之道、为国报效的朴素情怀的体现。
深可忧虑,仁圣哀怜
苏轼的上乞状子大多写于哲宗元祐年间,从元丰八年(1085)归朝以来,苏轼在京城得以重用,常侍朝廷左右,位显人贵。至元祐四年(1089),苏轼不想陷于党争,上乞外放,随后知杭州。苏轼是一匹驰骋的马,给他一片土地,定能耕耘出硕果。从贬谪黄州,到奉旨回朝,再到外乞一郡,苏轼在这过程中,上了一些关乎民生福祉的状子。这些状子,有的很细,就某个问题请求朝廷给予解决,有的带有普遍性问题,谋民生之远,为百姓之福。
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身在常州的苏轼得朝廷诏书知登州。十月十五日,苏轼到达登州,十月二十日,接朝廷召他回京旨意。“莫嫌五日匆匆守,归去先传乐职诗。”(《留别登州举人》)五日知守却对登州民生深有体察,“入境问农,首见父老”。时登州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乃边陲之地。登州沿海一带百姓以煮盐为生,按当时的榷盐制度,灶户所产之盐只能低价卖给官府,再由官府高价卖给百姓,结果是灶户生活难以为继,当地百姓只能吃贵盐。登州临海,本是产盐之地,百姓却吃不起盐。于是,回到京城的苏轼向朝廷呈上《乞罢登莱榷盐状》,指出登州榷盐制度之弊端,并提出了可行的操作方案,建议罢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以利国利民。苏轼上乞后,朝廷废罢了登莱榷盐。这个政策从宋朝一直延续到清末,造福当地百姓八百余年。当地百姓感恩苏轼为民请命,立起《乞罢登莱榷盐状》刻石,以资纪念。《增修登州府志·职官》载:“在郡未一月即内召,士民感化,深惜其去之速也,后立祠祀之,并祀名宦祠。”《蓬莱县志·食货志·盐法》载:“蓬邑不食官盐,自宋代苏长公已条陈得免其累,洵所谓仁人之言,其利薄哉!”
元祐四年(1089),知杭州不久的苏轼,见雨旸失调,很是揪心。时浙西七州,杭、湖、秀、睦、苏、常、润,要么淫雨为患,要么干旱异常。苏轼预料明年春夏必有饥馑盗贼之忧,于是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陈述了灾情,并提出了对策:“乞出自宸断,来年本路上解钱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余候丰熟日,分作二年,随年额上供钱物起发,所贵公私稍获通济。”“见今逐州和籴常平斛斗及省仓军粮,又籴封桩钱、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务趁办,争夺相倾,以此米价益贵。……欲乞指挥提、转令将合发上供钱,散在诸州税户,令买金银绸绢充年额起发。”苏轼上乞后,久久未有诏答。他知道地方监司有报喜不报忧的习气。他心里很是不安,于是又分头给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防以及门下仆射诸公去信呼吁,请他们给予支持。经过苏轼的多方呼吁,朝廷终于许可,准许保留上供米三分之一,约二十万石,办理平籴。
柴米油盐乃民生之本。苏轼于元祐五年(1090)五月上《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斗出粜济饥等状》、元祐六年(1091)三月上《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上《乞赐度牒籴斛斗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绍圣元年(1094)正月上《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绍圣二年(1095)二月上《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等。苏轼上乞,为百姓求盐、求米,是其心怀百姓、为民做主的表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这朴素的为民情怀,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苏轼的上乞中,还有一些看似小事,但也展示出其高远的情怀和务实的作风。
《大雪乞省试展限兼乞御试不分初覆考札子》,于元祐三年(1088)正月上乞。时数千里大雪,道路艰塞,四方举人赴省试者,三分中未有二分到阙。朝廷展限,但所展日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苏轼乞自今日已往,更展半月,又乞省试添差小试官十人,促限五七日出榜。“……御试差官,分为初考、覆考、编排、详定四处,日限既迫,考官又少,以此多不暇精详。又缘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齐足,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据誊录所关到卷子三十五十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后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于幸与不幸,深为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条式,聚众考官为一处,通用日限,候卷子齐足,众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详寡失,又御试放榜,亦可以速了。”为了考生能如愿应试,也显朝廷用人之公、之恩,苏轼上乞札子可谓细致,陈述了理由,又有很强的操作性,细微之处见情怀、见精神。
元祐三年(1088)三月,省试放榜后,苏轼又上了札子三首,即《乞裁减巡铺兵士重赏》《乞不分经取士》《乞不分差经义诗赋试官》。在这三首札子中,苏轼主要陈述朝廷应不分经取士,“将来兼用诗赋,不专经义”。“……试经义者主虚浮之文,考诗赋者主声病之学。纷纭争竞,理在不疑,举人闻之,必兴词讼,为害如此,了无所益。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经义、诗赋等是文词,而议者便谓治经之人,不可使考诗赋,何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赐指挥,今后差试官不拘曾应经义、诗赋举者,专务选择有词学人充,其礼部近日所立条贯,更不施行。”朝廷既复诗赋,当以实施。后来,苏轼职杭州后,还上《乞诗赋经义各以分数取人将来只许诗赋兼经状》:“臣曩者备员侍从,实见朝廷更用诗赋本末。……然臣在都下,见太学生习诗赋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闻蜀中进士习诗赋者,十人而九。及出守东南,亲历十郡,及多见江湖福建士人皆争作诗赋,其间工者已自追继前人,专习经义,士以为耻。以此知前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皆妄也。惟河北、河东进士,初改声律,恐未甚工,然其经义文词,亦自比他路为拙,非独诗赋也。朝廷于五路进士,自许礼部贡院分数取人,必无偏遗一路士人之理。”朝廷取士,旨在得人才,治天下;学子苦读,意在出仕,为社稷苍生谋福祉。如何才能使朝廷满意、学子满意呢?应试是至关重要的,从隋唐以来的科举,至宋时已相当完备。苏轼上乞不分经取士等,也意在朝廷不偏遗一路士人。“诗赋进士,亦自兼经,非废经义也。”
元祐四年(1089)八月,苏轼上《乞赐州学书板状》,说有生员二百余人,学粮生计为重,奏乞用废罢市易务书板,赐予州学,印赁收钱,以助学粮。“伏望圣慈特出宸断,尽以市易书板赐与州学,更不估价收钱,所贵稍服士心以全国体。”元祐四年(1089)九月,苏轼上《乞赐度牒修庙宇状》,称杭州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乞支赐度牒二百道,及且权依旧数支公使钱五百贯,以了明年一年监修官吏供给,及下诸州刬刷兵匠应副去讫。后杭州供米出粜,见缺三万余石,民间恐顿然缺粮。于是,苏轼就想到,以度牒召苏、湖、常、秀人户,令于本州缺米县分入中斛斗。“以优价入中,减价出卖,约可得二万五千石,粜得一五万千贯。访闻苏、湖、常、秀,虽其灾伤,富民却薄有蓄积,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钱修完廨宇,庶几先济饥殍之民,后完久坏屋宇,两事皆济,则吏民荷德无穷。”先济饥民,后修廨宇,苏轼给出了可行的方案。
元祐五年(1090)五月,苏轼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苏轼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随后列举西湖有不可废者五,“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赐详览,察臣所论西湖五不可废之状,利害较然,特出圣断,别赐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转运、提刑司,于前来所赐诸州度牒二百道内,契勘赈济支用不尽者,更拨五十道价钱与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尽力毕志,半年之间,目见西湖复唐之旧,环三十里,际山为岸,则农民父老,与羽毛鳞介,同泳圣泽,无有穷已。”在苏轼的努力下,杭州西湖遂成西子模样,美不胜收,亦造福一方。在杭州期间,苏轼还上《乞相度开石门河状》,“使数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咏歌圣泽,子孙不忘”。
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重起变法措施。苏轼作为守旧派人物受到冷遇,外知定州。政治失意,又逢妻子王闰之病故,肝肠欲断。但苏轼主知一方,就是要为民谋政,为国分忧。时定州乃宋北部边陲,北临契丹,辖七县一寨,河北军区还要负责两州三军的防务,即定州、保州,安肃军、广信军、顺安军,军政责任重大。苏轼到达定州后,发现定州的情况非常糟糕,满街都是军容不整的士兵和食不果腹的百姓,政务军务十分混乱。又旱情,收成锐减,士兵逃亡屡有发生。假如此时兵临城下,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顾不得悲伤的苏轼上《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改善士兵居住环境和饷银制度,短时间内稳定了军心,提高了战斗力。接着又上《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一二,强化军民军事训练。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或许就是苏轼这般的务实执政,为国为民的职操,为我们后人树立了榜样。
不管是盐、米,还是修建廨宇,开西湖、石门河,赐学书板,整军务,大考遇雪当延期,不分经取士等,都是苏轼着眼小事,为百姓民生呼吁,为民上乞,为国效力请状。心中有民,民为本,遇民之疾苦,见民之困境,自然就“深有忧虑”,其上乞希望“仁圣哀怜”;心中有国,国为基,见国之危,希望国为安。这样的上乞,苏轼偶也“惶恐战栗”,但我们今日读来,却倍感亲切,于平常中见情怀,于细小中见伟大。
以计图之,似为得策
苏轼上乞的状子、札子中,窃以为有不少是带有开创先河意义的,比如元丰二年(1079)正月的《乞医疗病囚状》。时苏轼知徐州,状子的大意,就是要给监狱服刑的囚犯医病的权利。“……若本罪应死,犹不足深哀,其以轻罪系而死者,与杀之何异?积其冤痛,足以感伤阴阳之和。”苏轼提出,军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选差衙前一名,医人一名,每县各选差曹司一名,医人一名,专掌医疗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为界。量本州县囚系多少,立定佣钱,以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充,仍于三分中先给其一,俟界满比较,除罪人拒捕及斗致死者不计数外,每十人失一以上为上等,失二为中等,失三为下等,失四以上为下下。朝廷按等级给予不同的奖励或处罚。时囚禁的罪犯,寻常人往往避之不及,甚至欲除之而后快,但苏轼体恤弱势群体,整饬法令制度。后苏轼的上乞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宋人黄震撰《黄氏日抄》卷62《奏议》有载,“‘乞医病囚状’具载治平手诏、熙宁札子折衷其说,毋坐狱官罪,而课医病者功罪”。这里所说的“乞医病囚状”,即指苏轼的上乞奏状。
苏轼在上乞的状子中,还有一些涉及边境政策的,也是值得我们给予重视的。
“臣闻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则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则战胜而寇愈深,况不胜乎?功成而兵不解,况不成乎?”治边治疆,当以服其心也。苏轼在《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中,对边疆之患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希望朝廷能“深诏边吏,叛则讨之,服则安之”。时有“鬼章犯顺,罪当诛死”。但“鬼章若死,则其臣子专意复仇,必与阿里骨合,而北交于夏人”。如果给鬼章生机,可以鬼章之众与温溪心合而讨阿里骨,其势必克。鬼章者,唃厮啰将领,桀黠有智谋,所部精锐,数为边患。宋熙宁中,诱陷河州,神宗屡诏王韶,欲生致之。至是与夏人解仇为援,筑洮州居之。谊率众破其城,擒鬼章,槛送京师。温溪心,吐蕃首领,时与其侄温讷支郢成共有邈川(今青海乐都)之地。阿里骨,宋时青唐唃厮啰政权第三代主,哲宗时封其为冠军大将军、右金吾卫大将军等,使持节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充河西军节度、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元祐二年(1087),阿里骨联合夏国相梁乙逋,进攻熙河六州。是年四月,以大将鬼章与子结咓龊出兵占据洮州,亲率大军十万配合鬼章围攻河州,被宋将游师雄等击败,从此一蹶不振,政权渐衰。苏轼于元祐二年(1087)的两份上乞,意在联合鬼章、温溪心,以图瓦解阿里骨政权。这种“以夷狄攻夷狄”的做法,可谓“以计图之,似为得策”。
元祐五年(1090)八月十五日苏轼上《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这是一篇海外贸易制度建设的重要状子。在这篇上乞中,苏轼提到了几个当时的案件:一是泉州商人徐戬假借为高丽国雕造经板两千九百余片的理由,私下收受酬答银两达三千两。二是商客王应升等人,向市舶司申请前往高丽经商的公凭,却借机前往北宋的“敌国”大辽进行走私交易。三是商人李求假借前往高丽国经商,私下收受“实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余布袋”。在这三起案件中,商人假借贸易,公私骚然,收受利益,规避监管。苏轼对此高度警觉。除此外,他还看到了宋代随着海外贸易的繁盛,铜钱、兵器、白蜡、盐、铅、锡、矾、乳香等重要战略物资因走私大量外流,奸民猾商,往来无穷。他从维护国家利益,严肃法律秩序,加强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引用《庆历编敕》《熙宁编敕》的相关规定,向朝廷提出了对外贸易的整改措施。他要求加强商船货物的检验手续,特别是商船出海必须有三人以上担保不夹带禁物,方可发给公凭,同时还要对走私者落实惩罚机制,严肃法律处分。苏轼看到的是当时海外贸易走私的弊病,并提出了补救对策。这些对策有的得到了朝廷的采纳,比如出口日本的货物,就需开出货物的名称、件数及出卖的目的地等,而且要有三个当地人写的保证书。可惜的是,苏轼的这些对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从北宋到南宋,海外走私日益猖獗,加夹着里通外国等,给宋朝政权带来严重伤害。法不严执,令无威慑,一定程度上伤了国体。但就苏轼的《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而言,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显然已经超出了其文学情怀追求,展示出其政治格局和谋略,其政治洞察力、前瞻性、忧患意识、全局意识等,都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
苏轼上乞,乞己之愿,乞人之恩,乞民之安,乞国之治。有微有宏,有情有理,有破有立,都以社稷为计,以民为计。为官者,在其位谋其政,苏轼虽以文学见长,留于史册,但其为政也深得民心,到任一方,造福一方,为后人所敬仰。
责任编辑 韦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