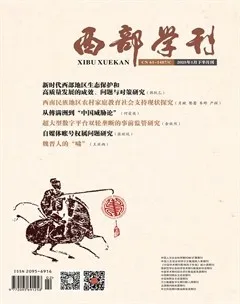ODM生产模式下专利侵权主体的认定与责任承担

摘要:ODM代加工是制造业常见的商品生产方式,实践中该领域专利侵权纠纷日益频发,在专利侵权主体认定及责任承担等问题上引发较大争议。以近十年50件典型案例为基础,结合专利法、民法合同及侵权原理,运用法律解释学方法、法经济学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认为ODM模式下专利侵权主体应该是对侵权产品生产过程具有“直接控制力”的当事人;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在明确ODM协议双方法律关系的基础上依据各方过错情形分别承担按份责任或连带责任。
关键词:ODM;承揽合同;侵权主体;无意识联络数人侵权
中图分类号:D923.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5)02-0099-04
Subject Identification of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Responsibility Division in ODM
Lu Ruimin
〔Law Schoo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chool),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 (ODM) is a common method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in this field have become more frequent. Thus, there are several significant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subject identification of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their responsibility distinction. Based on 50 typical cases in the past decade,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patent law, civil law contracts, and tort principles, this study employs methods of legal hermeneutics and legal economics t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ODM model, the subject of patent infringement should be the party with “direct control” over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infringing product. The assumption of infringement liability should be based on clarifying the leg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both parties in the ODM agreement, and each party should bear joint or several liabilities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faults.
Keywords: ODM; contract for work; subject for infringement; joint tort without conscious connection
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代加工模式是制造业中一种常见的生产模式,ODM协议双方系品牌商与设计制造商。由于ODM协议履行过程中牵涉多个市场主体,一旦生产过程涉及专利纠纷,品牌商与设计制造商当如何进行专利侵权赔偿便产生了该领域特有的司法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对比分析了近十年50份ODM模式下专利纠纷典型案例,通过对该领域司法实践的检视,发现实务观点之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ODM模式下专利制造侵权主体认定标准不一
ODM模式下专利侵权制造主体认定的司法实践呈现出三种裁判思路。第一,在专利权人同时起诉品牌商与商品标识的制造商,法院基于二被告以共同故意一起实施了专利制造侵权行为判处二被告共同侵权。第二,诉讼参与人不包括设计制造商,因诉讼主体数量限制,判决唯一被告(品牌商)承担专利制造侵权责任。第三,法院认为只要一方实际控制生产过程,就应该认定其实施了“制造”行为。
(二)ODM模式下专利制造侵权责任划分存有争议
对应上述三种侵权主体认定的三种司法裁判思路,在责任划分层面亦存在连带责任、单独责任与其他责任形式多种观点。ODM模式下专利侵权责任划分,无法简单适用《专利法》第七十一条关于赔偿数额的规定,司法实践回归《民法典》区分多数主体是否有意思联络而分别承担不同的责任形式。但是,主观过错并非专利侵权的构成要件,法院着重论证了专利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落入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的主观构成要件,忽视了《专利法》的特别法地位。另外,司法机关误判品牌商与设计制造商之间的法律关系,裁判理由模糊了物理意义制造与法律意义制造的区别。
二、ODM模式下专利侵权中“制造”的认定
整理50件案例后发现,15件案例坚持“贴牌即制造”观点,其主要立论是深口袋理论,即默认实施贴牌行为的品牌方比实际生产的制造商具有更大的市场占有率与风险承担力,发生专利侵权风险时应当由品牌方承担责任。22件案例采用“贴牌初步认定为制造”的观点,认为商标是认定侵权产品制造商的初步证据,综合考量商标权人经营范围、商标权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一般公众的注意义务,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该商标权人就是侵权产品制造者。另有10件案例采纳“实质性判断标准”,认为当事人的实际制造行为消除了商标的标识作用。
(一)专利法意义上的制造主体应具备直接控制力
司法实践对于专利“制造”行为解释随着时代发展作出调整。敖谦平与飞利浦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再审案判决之前,对于专利制造侵权主体的判断多以商品外观标识为准,但敖谦平案最高法认为,“在ODM专利产品的情况下,如果委托方要求加工方根据其提供的技术方案制造专利产品,或者专利产品的形成中体现了委托方提出的技术要求,则可以认定是双方共同实施了制造专利产品的行为。”[1]该裁判基准区分了物理意义上的制造者和专利法意义上的制造者,即《专利法》第十一条的制造侵权主体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亲手制造的人。(2021)闽民终1565号判决书对上述两种意义的制造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至于被诉侵权产品是由被告自行制造,还是委托他人制造,均是就物理制造行为而言,不能据此否定被告系法律意义上的制造者的事实。”专利法意义上的制造侵权主体应当扩大解释为一切对侵权产品生产过程有直接控制力的人,直接控制力具体表现为在物理意义上总有一个主体作为实现权利要求中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主体存在,物理意义上从事实现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主体作为某一主体的“手足”来实现产品的制造时,那么,物理意义上的主体就不具有规范意义上的主体地位,而是将其作为“手足”利用的主体应该被评价为“制造主体”[2]。ODM加工专利侵权案中,具有“直接控制力”存在如下表现方式。第一,品牌商选择或者提供具有专利侵权风险的设计方案制造专利产品,或者专利产品的形成中体现了一部分定作人提出的设计要求。第二,生产所涉及的侵权行为由制造商独自实施,品牌商未干涉侵权产品生产过程。
(二)专利制造侵权判定不宜以商标归属为准
采用“贴牌即制造”观点的判决书多以品牌方具有“更深的口袋”,即更大市场占有率与风险承担力,判决由品牌方承担专利制造侵权责任。但是,随着制造业产业升级与市场下沉,当前作为商标权利人的品牌方不必然比实际生产人拥有更深的“口袋”,前者不必然有能力向社会分散风险。另外,品牌商仅在成品上贴附商标这一行为很难解释为“生产”行为。商标具有标识商品来源作用,不能以商标标识作用掩盖当事人间对“制造”行为之分工。
部分主张“贴牌即制造”裁判基准的判决书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2020修正)》来论证商标权人,即制造侵权主体:任何将自己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个人,均属于《民法典》和《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生产者”。本批复系关于诉讼主体的明确,并非明确责任承担主体,以程序法上的批复论证实体法上的侵权主体不甚合理。
三、ODM模式下专利制造侵权主体的识别
OMD模式下专利制造侵权主体的识别首先应当正确识别ODM协议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再以该法律关系为出发点分别解释协议双方的行为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制造”行为。
(一)ODM模式下委托方与受托方法律关系的认定
目前,司法实践关于ODM品牌商与设计制造商之间的法律关系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
首先,ODM加工专利纠纷判决显示,被诉品牌方多以与案外设计制造商系买卖关系主张合法来源抗辩。买卖合同区别于承揽合同的关键是合同义务人是否需要提供创造性的劳务。本文讨论的案例模型无论行为主体是否为同一人,“加工”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具有创造性的劳务过程,而非产品的物权转移过程。故,“参与”甚至“主导”侵权产品生产过程的品牌商,应认定为承揽合同定作人。
其次,委托合同与承揽合同的区分在学术上争议已久。主流观点认为,在判断某一劳务给付合同的性质是委托还是承揽时,应当以合同标的(即劳务提供者的主要支付义务)是否包括提供工作成果为标准。兼顾报酬支付是否与工作成果交付形成对待给付,以及违约责任是否仅仅取决于提供劳务一方是否按约提供工作成果两因素,而不是单纯地关注提供劳务一方履行行为是否合理来进行判断[3]。在ODM模式下专利纠纷表现为合同义务人按照权利人的要求生产与之相符合的实体产品。另,合同权利人已经将义务人提供产品的规格、质量与乙方之报酬、违约责任相关联,常以“有偿”+“符合甲方要求”为合同内容,这契合了学界关于承揽合同与委托合同区分的“其他合理因素”。
最后,从承揽合同的构成要件与定义来看,我国《民法典》第七百七十条第一款和第七百七十九条第二款分别以构成要件立法与列举式立法对承揽合同进行了规定。上述规定仅具有参考意义,实践中如何识别承揽合同,还是应当从给付标的——“完成工作”与“交付工作成果”两个方面来判断承揽合同[4]。“完成工作”即指承揽人生产出定作人所要求的产品,“交付工作成果”即指承揽人将上述产品的所有权与占有权均转移至定作人。在ODM专利产品加工的交易模型下,品牌厂商具有不同的法律身份,首先是承揽合同定作人,其次是专利侵权产品的所有人。设计制造商同样兼有两种法律身份,一是承揽合同的承揽人,二是案涉专利使用人。
(二)承揽关系中专利制造侵权主体的具体认定
上文提到ODM模式专利侵权中对生产过程有“直接控制力”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承揽合同双方对于样品/方案存在的专利侵权风险进行过深入沟通,即存在着侵权的合意,并且定作人管控着生产过程,侵权合意一直持续到侵权产品生产完毕交付定作人,协议双方共同侵权。第二种“直接控制力”表现形式是生产所涉及的侵权行为由承揽人独自实施,定作人不知情侵权产品生产过程。此种情形下,定作人发出要约,未参与实际生产,构成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基于我国专利侵权不考虑主观因素以及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定作人合理注意义务与承揽合同效力问题并不影响定作人被认定为专利制造侵权主体的法律判断。
1.共同侵权:双方共同实施专利制造侵权行为
尽管学界关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共同过错”存在共同故意说、主客观共同说、共同过错说之分歧,但我国司法实践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共同侵权的主观要件是“共同故意说”,共同加害行为应以意思联络为构成要件,这样有助于澄清共同加害行为与共同危险行为、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之间的区别,减少相关条文的适用冲突,避免数人侵权行为体系的混乱[5]。承揽合同双方当事人关于专利侵权有明确的侵权合意,且在合意之下分别以“控制手足”和“依约侵权”的行为方式共同实施了客观侵权行为,因为双方的不法行为共同造成权利人经济损失,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与《专利法》第十一条予以规制。
2.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承揽人独自实施专利侵权行为+定作人的过失
法经济学理论可以预测法律制裁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学上产品的真实成本,包括产品社会成本是私人成本与外部成本之和,前者包括工资等由厂家所支付,后者包括因厂家生产致使其他人所受损失,如环境污染、知识产权侵权。定作人为了减少产品社会成本,将私人成本转移给承揽人以追求更高的商业利润。但出于对外部成本的考量,定作人会维护商标商誉,拒绝贴有自己商标的侵权商品滥觞于市场。同时,定作人有《民法典》第七百八十条赋予的“验收权利”,定作人怠于行使验收权利,理应承担产品侵权带来的法律风险。
另一方面,期望价值理论揭示了ODM协议双方所面对的市场风险不尽相同。假设某一市场主体面临两个可投资项目,其中第一个项目生产市场主体熟悉而稳定的产品,这一项目的收入稳定。而第二个项目该主体将生产市场前景存在风险的新型产品,如果不存在侵权风险,则可以赚取大于第一项目稳定收益的利润;若存在侵权风险,那么该主体将面临亏损。第一项目的期望值为所有可能性概率乘以其收益价值的总和;第二项目,也是所有偏好盈利的市场主体会投资的项目,其期望值可以表示为:
期望值=成功率×成功收益-(1-成功率)×失败收益
市场主体计算项目成功率时需要考虑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三个方面,即搜寻成本、谈判成本与执行成本。ODM专利加工协议双方具有不同的法律身份,故双方考虑交易成本时,考量的内容不尽相同。作为定作人与侵权产品所有人的品牌商在考虑成功率时,需要考虑的交易成本可以拆分如下:搜寻成本=搜寻承揽人与消费者的成本;谈判成本=与承揽人商定标的额的成本+市场调查定价成本;执行成本=承揽合同如约履行成本+售后成本。而承揽人与专利权人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寻定作人与专利权人的搜寻成本,承揽合同与专利许可的谈判成本,如约交付产品与按许可进行生产的执行成本。ODM专利加工协议的成功率会影响承揽人与定作人的市场决策,双方决策者可以计算出产品专利侵权与不侵权各自的市场成功率。即使无法知道准确概率,如果通过计算得出风险项目(专利侵权)成功率高于稳定项目(不涉及专利侵权),承揽方就会选择实施侵权行为。由此可以推断,ODM模式下专利侵权承揽双方主观内容与形式均不相同,属于无意思联络数人分别实施加害行为造成同一损害。
四、ODM模式下专利制造侵权责任的具体承担
(一)ODM协议双方共同侵权:连带责任
ODM专利侵权纠纷中定作人“直接控制”生产过程,提供专利侵权技术方案,属于“定作人存在定做或者指示过失”,承揽人主观上明知定作人存在上述过失仍然进行了生产工作,则二者构成共同侵权。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916号民事判决书直接适用原《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被诉侵权人具有侵权合意,且共同实施了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仅有一方的行为均无法完成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故应认定二者共同实施了侵害涉案专利权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ODM协议双方构成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按份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但书规定定作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学者认为从立法技术上讲,“相应的责任”条款之所以存在,与其说是给理论与实践发展预留空间,不如说是因多数人侵权的复杂性而对其无法采用单一的责任形态予以规范[6]。定作人对定作、指示和选任具有过错,承揽人也有过错,此时需依据双方过错内容进一步区分,根据上文分析承揽人控制生产过程,定作人不知侵权实情,则定作人与承揽人过错的内容与形态均不相同,不存在共
同过失,其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结合造成同一损害,应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承担按份责任。
前文已经用期望价值理论分析了承揽人提供生产侵权技术方案,定作人受领侵权产品这一侵权模式下承揽合同双方的主观心态与客观行为。个体在不确定的市场情况下做决定时,并不是试图最大化其期望值,而是最大化期望效用。经济学家通常把大型商业组织假设为风险中性,即相同期望值的确定收入和不确定收入对其而言无差异,效用函数是一条正比例函数;而偏好不确定性资产的风险追求具有递增的边际效用,二者函数关系如图1所示。
图1ODM协议双方的风险曲线
对于风险中立者来说,无论在何种收入区间内,随着收入增加资产的效用都保持同样的增长率。对于风险偏好者来说,收入需要从2 000增加至5 000左右,效用才会增加40%,在高收入区间收入仅仅需要增加750左右就可以实现40%的效用提升,故风险偏好企业会选择更高的收入区间。在承揽人独自实施侵权行为的模型中,承揽人选择了更高风险的市场策略,符合了图表中的承揽人风险偏好,ODM专利协议的承揽人会在交易过程中搜寻商标影响力更大或者市场占有比更大的品牌商,在谈判过程中争取到更大标的额并在执行过程中生产更多专利侵权产品。而不明真相的定作人是侵权产品的商标权人,仅需按照ODM协议受领产品支付对价,并顺利在市场上销售商品并获得确定性收入,符合上述图表的定作人风险中性,即无论收入额上升多少,其资产效用增长率始终持平。
承揽人与定作人双方的商业策略背后蕴含着按份责任的原因力大小归责逻辑,对于专利权受侵害这一“同一损害结果”承揽人追求更高效用具有更积极的侵权意图与行为应承担主要的侵权赔偿责任。而定作人风险中侵权意愿不会随着收入增加而有所变动,因其轻信承揽人且疏于验收应承担次要的侵权赔偿责任。
五、结束语
法律实践应辅助我国制造业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收官之年交出满意的答卷。以合同原理探明ODM协议的承揽合同属性,再回归《专利法》视角审视各主体是否实施了该法第十一条所规制的侵权行为,最后依据侵权责任原理划分各主体责任。如此既维持了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亦不脱离民法一般规定,是为规制ODM模式下专利侵权的合理路径。
参考文献:
[1]崔国斌.专利法:原理与案例[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47.
[2]张鹏.专利法意义上“制造”主体的认定:敖谦平与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再审案[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8(10):110-112.
[3]游冕.《民法典》第919条(委托合同的定义)评注[J].南大法学,2023(4):170-200.
[4]唐波涛.承揽合同的识别[J].南大法学,2021(4):34-51.
[5]程啸.论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以《侵权责任法》第11、12条为中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65-76,162.
[6]焦艳红.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解读[J].中州学刊,2022(6):36-43.
作者简介:卢锐敏(1998—),女,汉族,四川成都人,单位为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
(责任编辑: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