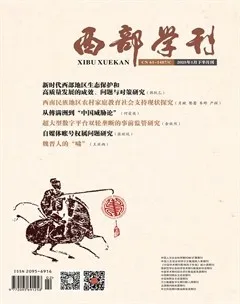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现状探究
摘要: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融合场域中,社会支持对家庭教育的重要价值不可忽视。聚焦西南民族地区农村,以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框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审视当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现状。调研结论:宏观层面,首部家庭教育立法及各地政策助力农村家校社协同育人,村规民约成为农村家庭教育的重要准绳;中观层面,农村家校合作偏向于单向支持状态,社会各界聚焦农村特色加大支持力度,重视民族文化成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特色;微观层面,家长遇到家庭教育问题时优先向家人、亲属等寻求支持。
关键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现状
中图分类号:G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5)02-0008-0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及实施路径研究”(编号:22XJC880009)的研究成果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Support
for Rural Family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Xiao Xuan1Fan Lei2Wei Ye1Yan Hui3
(1. School of Educ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ning 530000;
2. School of Education, Dehong Teacher’s College, Dehong, 678400;
3.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 Guangxi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ning 530000)
Abstract: In the integrated field of family-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he significant value of social support for family education cannot be overlooked. Focusing the on rural areas in ethnic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this study takes Bronfenbrenner’s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as a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support for family education from macro, mes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At the macro level, the family-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is supported by the first legislation on family education and local policies, with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conventions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guideline for family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At the meso level, rural school-family cooperation tends to be in a one-way support model, with various sectors focusing on rural characteristics to increase support and emphasizing ethnic culture a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social support for family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At the micro level, the parents are more likely to seek support from family members and relatives when encountered with problems in family education.
Keywords: ethnic area of Southwest China; family education in rural area;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support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提出,要“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1]。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融合场域中,家庭教育社会支持是重要一环。西南民族地区包括广西、云南、四川、贵州、重庆和西藏等地,拥有壮族、苗族、白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藏族、布依族、仫佬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性格特点等,构建出不同的家庭教育环境。本文以英国学者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作为框架,探究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现状。
一、核心概念界定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他认为儿童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中,这些环境系统也影响着儿童的发展,他将环境系统分为宏观系统、中观系统、微观系统等[2]。其中,宏观系统由社会文化、行为规范和准则、法律等构成;中观系统是两个或多个微观系统的联系,如学校与家庭、社区的关系等;儿童自身的身心特征和其父母、教师等与儿童接触最密切的人都处于微观系统。同时,社会支持体系是由持续的社会集体组成,它为人们提供自我反馈和验证他人期望的机会。这些社会支持包括提供信息或认知指导、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农村子女教育过程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一种着眼于社会治理的教育策略,有助于缩小先赋性不足引发的过程性教育差距[3]。
本文将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界定为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使家庭成员与外界保持有效互动,从中获得政策、情感、信息等支持,以满足家庭养育和教育子女过程中所需要的服务与指导。为了更好地了解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现状,本研究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三个维度出发,面向西南民族地区六个省份农村家长、村民、学校领导和教师、村委干部、儿童等展开调研。
二、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现状分析
西南民族地区家庭主要由核心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等构成,以留守家庭居多,仅广西农村留守儿童目前已有约20万人[4]。而由于我国广西、云南等西南民族地区与越南、缅甸等国家接壤,地理位置相邻、民族相同、语言相通、文化相近、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相通等原因,交往历史悠久,相互通婚的现象较为普遍,形成一定的跨境家庭,成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工作的特色。
(一)宏观层面
本研究将法律、政策、财政等因素归于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的宏观层面维度进行探究,得出首部家庭教育立法助力农村家校社协同育人、各地出台各项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政策,以及村规民约成为农村家庭教育的重要准绳等结论。
1.首部家庭教育立法助力农村家校社协同育人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我国于2022年1月起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托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立社区家长学校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配合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组织面向居民、村民的家庭教育知识宣传,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5]这一规定明确作为农村社区管理组织的村委会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等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职责。同时,该法律强调社会协同,要求妇联、教育、民政、人社、政法等部门联动协同育人,更有利于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工作规范化、有序化。
2.各地出台各项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政策
调研发现,西南民族地区将家庭教育社会支持触角延伸至各村屯,通过扎实落地的政策解决农村家庭教育问题。
以四川为例,2023年3月,四川发布《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2025年)》提出,推动中小学、幼儿园普遍建立家长学校,农村学校建校率达到85%[6]。再以西藏为例,全区各级妇联组织积极推动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部署和专项规划,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7]。而广西也于2023年提出在未来三年培育100个五星级、200个四星级、300个三星级社区(村)家长学校的规划[8]。同时,2023年9月1日起,《崇左市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条例》作为广西首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地方性法规正式实施,遵循“家庭尽责、政府主导、社会关爱”的立法思想,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作了相关规定[9]。
此外,西南民族地区积极落实贫困地区“雨露计划”“控辍保学”和“两免一补”等政策要求,实现农村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一个也不能少”,免除农村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课本费和学杂费并给予寄宿生生活费,鼓励农村学生努力求学,对优秀农村学生给予奖励等。
3.村规民约成为农村家庭教育的重要准绳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基石,它在自治进程的初期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村规民约是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结合本村实际,为维护本村的社会秩序、社会公共道德、村风民俗、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制定的约束规范村民行为的一种规章制度[10]。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为了更好地开展村民管理工作都会结合当地特点制定村规民约。以云南德宏州芒市遮放镇B村为例,B村是我国爱国固边模范村,在该村村委会设置有道德小屋,以道德小屋的方式推行村规民约,道德小屋实行村民积累道德积分兑换实物、精神奖励等措施。在道德小屋积分评定要求中,“重视子女教育”“家庭成员和睦相处”“帮助留守老人、儿童、妇女”等要求成为评定标准。再以重庆九龙坡区西彭镇C村为例,将“亲乡爱家、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等优良家教家风写入村规民约中,张贴在各户门前和院落口最显眼的位置,让村规民约内容入脑入心。
(二)中观层面
本研究将政府机构、学校、村委会、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归于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的中观层面维度进行探究,得出农村家校合作偏向于单向支持状态、社会各界聚焦农村与民族特色加大支持力度等结论。
1.农村家校合作偏向于单向支持状态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儿童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大多以寄宿制的方式上学。家长只需要在每周五晚上和寒暑假将儿童接回家。但由于父母更多地忙于工作或者农活,儿童在家玩手机成为一种常态。例如,广西百色市靖西市Z村村委干部F在入户走访时发现,“孩子们一在家就玩手机,二三岁的孩子玩手机,十一二岁的孩子也玩手机,有时候玩到凌晨三四点,父母不在他们身边,没法管,爷爷奶奶在身边也不管,这样的现象挺让人着急的。”
调研发现,西南民族地区部分农村家庭教育过于依赖学校教育,农村家校合作功能较为弱化,偏向于学校对家庭教育的单向支持状态,大多数家长被动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例如,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岜盆乡R村6岁女孩的母亲H表示:“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和我们讲一些科学教育孩子的家庭教育知识,有时候通过微信群、QQ群的方式发布家庭教育知识链接,也会通过家访的形式入户指导我们怎么教育孩子。”广西南宁市横州市马岭镇A村7岁男孩的爷爷D表示:“不过一般来说我们很少主动去询问家庭教育问题,除非自己实在解决不了,才会找学校帮忙。我们只管配合学校教育,将娃娃的教育交给老师就好了。”
不少农村家长会根据学校要求购买课外书籍或者选择参加活动等,在自家孩子出现问题时呈现出“配合学校的要求开展教育”的状态,主动性并不强。
当然,部分农村家校合作和交流逐渐从“单向”走向“互动”。以广西防城港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联合防城区滩营乡中心小学创建的“三支队伍”乡村家校为例,“三支队伍”主要包括“随喊随到”专家服务队、本村的“教子有方”家长榜样队和本校的“好爸好妈好孩子”学生点赞队。通过老师、家长的推荐,家校考核确定家长的榜样,发挥示范作用,弘扬良好家风,学校的优秀学生、文艺骨干作为点赞队成员不定期点赞好爸好妈、同学中的好人好事等,充分调动家长开展家校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社会各界聚焦农村特色加大支持力度
调研发现,西南民族地区农村部分家庭的祖辈或者父母由于思想素质和知识水平较低,以及传统观念影响等原因,不能很好地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他们对孩子更多的是监护而非教育,并没有意识也不会主动开展家庭教育,缺少合理教育孩子的能力。例如,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J村5岁男孩的奶奶C表示:“只要孩子能够吃饱穿暖、安安全全就可以,教育是学校和老师的事。”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G村11岁女孩的母亲Y认为:“有时候觉得教不得法,虽然说了很多次,但感觉孩子觉得我在说教,并没有听进去,教育效果也不好。”仍有部分家庭存在棍棒教育、溺爱教育或者“拔苗助长”教育。
为了更好地提升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家长的家庭教育意识和能力,政府机构、村委会、社会组织等社会各界积极聚焦农村特色,根据农村地理位置、社会经济水平、家庭教育特点等加大社会支持力度。
(1)村级儿童之家打通社会支持“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西南民族地区村级儿童之家不断增加,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工作提供良好的教育指导场所。
以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岜盆乡W村为例,岜盆乡村级“儿童之家”的阵地设有游戏区、阅读区、活动区等,配置有桌椅、儿童玩具、书柜等,儿童之家会不定期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培训,也会组织一些包粽子、做手工等有趣的亲子活动等吸引家长和儿童参加。当地家长们反馈,“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村委通知会去参加活动,在活动中也学习了一些家庭教育知识,挺有意义的。”再以广西钦州市灵山县首家村级儿童之家为例,该儿童之家开设传承红色基因教室、心理健康辅导室、儿童议事室等,并对留守未成年人开展“一对一”问诊。
但是部分村级儿童之家形同虚设,虽然有开设但是却经常关门,在村级儿童之家运行过程中也遇到了政策、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的问题。
(2)儿童主任、第一书记成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主力之一
2023年我国已有66.7万名儿童主任,基本实现儿童主任村(社区)全覆盖[11]。儿童主任主要由村委会委员、大学生“村官”或专业社会工作者等担任,优先安排村(居)民委员会女性委员担任,主要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日常工作,是服务农村困境儿童关爱的关键一环。
云南瑞丽市姐相镇E村作为儿童主任最早的试点村之一,该村儿童主任通过走村入户,及时发现农村儿童问题并上报民政部门。在广西钦州市灵山县佛子镇Y村,儿童主任不定期入户进行家访服务,指导家长开展家庭教育。
同时,由各政府机关单位派驻的第一书记在农村挂职,由于他们知识水平、文化素质较高,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注入了新鲜血液。以广西柳州市融水县X村为例,第一书记联合村委干部通过自筹经费开设村级幼儿园,带领农村儿童走出大山,鼓励农村学生报考大学等方式,该村大学生人数实现零突破。此外,各级政府机关单位工作人员通过“一对一”精准扶贫帮扶计划开展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工作。
(3)社会组织成为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的有效力量
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将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的触角延伸至农村,成为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的有效力量。他们通过支教活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等方式深入农村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以“美丽中国”支教项目为例,该项目通过教师“服务学习”的模式,深入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开展志愿服务,支持农村家庭教育。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州城镇某完小,支教教师通过专为孩童打造的阅览室、精心设计的阅读课和丰富的阅读活动,以及引导家长加入亲子阅读活动等,支持家庭教育。不少支教教师通过开设兴趣社团方式,丰富农村儿童教育内容。
再以广西外国语学院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例,该高校大学生利用暑假时间深入广西各村屯,让农村儿童依托学校平台,通过上课、组织活动等方式,丰富农村儿童教育。广西南宁市上林县Q村村委干部E表示:“这些学生把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带到农村,也为我们开展家庭教育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思路。”
此外,西南民族地区各级妇联组织、教育部门、高校或者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组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队伍,通过暑假乡村行、“能者为师”优秀课程走进乡村、家庭教育心理咨询服务进农村等形式开展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工作。
3.重视民族文化成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特色之一
由于西南民族地区为多民族聚居区,他们有着丰富的民族节日、民族建筑等,这些已经成为开展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的特色。例如,在贵州黔南州荔波县L村,他们在过“四月八”布依民族节时,会将家庭教育内容融入民族舞蹈、民族歌曲等。再比如,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四荣乡E村建造具有苗族特色的家教家风长廊,在长廊挂置有关家教家风要求,将“家庭教育”的要求潜移默化渗透到村民心中,指导农村家庭教育。
(三)微观层面
本研究将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个人支持归于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的微观层面维度进行探究,其中,血缘包括亲属、家族关系,地缘包括邻里、同乡关系,业缘包括朋友、同事、同学关系。得出部分家长在遇到家庭教育问题时优先向家人、亲属主动寻求支持等结论。
例如,广西玉林市陆川县乌石镇I村12岁男孩的母亲W表示:“我们农村家族观念比较重,一般来说,家丑不外扬,遇到问题首先在自己家里解决,实在不行先寻求家族有名望的长辈或者亲戚来帮忙。”部分村委干部也表示,在开展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工作中,有些家长认为家庭教育属于私人领域,他们普遍认为“谁家孩子谁抱着”,不会主动向学校、村委会或者社会组织寻求帮助。
当然,部分家长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小红书、抖音、微博等网络形式获得一定的家庭教育社会支持。部分家长也会在配合学校教育过程中,主动向学校咨询有关家庭教育的事宜。
三、结束语
结合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特点,我国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工作浮于形式、社会支持主体未形成联动合力、家庭教育社会支持效果不佳等问题,亟须构建适合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的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并探寻有效的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实施路径,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提供更为有力的社会支持。
参考文献:
[1]黄正平.家校社协同育人:基础、核心与关键[J].江苏教育,2023(21):60-62.
[2]吕甜雪,安燕.基于生态理论视角的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探析[J].池州学院学报,2024(2):61-64.
[3]谭敏.农村子女教育过程的社会支持系统:功能与框架[J].学术探索,2023(10):71-78.
[4]张伟涛.儿童主任,“贴身”守护孩子们成长[N].中国社会报,2023-05-24(1).
[5]吴佳莉,孙雨萌.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政策工具的使用及优化研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J].教育与教学研究,2024(5):78-89.
[6]四川省家庭建设研究院.关于印发《四川省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EB/OL].(2023-03-28)[2023-04-01].
http://scjyy.sicnu.edu.cn/p/1/?StId=st_app_news_i_x638
156341189528415.
[7]人民资讯.今年西藏妇联组织将多举措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EB/OL].(2023-02-03)[2023-02-05].
http://k.sina.com.cn/article_7517400647_1c0126e4705903
w4tv.html.
[8]黎伊玮.广西3年内将培育600个社区(村)家长学校[EB/OL].广西新闻网.(2023-03-14)[2023-03-25].
https://new.qq.com/rain/a/20230314A094QD00.
[9]管林华.广西首部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地方性法规!《崇左市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条例》9月1正式实施[EB/OL].广西文明网.(2023-08-31)[2023-09-01].
http://gx.wenming.cn/zbgx/202308/t20230831_6659983.htm.
[10]张铭荃.村规民约对乡村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2.
[11]新华网.助力困境儿童走出困境:走近66.7万名儿童主任[EB/OL].(2023-06-02)[2023-06-05].
http://www.news.cn/edu/20230602/677fe4cf67d34e49b73
54e0f512e82e8/c.html.
作者简介:肖璇(1987—),女,壮族,广西柳州人,广西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教育、语言教育、儿童心理学。
樊蕾(1988—),女,汉族,云南宣威人,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文化与社会、教育社会学、教育叙事。
韦晔(1988—),女,壮族,广西南宁人,单位为广西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儿童心理学、语言教育。
严辉(1985—),男,汉族,广西梧州人,广西外国语学院学生工作事务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学生管理、校园文化建设。
(责任编辑: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