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生命》:复生十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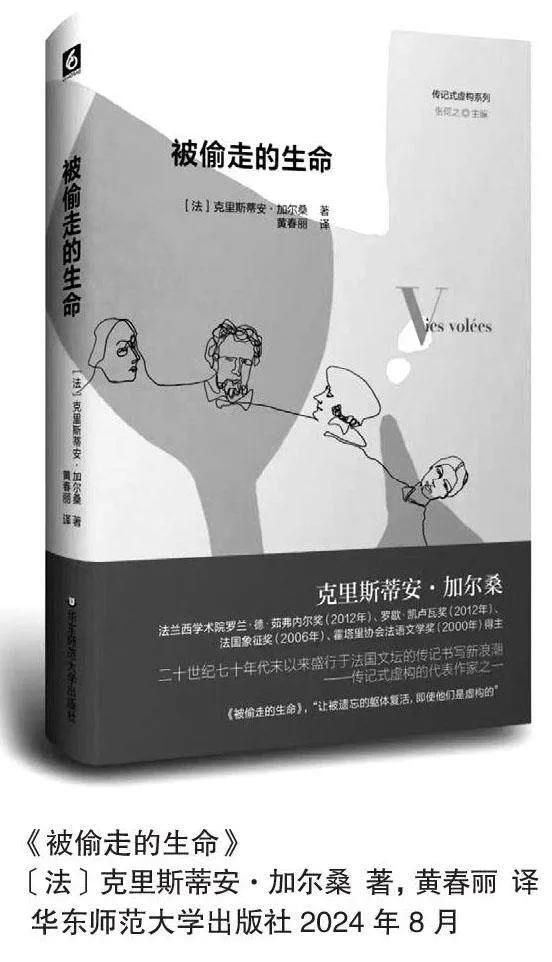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当我们快要忘记这句电影台词曾经激起的心灵震荡时,《被偷走的生命》一书不期而至。“那些交杂、模糊、被遗忘的生命,像我的生命一样丰富、不可复制和复杂,可除了名字和这些日期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在某个或许很平常的日子里,法国人克里斯蒂安·加尔桑翻阅着家谱,心中不禁涌起一种感觉、一股冲动:“挖掘尸体,让被遗忘的躯体复活,即使他们是虚构的。”复活生命!创造故事!由此,他接连完成了《被偷走的生命》等多部传记式虚构作品,开辟出自己的作家之路。
何以复生?
不言而喻,因为生命逝去了,而且这绝非我们所愿。在加尔桑看来,这种逝去是被动的,缘于被遗忘,更真切地说,缘于被偷走。偷走一词难免引人发问,偷盗生命者究竟是什么?时间、自然规律、集体无意识、个人记忆习惯……我们根据自身的阅读与生活经验,可以想出一些模糊的答案。这些也或多或少得到了作者的承认。不过,在此问题上,他另有一条思路:“《被偷走的生命》,当这个书名出现在我面前时,它显然是‘从遗忘中偷来的’。”
问题显得复杂了些。所谓偷走,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一面对应于最直接的思路,指种种外力将生命从人世间偷去,带往彼岸或者世人目不可及的其他地方。另一面则指,加尔桑(以及更多的志趣相似者)试图把那些被偷去的生命从渺远之地偷回,安置于可观可感的文字作品当中。如果理想的话,家谱上那些孤零零的名字就会转化为作品里栩栩然的人物,实现复活。
沿着家谱、人名、日期等大小线索,加尔桑的复活欲继续扩展。他捕捉到更多曾经存在的、如今可堪复活甚至亟待复活的生命。其中有些所留信息极其繁密,已被数次取用和再创造;相反,有些人的信息却寥寥无几,可能连名字都不清楚。加尔桑一边小心地重拾史料,一边大胆地加以虚构,在《被偷走的生命》里最终复活了十六个或实或虚的人物,包括诗人威廉·莎士比亚、艾米莉·狄金森、阿格里帕·德奥比涅,也包括狼修女阿涅丝、野孩子艾梅丽·斯旺,还有不为人知的肠子、西小怜等,形成了十六篇以传主命名的人物小传。
复生后怎样?
加尔桑多次谈起,他最初并不知道,自己的创作会被归入传记式虚构这种时髦的创作形式。因为像许多热爱自由的文人墨客一样,他通常不会将视线停在某某文学理论或文学热点上,而是投向广泛的写作,连同与其相互交融的多元生活体验。他写传记、小说、游记、散文,也写诗歌,还从事翻译,这些又与他的世界旅行交叉进行着。自然而然地,凡此种种皆投射到了《被偷走的生命》的主角——那十六个得以复生的人物身上。
文学中的人物素有扁平和圆形之分。扁平人物从始至终仅表现一种特质,任时空流转而岿然不动;圆形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发展变化着的,往往充满故事性。无一例外,加尔桑偷回的生命都循着圆形人物的方向。他们的复活相当于以各自的方式重新来过,借由若干我们已知的和未知的、记住的和遗漏的事情,来演绎各自的传奇。
莎士比亚当属典型。莎翁如今已家喻户晓,这几乎让莎翁的故事写无可写。而在此处,莎翁的新魂出现,没有老生常谈的光辉的文豪成长史,只有诡秘的幽灵混迹史。他是一个幽灵,从屠夫父亲手中接过尸体解剖刀和放高利贷的营生,兼顾宰割与吟诗,鬼使神差地蜕演为大诗人,创造着生命神话。不过,他去世后,却“没有几个人来送葬”。
又如西小怜。他的小传开门见山,说“此人是个疯子”。历史上查无此人,正如加尔桑自己所言,此人没有确切的原型,几乎完全出于虚构,或者说,出于作家脑海中无数人物的无数信息的提炼与整合。在西小怜的生命里,时间越向前,他疯的程度就越深。起初,他只是与林间小动物做伴;随着与人的接触,他变得爱说疯话,直到遇人、遇事、遇物都说疯话,尤其是说他从人那里学来的,也是唯一能让人听懂的一组词:“粪便”“该死的孩子”。
何必向死?
生与死的辩证法总也说不尽。加尔桑对(复)生倾注了足够充沛的情感。而让人难免惊讶的是,《被偷走的生命》围绕死亡的书写实则更为醒目,用书里的话来讲,俨然“到处充斥着死亡”。
很容易看见:人们安葬莎士比亚,用仪式宣告了他的故去;西小怜的故事以他跑向森林结尾,与莫名失踪后被纷传或被证实殒命的阿涅丝、肠子、艾梅丽·斯旺暗相呼应。传主的死亡结局,以及作为其含蓄表达的失踪或消失,它们的有关描写往往比别的生命节点更加浓墨重彩。相应地,书中的死亡隐喻也是星罗棋布,随地营造着不安的气氛。在阿涅丝周围,狼群纵情享用瘟疫和战争留下的遍野人尸;肠子的最大癖好是处理动物尸体,解剖、刨挖、摘除、缝合;吉勒姆·徳·卡贝斯当被活取心脏,这颗心脏随即被烹饪,接着被送上他对此浑然不知的情人的餐桌;卡桑德拉会生食耗子头,吮吸死人的脚趾,还会半预言、半诅咒似地指天大喊:“唉,总是要死!”无论人、物,还是环境,皆在生机感中渗透着向死性,冥冥间竟有了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的意味。
加尔桑既致力于说生,更不吝于说死,归根结底,他对死和对生一样,有着颇为积极的认识。他笔下的死,相当于现实意义上的生命终点与宗教意义上的生命轮回之始的折中。死亡好比一座桥,连接人物此刻所在的世界和将要去往的另一世界;前者怎样已然定型,但后者并无定数,因为它取决于人物本身,而非各种既有的客观规定。譬如对迷恋《圣经》和上帝的阿涅丝来说,另一世界即为天国;在饱受众人异样眼光的西小怜那里,则是无人侵扰的森林。
不得不承认,死亡被艺术化了,至少与痛苦、绝对等我们默认的消极事物松绑了,变得轻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纵然死亡书写在《被偷走的生命》中俯拾即是,我们读后仍不觉得哀痛或者恐怖,反倒偶有身处童话之感?——在这里,死亡原是水满杯后的流溢,是万物生存形态的适时更迭。
加尔桑也是直到父亲过世和在家谱面前产生晕眩,才意识到生命无痕的遗憾,才决定为逝去的生命写些什么。如我们所见,加尔桑所写生发于自身,亦穿梭于广阔的古今、东西与虚实,某种程度上在点亮人们的共同记忆,也在实现人们的共同愿想。
作者:卢荻,文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