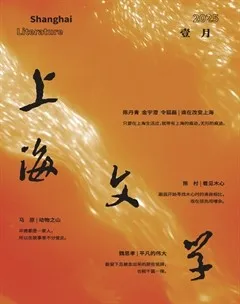西雅图:别让那些混蛋进来
1
我没有任何理由路过你家。①
——电影《单身人士》(Singles)
我喜欢西雅图正因为这里处处是洛杉矶的反面。
当飞机盘踞在城市上空,洛杉矶向你展现的是钢筋水泥的丑陋裸体:高楼、高架、马路,连绵不绝,无穷无尽。西雅图则奉上大片大片的水域,蔚蓝,平静,偶有粼粼的波光,城市像被群水环绕的一片帆叶。
在洛杉矶,路怒是家常便饭,每个人都不能等,连公交车都横冲直撞。西雅图则仿佛让我回到了美国中西部的安谧小城,所有车都会在路口停下,示意让对方先过。
洛杉矶非常嘈杂,邻居家的高分贝音乐,街上野马跑车(Mustang)的怒吼,我已经习惯戴着耳塞入眠。在西雅图,我竟然一个礼拜都没见到一辆跑车,而后才发现,西雅图人要登山,跑车不实用,这里大多数人开的都是SUV。
这张列表可以无限延长,直到我发现,西雅图可能并不欢迎从洛杉矶来的我。
我起先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去年走访美国东北部城市的时候,只要一跟别人提我现在的住处,就打开了各种话匣子,布法罗的一位女士跟我聊起她在洛杉矶市中心工作的往事,底特律博物馆的检票员听了我报出的邮编就感叹:“你从洛杉矶来!”在西雅图,各种售票处对我的邮编表示沉默,大多数优步司机不接我的话茬,最糟糕的尝试是在民宿附近的咖啡店,露天的长桌上只有另外一个客人和我,一阵风吹过,他扑蝶似的逮住了正要展翅的纸巾,我和他相视一笑。这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是破冰的绝佳机会,我对他说:“我是从南加州来的旅客,西雅图的夏天太美了。”
他扭过头去,一句话也没有跟我说。
来之前,在西雅图长大的朋友杰夫跟我提过“西雅图冷淡”(SeattleFreeze),他说西雅图人很内向,陌生人搭讪会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但我隐隐感到,“加州人”才是触发冷淡的开关。
华盛顿大学的网站上公开了该校“华盛顿州及太平洋西北地区历史”的课程资料,验证了我的直觉,近半个世纪以来,整个美国西北地区(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的假想敌都是加州。该课程每年都会采集本州学生对“加州”和“加州人”的印象,得到了如下的关键词:“不会开车”“污染”“拥挤”“节奏快”“富裕”“强势”“虚荣”“自私”“粗鲁”等等②。
对加州“印象”的拒绝背后其实是两地价值观的不同:在《西雅图:野心的魔鬼》(SeattleandtheDemonsofAmbition,2003)中,弗雷德·穆迪把西雅图独特的价值总结为“雷尼尔山因素”(MountRainierFactor),西雅图人拒绝像加州或其他美国城市那样野心勃勃地发展扩张,宁愿少挣点儿钱,有更多的时间享受自然美景,活得更自在舒心。穆迪回忆自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童年,曾几何时,他厌恶周围人对“礼貌”和“适度”的过度推崇,连提高嗓门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都会被认为是粗鲁。但等他在美国东部旅居多年之后,忽然发现,家乡的文化如此珍贵,他的修养快被东部快节奏的生活摧毁了。这位归来的西雅图之子感慨道:“荣耀、关注度和城市化意味着我们好不容易发现的天堂将会被过多的人口摧毁,因房价高涨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对此也绝不接受。”(弗雷德·穆迪《西雅图:野心的魔鬼》)
其实西雅图早已反向宣传多年,防止外来人口的涌入。或许你也听过以下这些西雅图的“污名”?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西雅图有两百多天都在下雨!”
“西雅图的自杀率全美最高!”
“华盛顿州产生了最多的连环杀手!”
几年前,当时的男朋友在找科技行业的工作,我们曾考虑过移居西雅图的可能。最后让我们打消念想的是西雅图的雨。后来,前男友如愿找到亚马逊的工作,移居纽约,而我却在辅导一个温哥华的孩子时无意中发现:距离西雅图不远的温哥华也常常下雨,但我不曾听人抱怨过温哥华的天气。俄勒冈州的城市波特兰(Portland)几乎也是同样的气候,也没有西雅图这般“臭名昭著”。事实上,美国北方绝大多数的城1e95a094cda630d8d5244172afaf340edafa8a696f24d637ca5dd69ab181e6c0市比西雅图的冬天难熬多了,和我曾经待过的冰天雪地的艾奥瓦比起来,西雅图的冬天简直温暖如春!
“这里的冬天怎么样?”是我在西雅图逢人便问的第二个问题,当然理睬我的人不是原本就认识的朋友,就是从外地移居来此的人。
“到了夏天,似乎就把冬天完全忘掉了。”三年前来此定居的作家Yan对我说。
“只是一点点雨。”唯一和我搭话的优步司机刚搬来一年,“不太糟。比起阴雨来,西雅图冷淡更难熬。”
我的民宿老板三十年前从加州北部搬来西雅图定居,十多年前买下现在位于瓦灵福德区(Wallingford)的房子。她也说了类似的话,熬过第一个冬天,一见过西雅图的夏天,她就哪里也不想去了,不适应的仍旧是:邻居搬来八年了,除了第一天打过照面,之后从来没说过话。
还是在穆迪的《西雅图:野心的魔鬼》中,我发现了那些西雅图谣言的来源——以上三条都属夸张或不实的谣言——因为头一个报道海明威自杀而名声大噪的西雅图记者艾米特·沃森(EmmettWatson)曾用自己的报纸专栏建立了一个虚构的组织“小西雅图”(LesserSeattle),口号是“别让那些混蛋进来”(KeeptheBastardsOut)。他在一九六九年的专栏里“恐吓”道:
我们可以成为不一样的第一名,让我们吸引一班自杀的人,最好是两三个世界巨星在西雅图阴郁的十二月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会登上所有报刊的头条。要好好运用我们的雨,我们可以成为骄傲的、冷漠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社群。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西雅图的爆发式的发展了。③
是的,我想了一想,即便半个多世纪之后,能被雨吓跑的人大概也就只有加州人了。
2
——嘿,猫粮生意怎么样了?
——棒极了,我现在在卖蔬菜。④
——电影《一曲相思情未了》
(TheFabulousBakerBoys)
西雅图正在变得越来越像加州城市。
当我做个单纯的游客时,我感受不到:我去城市西岸散步,看到骑着自行车的巡警(西雅图是自行车警察的发祥地)。我去派克市场看鱼贩丢鱼,到后巷见识恶心的“口香糖街”。我甚至乘轮渡去了布雷默顿(Bremerton),我对那里一无所知,只是为了站在甲板上吹吹海风。打车回到民宿,我仍意犹未尽,出门几步路就是联合湖,我就沿着湖滨走道一路走到煤气厂公园,路上是慢跑和骑行的人,湖面上则是正在起飞的水上飞机。
是在第三天,我从游人如织的太空针塔(SpaceNeedle)走路去西雅图最早的社区拓荒者广场(PioneerSquare),路上不仅经常瞥见衣不蔽体的流浪汉,更是看到一个流浪汉停在路中央,九十度弓着背脊,浑身抽搐——这很可能是吸毒过量的反应。隔着半个街区,我就绕路走开,而后似乎来到更糟糕的区域,很多门面都已经关张,另一个流浪汉模样的人从街角的便利店里刚偷了一瓶水出来,店家站在门口大喊了一声,而后摇了摇头,走回店里。我用谷歌地图查询了一下我所在的位置:贝尔顿(Belltown)街区。
当天晚上,我在“油管”上找到KOMONews拍的两部纪录片,五年前的那部纪录片被大胆地命名为《西雅图正在死去》(SeattleIsDying),在“油管”上拥有一千九百万的观影量;三年前的纪录片《为西雅图的灵魂而战》(TheFightfortheSoulofSeattle)则是前一部的跟踪和补充,我会看到白天走过的地方离西雅图“流浪汉危机”(homelesscrisis)的腹心之地只差半条街,西雅图的流浪汉人口全美第三,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
我住在洛杉矶,已经习惯了流浪汉的存在。说是“习惯”,充其量只是被迫地接受。我当然知道,大多数的流浪汉都不是坏人,而是种种社会、家庭、个人健康的因素叠加起来,引发了绝境。原先“住”在我家楼下的流浪汉叫大卫,我不知道他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他每天早晨七点会进我们的停车场(他有钥匙),取走扫帚和簸箕,清扫公寓楼所在的街区。他最后的“消失”是出面制止偷车贼,不幸中枪,楼里的老住户去医院找过他,可惜因为不知道他的姓氏,几近大海捞针。然而,尤其是二○二二年上半年纽约接连发生两起流浪汉袭击亚裔女性的事件之后(高慧民被推下时代广场的地铁,李宥娜被尾随,而后在华埠的公寓里被人捅死),我对流浪汉开始产生恐惧,而且在最近的两年,越来越频繁地遭遇流浪汉对我比画拳头,或者口出秽语。
在洛杉矶,我无法表达自己对那些有暴力倾向的流浪汉的恐惧,也无法言说我对城市立法越来越“自由派”的不满(自二○二一年八月起,低于九百五十美金的偷窃只是轻罪,不会遭受起诉甚至立案)。一旦言说,别人就会认为你“倒戈”了共和党。我曾有个学生写文章批评洛杉矶近几年的“轻罪”定义,他引用了很多福克斯电视台(FoxNews)的报道,我在反馈里指出右翼的福克斯新闻在学界被认为是不可信赖的新闻来源。但这之后,我自己搜寻了左翼倾向的新闻,也似乎难以找到公正的报道。在许多当地左翼媒体看来,流浪汉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因此,纳税人理应出钱给流浪汉设立庇护所和保障性住房,而那些高喊着流浪汉不要“来我家后院”(NotinMyBackyard)的人全是自私的有钱人。
我感到KOMONews的纪录片非常难得,这是美国广播公司(ABC)旗下的西雅图地方台,中间偏左,并不是说他们的报道完全公正,而是他们跳脱了传统的左右框架。KOMONews聚焦的不仅是街头无家可归的人,更是蔓延全城的毒品危机,他们渴望把危机重新命名为“毒品危机”——威胁流浪汉的不仅是赤贫、恶劣的卫生条件、驱逐和暴力,还有无孔不入的阿片类毒品,不择手段的毒贩,以及被毒品蚕食的中枢神经,很多成瘾并无助的人会走上偷盗的不归路,然后心智进一步被毒品摧毁——面对这样的危机,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些人的“痛苦”(suffering),如果真的要表现人道主义,政府应当干预,而不是袖手旁观。
我特别留意纪录片拿来作为对照的城市,坏榜样自然是加州城市,不是洛杉矶,而是旧金山,镜头里已经摆脱毒瘾的志愿者走在满是帐篷的街上,他说:“我们如果只是不管他们,尊重他们的个人自由,给他们暖和的睡袋,枕头和帐篷,而后对他们说,你很好,继续待着,这不是具有同情心的表现。”好榜样是罗德岛(RhodeIsland)的“希望工程”(HopeInitiative),这是全美首个州层面的对触犯法律的瘾君子的干预措施,和普通的康复中心(rehab)不同,“希望工程”全封闭,有执法人员参与,给予专门的辅助戒断阿片类毒品的药物,还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而且一旦进入,最低的“刑期”是半年。“释放”后,这些人被建议继续服用辅助戒断毒品的药物,心理咨询师定期回访,按照希望工程合作药厂的系统记录,出狱后仍然坚持服药并且定期见咨询师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三。换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三的人经过了这段干预后,自愿要过断绝毒品的日子。
KOMONews借此提出对西雅图以及华盛顿州的倡议:与其用纳税人的钱建杯水车薪的庇护所,不如建类似罗德岛的“希望工程”,帮助触犯法律的成瘾者真正重获新生。他们无疑触碰到了一个美国左右两边无法达成一致的争议点:政府究竟有没有权力强制要求这些瘾君子接受“希望工程”的干预?
当我用文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时,我的答案变得清晰。
素有美国散文诗之父之称的罗素·艾迪生(RussellEdson)有篇短小精悍的作品题为《甜牙》(SweetTooth),拙译如下:
一个似糖似蜜般美好的小女孩被吃掉了,吃她的男人长着一颗象牙般巨大的甜牙。
啊,他说,该死的牙,真是受不了。
另一个声音响起,是小女孩的父亲。他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似糖似蜜般美好的小女孩?哎哟,你嘴里那颗像象牙一样大的东西是什么?
我的甜牙,真让我受不了。
你应该去看牙医。
但他有可能要把它拔了,我不喜欢别人拔我的牙,如果他们要拔,应该去拔他们自己身上可以被拔的东西。
对极了,小女孩的父亲说,每个人都该只拔自己身上可以被拔的东西,不该管别人身上可以被拔的东西。但他又问了一次,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似糖似蜜般美好的小女孩?
散文诗有很多解读的角度,传统的性别认知,对女孩的性感化处理,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嗜甜人关于牙医是否有权拔自己的牙的辩白。你可以问任何一个美国人,撇开语境,他/她是否同意嗜甜人所说的?他们十有八九会点头,因为这是对个体自由的尊重。
但“自由”常常是三个截然不同的政治概念搅和在一起:放荡主义(libertinism)、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自由主义(liberalism)。后两者在今天常常被用来代指美国的右派和左派,如果查找历史,今天的自由意志主义主要是指二十世纪中期罗斯福新政后与其分裂的财政保守主义(fiscalconservatism),主张避免赤字开销,而自由主义则和“新政”联系了起来。《甜牙》告诫的不是左右的分野,而是“个体自由”常常成了“放荡主义”的托辞。中文翻译中,“放荡”这个词不是特别确切,专栏作家大卫·弗兰奇(DavidFrench)曾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文谈到“放荡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区别:
简单说,是权利和欲望的区别。自由意志主义者主张自己的自由,但确切知晓她的自由的边界终止于你的自由的起点。自由意志主义尊重人的个体尊严。自由意志主义者仍然是个人主义者,但是他们也主张个人的美德以及他人的权利。
但是放荡主义者被自己的欲望所主宰。他人生中的目的是为所欲为,政治的目的是获取自己想要的……放荡主义者拒绝任何强迫其个人意志的行为,但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不惜强迫他人。⑤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看到的是自由意志主义和放荡主义之间必须画清界限,前者是自由,后者是自由的敌人。政府应当使用法律捍卫自由,遏制自由的敌人。任何人侵犯了他人的自由边界,政府都有权干预,干预的方式必须符合人道,但干预应当作为保障的底线。可惜这样的想法在美国的政治语境里又和左右胡搅蛮缠,似乎你一旦赞成干预,就等于认定所有流浪汉和瘾君子都是咎由自取,就等于你不具备任何同情心,我一看完《西雅图正在死去》,“油管”就给我推荐了满屏的福克斯新闻。
在爱迪生的作品里,还可以看到更反讽的现实:一旦嗜甜者操起“个人自由”这套说辞,便能在美国畅通无阻,连这位父亲也等不及赞同,根本看不出这已经侵犯了他人的自由,甚至夺走了他女儿的性命。
而在如今美国的现实中,这些嗜甜者正是不断煽动民众思维趋向两极的政客。弗兰奇的《纽约时报》文章实际上是批评主张禁止妇女堕胎的共和党人,说这些人是借着自由意志主义的幌子来行放荡主义之实(侵犯女性的个体自由,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很像《甜牙》中吃掉小女孩的嗜甜者。而回到西雅图的街头,我看到的是行放荡主义之实的市议会民主党人,他们侵犯的是小生意人的个体自由,满足自己的政治利益。
那个白天,在贝尔顿的我落荒而逃,没有去和那位遭窃的店主聊天,但查找资料时发现,西雅图市区的不少街区(如贝尔顿、华埠国际区)的小店主都久遭失窃问题,报警无济于事——西雅图通过了和洛杉矶类似的法律,少于九百五十美金的盗窃属于轻罪,很多行窃或者攻击的人有精神问题,不会遭受监禁。在数据上,西雅图的犯罪率和二十年前相比差不多,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轻罪”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在西雅图的第四天,我去了贝尔维尤(Bellevue),这座城与西雅图市中心隔华盛顿湖相望,可以算是西雅图的郊区。我去那里的原因是听说,不少原先在贝尔顿开店的小生意人都因为治安问题开不下去,搬去了贝尔维尤。
贝尔维尤很新,市中心都是摩天大楼,到处是各大商业广场常见的品牌连锁店:芝乐坊(theCheesecakeFactory)、苹果店、香蕉共和国服饰店、香奈儿、蔻驰、巴宝莉……街上没有流浪汉,因为更富有的郊区居民要求当地立法禁止流浪汉扎营,要求地方警察依法驱逐流浪汉。
我看到了路牌上标了不远处有贝尔维尤老城区(OldBellevue),欣然前往,但没有看到老城区,看到的是一条簇新的餐饮街。我去的时候是下午,露天座位是空的,餐厅的人在休息。我开始询问:“我在写关于贝尔顿街区毒品危机的文章,想找找看从贝尔顿搬到贝尔维尤的小店主,你认识这样的店主吗?”我没有提自己来自洛杉矶。
大多数人摇了摇头,但有一位指了指斜对面的古董店,说,他好像原先在贝尔顿的,不过不知道愿不愿意跟你聊。
这是家老式家具店,多数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情景剧里经常出现的扶手椅,柜子,但我也看到了日式的陶器。店主大概五十多岁,戴了副金丝边的眼镜,我直接说明了来意,以免对方误会。
“我在西雅图长大的。”他告诉我,“本来最鄙视那些城市问题解决不了,搬到郊区耳根清净的人。这不是歧不歧视流浪汉的问题,而是我必须面对门面无端被砸,必须承担没有客人再敢踏足这里的后果。市议会的人不需要面对这种矛盾,这是一个无产者(have-not)和低产者(have-little)之间的矛盾,是低产者在为市议会的无知买单。”
我本想问他对西雅图未来的预期,但我想到一个更好的问题。
“在今年的大选里。”我说,“你会投票给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他回避我的眼神,沉默了一会儿,说:“有时候连我都觉得,我们的两党政治把人给搞傻了。”
3
清楚你自己的问题和解决你的问题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⑥
——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GreysAnatomy)
某种程度上,我仍把亚马逊视作自己不共戴天的情敌,我仍记得前男友找到工作时的兴奋,当时还在疫情末梢,不需要去办公室上班,但他一天也不能等,立即驾车向纽约进发。我当然为他高兴,可也忍不住感到心碎,我在想做父母的要多么大度,才能忍心看着孩子迫不及待地离开自己。
我拖到行程的最后两天才去亚马逊位于西雅图联合湖南岸(SouthLakeUnion)的全球总部,三颗硕大的玻璃球拔地而起,玻璃球一侧的园区开放给公众,中间有辆餐车,给公司员工以及来往的行人免费派发香蕉,餐车旁有供孩子玩乐的益智游戏,两侧的台阶可以歇脚。绕园区走,隔几步就有一块路牌,扫描二维码后,会连到公司企业文化的宣讲,比如狗公园所配的文字是亚马逊非常重视员工的“劳逸平衡”:员工带宠物狗上班,它们也可以寄放于此,有专人负责照看。
我觉得亚马逊的宣传似乎有点用力过猛,并且欲盖弥彰。二○一九年,亚马逊斥资一百五十万美元,试图通过商会,在市议会里“植入”一批亲信,此举被公众得知后,不仅事败,次年西雅图市议会还立法禁止外资持资超过百分之五的企业资助本地候选人,其中就包括亚马逊⑦。市议会一直把亚马逊描绘成西雅图流浪汉危机的罪魁祸首:正因为他们带进了一批高收入的外来人口,害得西雅图当地人负担不了水涨船高的房价。
亚马逊也不是省油的灯,既然市议会如此宣传,比起乖乖交税,他们更愿意直接捐赠给当地的公益组织“玛丽的家”(MarysPlace),建造给流浪汉的庇护所,以此抵税⑧。换句话说,亚马逊也在暗示公众:我们已经造好庇护所了,为什么流浪汉还是越来越多?会不会是因为无能的市议会只是在拿我们做替罪羊?
前男友搬去纽约后不久我们就分手了。那年冬天,我去纽约见过他最后一面,那是个周日,他出来和我以及两个朋友在中城匆匆吃了午饭,赶回办公室加班。提起工作,他没有表现出兴奋,也没有怨言,只是说了句“工作都差不多”,我不知道他是否求仁得仁。此刻,我坐在西雅图亚马逊园区的台阶上,看着坐在玻璃球边缘的员工,感觉很像在校园里看大学实验室里的研究生,他们似乎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竞争。
玻璃球实际上就是三座温室,因为集结了世界各地的植被而更显昂贵奢华,按照亚马逊对设计理念的阐释,这是为了重建员工和自然之间的纽带,这样员工更能打开思维,迸发想法。但我越看越疑惑,西雅图这座城有山有水有森林,为何不去接触真正的自然,非要圈养在此与人造的自然相处?
二○一五年,《纽约时报》专门做过一期对亚马逊内部工作环境的报道,采访了多位在职和已经离职的员工,最让我发怵的不是践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办公室文化,也不是“每一个员工都在办公桌前哭过”这个事实,而是以下这句前员工发自内心的表白:
“我渴望成功,已经上瘾了。我们几个同事,都觉得在那里工作是可以获得自我价值的毒药。”⑨
这些人,和穆迪笔下那些宁愿少挣点钱,也要有更多时间享受自然美景的西雅图人比起来,是多么不同。
就在离亚马逊总部不远的南联合湖公园,我似乎看到了这两种价值观正在下一代人中激烈交锋。
我先经过了木船中心(TheCenterforWoodenBoats),看到家长带着孩子,双双穿好救生衣,来学开船。
而后我来到历史与工业博物馆(MuseumofHistory&Industry),这栋老建筑的外观乍看和东岸的博物馆没什么不同,但一走进去,空旷得像篮球馆,一侧的霓虹灯打出关键词“创新”(innovate),四周是一系列多媒体互动展区。简直是微缩版的商业课:先想出一个革新的创意,写下贴到墙上;下一步,大胆实践!不同的电视屏幕播放着不同的本土成功案例(星巴克、微软、亚马逊)——成功就是这么简单,只需要对日常的生活进行创新!
“创新”(innovation)这个词轰得我头昏眼花,但我身边那些孩子却好奇地按着按钮,急于探索下一个案例。
匆忙逃离之后,我总觉得,自己好像不久前也看到过“创新”这个词的高频次出现。想起来了,是在亚马逊总部,玻璃球就是“受自然启发的创新设计”,亚马逊的DNA是服务并为客人“创新”……很快,我还会知道,历史与工业博物馆里的这座展馆就叫做“贝索斯创新馆”,赞助人是亚马逊的创始人及执行主席杰弗里·贝索斯(JeffBezos)。
或许亚马逊只是想从娃娃抓起,在新一代人眼中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并不是要夺走孩子们的木船、沙滩和雷尼尔山,但我不知道被“创新”和“成功”炮轰长大的会是怎样的一代人。
我给杰夫发了短信,说:“我好讨厌‘创新’这个词,你从小到大也一直听到这个词吗?”
“如果你能待久一些,”他说,“你会听到很多本地人和科技企业之间的冲突,这已经在西雅图上演了三十年。联合湖南岸以前是一大片停车场,国会山街区原本是很有艺术气息、酷儿很多的地方,现在都已经成了亚马逊的办公楼或者夜生活去处。我也厌恶‘创新’这个词,但很可惜,科技企业带来的文化似乎势不可挡。”
半个多世纪前,艾米特·沃森用“雨”和“高自杀率”唬住了加州人。而今,西雅图要用什么阻挡科技文化的入侵呢?
在我准备离开时,这座城给了我最后的惊喜。
我只是多了一点儿时间,顺道来华埠国际区的陆荣昌亚洲博物馆(WingLukeMuseum)看看,也顺道参加了一场博物馆组织的免费游览。导游是个年轻姑娘,白人,T恤背后印着“停止资助警队”(DefundthePolice)。我走进了十九世纪末来西雅图修铁路的华工所住的旅店单间(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把椅子),摸着宗族联谊会里的麻将桌,看到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之后,用来填补劳力缺口的菲律宾裔以及日裔劳工留下的家什和服装。我们的导游在一张日裔农场工人劳作的黑白照片前停下,问我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贝尔维尤的地方。我举手说我去过。
她很意外,指着照片,说这座农场的所在地就是现在的贝尔维尤市中心的购物中心。“其实华盛顿州的白人早就想占据这块土地了,”她补充说,“是他们帮助散布了对日裔的恐惧,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二战时对日裔的拘禁。”
我在已经停刊的《西雅图国际主义》(SeattleGlobalist)的档案里找到了这段往事,贝尔维尤广场的建造者米勒·弗里曼(MillerFreeman)就曾通过旗下的报纸煽动对日本人的仇恨,也是弗里曼和其他贝尔维尤的白人,一等日裔被关进拘禁营,就开始大兴土木,促成了贝尔维尤如今的摩登景象⑩。
“‘二战’结束后,”导游告诉我们,“绝大多数日裔美国人没有回来,因为创伤,也因为当时西雅图地区的白人不欢迎他们回来。”
这是沃森和穆迪都不曾提到的西雅图“排外”的另一面,半个世纪前的“西雅图人”有着狭隘的种族定义,若再往前追溯,十九世纪中期西雅图立市时,最早对“流浪者”(vagrant)的定义是晚上九点后在公众场合行走的印第安女性。日裔美国历史学家梅根·朝霞(MeganAsaka)的家族亲历过被西雅图白人驱逐,在她眼里,“西雅图冷淡”的根源正是白人至上主义(WhiteSupremacy)。那么,作为少数族裔的我还应当支持西雅图的文化保守主义吗?
我依然支持,前提是所有捍卫“雷尼尔山因素”的人都被视作西雅图人,无论族裔,无论职业,无论来自哪里,也无论他们逗留多久。
我想起前一天Yan带我去西雅图西北部的巴拉德水闸(BallardLocks),我们正巧看见一只小海豹在水里翻筋斗,而后突然“嘣”一声,有如炸开的鞭炮,小家伙不见了!Yan担心地绕着水闸转,搜寻海豹的踪影,半晌后我们才看到一旁的标识,原来这些响声是为了吓走猎食者,保护三文鱼苗,不会对动物产生任何伤害。
那一刻,我感到没有人比Yan更像一个西雅图人。
①原文为“Iwasjustnowherenearyourneighborhood”,是男主角第一次敲开女主角的家门后说的台词。
②“LessonOne:WhoBelongsinthePacificNorthwest?”CenterfortheStudyofthePacificNorthwest,UniversityofWashington,link:https://www.washington.edu/uwired/outreach/cspn/Website/Classroom%20Materials/Pacific%20Northwest%20History/Lessons/Lesson%201/1.html.
③转引自FredMoody,26.
④原文是:JackBaker:Sohowsthecatfoodbusiness?
SusieDiamond:Terrific.Imdoingvegetablesnow.
⑤DavidFrench,“TheNewRepublicanPartyIsntReadyforthePost-RoeWorld,”TheNewYorkTimes,Nov.12,2023,link:https://www.nytimes.com/2023/11/12/opinion/ohio-abortion-republicans.html.
⑥原文是:Beingawareofyourcrapandactuallyovercomingyourcraparetwoverydifferentthings.
⑦GregoryScruggs,“Amazons$1.5millionpoliticalgambitbackfiresinSeattleCityCouncilelection,”Reuters,November11,2019,link: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technology/amazons-15-million-political-gambit-backfires-in-seattle-city-council-electio-idUSKBN1XL09B/
⑧“AmazoninSeattle:TheRoleofBusinessinCausingandSolvingaHousingCrisis,”HarvardBusinessReview,Aug.23,2024,Link:https://hbr.org/podcast/2024/04/amazon-in-seattle-the-role-of-business-in-causing-and-solving-a-housing-crisis.
⑨JodiKantorandDavidStreitfeld,“InsideAmazon:WrestlingBigIdeasinaBruisingWorkplace,”TheNewYorkTimes,Aug15,2015,link:https://www.nytimes.com/2015/08/16/technology/inside-amazon-wrestling-big-ideas-in-a-bruising-workplace.html.
⑩AliaMarsha,“HowBellevueBusinessmenwhostokedfearsbenefitedafterJapaneseAmericanincarceration,”Feb19,2017,TheSeattleGlobalist,link:https://seattleglobalist.com/2017/02/19/anti-japanese-movement-led-development-bellevue/62732.
AdamWillems,“MaybeItstheSeattleFreeze,MaybeItsWhiteSupremacy,”Jun.13,2023,TheStranger,link:https://www.thestranger.com/books/2023/06/13/79034679/maybe-its-the-seattle-freeze-maybe-its-white-supre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