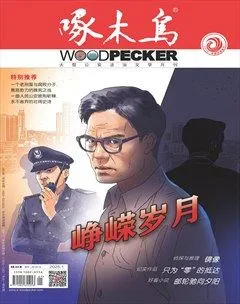雪落黔西北

一
那年寒冬来得好早。才过寒露,凛冽的风从阿勒河谷北面刮来,像一群群盯上肉摊儿的饿狗,呜呜地在黔西北的山山岭岭打着转儿。
我一早离开水城,蹚过磨刀溪绕开枷担湾爬上和尚岭向打鼓坪方向赶。最后一程是水西的菜籽坪,那儿是通往打鼓坪的必经之路,再往前就是彝区了。水西刑警坑卫东在那儿接我,他懂彝语,熟悉那一段路。这一带是乌蒙山区,山挨山,岭挨岭,羊肠小道大都沿水流湍急的河谷和刀劈火烧一样光秃秃的山脊兜兜转转。我走得很辛苦。
没人看得出我是个刑警。我白净斯文穿着休闲,戴一副金丝眼镜,系一条大方格羊毛围巾,妥妥一民国文艺青年范儿,复古,帅气。我没啥行头,只挎了台理光KR5单反相机,手枪贴腰掖着。事实上,我在刑警队技术室搞照相,干的正是拍拍画画的事儿。照相前我是警犬员,带一条叫佐格的德国牧羊犬,佐格病死后我才转的行。老邓说:“你一直就是部队头的炊事兵、司号员,不是正经打仗的兵。”我来贵州的唯一原因是我和胡锅巴小学同过学,一起在一个叫干坝子的山村长大。小学毕业那年冬天,胡锅巴突然离家出走生死成谜。二十年后再次现身,已经是一个背负两条人命的杀人逃犯。胡锅巴列省级通缉犯第三,照片是我从小学毕业照里翻拍的。理论上讲,我是唯一一个真正见过胡锅巴的警察。我从技术室借调到重案组和老邓搭档,任务是辨认胡锅巴。其实我心里明白,就让胡锅巴现在站我面前我也认不出他来。我对胡锅巴的记忆像一堆破布头,零零碎碎能拼接出一个爱流鼻涕看人总像是在剜你一眼的小屁孩儿。我不能说出口,说出来我就得回技术室,继续照相。
“眼神!人不管咋变化,眼神永远不变!”我记得胡锅巴用眼剜人的样子,我拍胸脯说。
“也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老邓笑着说,他是破案高手,下川东有名的“邓弯刀”,一张瘦脸上过《人民公安》封面。
半月前有线索从贵州方向传来,胡锅巴躲在黔西北打鼓坪一个叫“天叫水”的矿区,给一些黑心矿主当打手。杀人前胡锅巴在广东东莞一带当鸡头,专门从黔西北诱拐当地女孩儿到广东。贵州警方也在通缉胡锅巴,罪名是拐卖妇女。重罪吸收轻罪,如果贵州警方抓住了胡锅巴,程序上讲他们是该移交给我们四川的。贵州警方有个打拐小组正在黔西北抓捕这些鸡头,领头人是传奇的警察英雄沙玛尔呷,他是彝族人,打拐追逃专家。我和老邓只需赶往黔西北和沙玛尔呷接上头,在沙玛尔呷逮住胡锅巴后,由我掰过胡锅巴脑袋,怒喝一声“胡锅巴!认得我吗”,这事就算大功告成。以上是标准套路,至少出发前我是这么想的。
老邓对与沙玛尔呷的这场“双雄会”满心期待,一路上亢奋得像打了鸡血似的。可刚到水城,老邓慢性支气管炎的老毛病就犯了。他蜷缩在旅馆火塘边,恶狠狠诅咒着该死的天气,直到喉咙像一口破风箱丝
儿丝儿地没个囫囵气儿了,才掏出他的六四式手枪瑟瑟缩缩地递给我,像一个絮絮叨叨的大姨妈说了一大堆话后才挥挥干柴一样的手催我上路。他的手还没落利索,我早一步跨出门去了。
“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我好歹也是三个六月三个冬过来的警察吧?”一路上我都在嘀咕。打小山里长大,虽说不能虎步上山兔步下岭,一般山路也不在话下。
下晌时分,当我走近一座地势稍稍平坦的小山坳时,只见山坳里稀稀朗朗长了些栎树,一个年轻人正盘腿坐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小伙儿细高细高的,穿一身水磨蓝牛仔服,额头上架了个宽边墨镜,嘴里有一下没一下地嚼着泡泡糖。他斜我一眼,吐出个乒乓球大小的泡泡来。
“这家伙不会是坑卫东吧?”我心里问自己。虽说贵州地无三尺平,有屁股大一块稍稍平坦点儿的地方就敢叫坪呀坝的,可眼前这个坪也忒小了点儿,不该是菜籽坪呀。这么想着,我和那小伙儿错身而过。
“喂?徐志摩?就这么走了?”那小伙儿在我身后吆喝了一句。口气好邪性。
“你叫我吗?我可不是徐志摩。”我半转脑袋,撇撇嘴说。
“没人管你叫徐志摩吗?”那小伙儿一骗腿下到路上,拍拍屁股伸手说,“坑卫东!水西刑大的。告诉你,我就姓坑,别问我为啥这个姓。”
“呵呵!倒是真有人说我像徐志摩的。”我伸手碰了下坑卫东的手,随手递上一根烟,说,“朱进!添麻烦了。”
“我不麻烦!麻烦的是沙玛。”坑卫东接过烟,掏一只防风打火机砰儿一声点着了,手一抖合上盖儿,抬腕看看表说,“看不出你还很能走的!我估摸你怎么也要五点才能到菜籽坪的。你这身板儿,真不像干我们这行的。”
“我复古,你新潮,我们都不像干这行的。”我看看天色,微微含嘲说,“我们该不是在这儿和沙英雄见面吧?”
坑卫东哼了声,径直往旁边栎树林走。我迟疑一下跟了去。走没一阵,隐隐听得訇訇的水声。还纳闷间,我们已经站在一道绝壁之上了。远远的山脚下,一条湍急的河流从遥远的群山间蜿蜒而来,翻花卷流,汹涌咆哮。隔河是一座更高的山峰,黑沉沉的。一团岚烟缓缓飘过,浅灰色的天光将山脊勾勒出一廓若有若无的虚线。
“我们脚下是雉街小河!更远的地方是小韭菜坪,贵州屋脊。”坑卫东努努嘴,又看了看表。
我没有接他话茬儿,只纳闷这悬崖绝壁上如何和沙玛尔呷见面。狐疑间,坑卫东从怀里掏出一个对讲机,调调频道开始用一种听不懂的话呼叫。不一会儿,对讲机里有了嚓嚓声。远远那道虚线上有了两个树桩一样的人影,隐隐能看见有一个人也举着望远镜望向我们。坑卫东开始懒洋洋地和对方说话,时不时松了应答键仄脸和我说话。
“沙玛问,就你一个人来了?我替你答了,嗯。他又问,你真能确认对象不?我也替你答了,能。他还说,你不像干我们这行的,太奶了不能带你进山,我还是替你答了,行。”坑卫东嗤笑说。
“我能和沙英雄说说话吗?”我隐隐不快,伸手想要对讲机。坑卫东却收了对讲机往怀里一插,耸耸肩,摊了摊手。那边山顶上,两个人影也缩到山脊线下面去了。
“沙玛说‘针鼻大的眼儿,磨盘大的风’。”坑卫东不再说啥,自顾往回走。走下山洼,他转头和我撞了撞眼光,揶揄道。我还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坑卫东啪一下吐了泡泡糖,不屑道,“大英雄当然架子大!不过也好,坐等验货,你可以作古正经当回摄郎呢!我给你选个离小韭菜坪不远的镇子等消息,那儿是摄郎的天堂。”
“你当我真是来当摄郎的吗?见不着沙英雄,我们的邓老英雄会很失望的,他可是指着这场双雄会来的呢。”我闷声说。
“你们真把沙玛当回事了。”坑卫东又哼了声,瞪我一眼说,“你别一口一个沙英雄。人家不姓沙,姓沙玛。你能管令狐冲叫老令,欧阳锋叫老欧吗?”
“哦!领教领教了。”我没好气地回道。
二
接下来小半月,我一个人困在水西城北一爿小旅社,进退两难。除了看电视就是没日没夜混混沌沌地睡。这天迷迷糊糊正睡着,听见窗外淅淅沥沥的冻雨打在楼下一篷芭蕉上,嘣嘣嘣格外地响。冷飕飕的风从窗缝儿钻进来,满屋子荒凉的味道,让人觉得不是身处黔西北而是漠北了。这样的天气更让我沮丧,让我怀疑沙玛尔呷、坑卫东他们早把我给忘了。
刚开始老邓还见天打个电话到旅社,说一句喘半口。我厌气得慌,直说叫他等着。老邓也就不打电话了。两天不打,我又慌了。这天,我干脆不起床,捂在被窝里听寒风在窗外打旋儿,一会儿呼呼的,一会儿嘘儿嘘儿的。忽然,听得楼下有人大声武气说话。
是坑卫东!我一掀被子下了床。
下楼一看,果然是坑卫东。他大大咧咧坐在火塘边,满身的霜花。手一抹,霜花四溅,霜花掉进火塘,吱吱直冒烟。我顾不上矜持,几步过去,殷勤地递烟打火。坑卫东“嘘嘘”着吸了半截才开口说话。没说几句,我心一下子又凉了。他没带来啥惊喜,却让我去见见菊子。
这个菊子我知道。她真名叫杨大菊,川东夔门人,是胡锅巴在广东东莞认识的一个坐台小姐,三个多月前从东莞那边赶到贵州找胡锅巴。一到水西,人就病了。胡锅巴刚到东莞那阵,菊子还在厂里打工,拗不过胡锅巴怂恿坐了台。胡锅巴靠菊子坐台吃了一年软饭,然后才慢慢做大的。据早前群众举报,胡锅巴和菊子感情很好,一直有谈婚论嫁的计划。天叫水一带有五十多个矿山,一条单沟直通矿区。别说警察,任何一个生人进去,马上就能被发现。只有菊子晓得胡锅巴在沟外的窝子,盯住那窝子才有办法。我和老邓来贵州前,沙玛尔呷没少在菊子身上下功夫,但收获都不大。
“沙英雄都没搞定,我哪好去炒冷饭?”我直摇头。
“你,还有你们那个‘邓弯刀’,都把沙玛当神了。”坑卫东冷笑一声把烟头往火塘一丢,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担心得罪坑卫东,又把我一丢不管了,急忙赔笑说:“追逃这行,沙英雄不说是出神入化也算是行家里手吧?我是怕贸然去见菊子,乱了他的节奏啊。”
“徐志摩!你还真中蛊了。”坑卫东一撇嘴,挖苦道,“沙玛的节奏无非装神弄鬼。太原始,充其量刀耕火种。”
“是吗?墙内开花墙外香,你见多了,不足为奇吧?”我哂笑一下,随口问,“我们干坐着也是无趣。说说沙英雄装神弄鬼的案例如何?”
坑卫东望望我,还真说了沙玛尔呷的两则案例。一次沙玛尔呷去广东潮州一个村子解救一名女童,正愁没法子进村,得知当地鼠患成灾,灵机一动,去市场买了一笼子小猫,大大方方来到村里,一边吆喝卖猫一边观察。一个老太太牵了个小女孩儿出来买猫,讨价还价间,沙玛尔呷顺手摸摸那女孩儿脑袋,耳朵后面露出一块红色的胎记,正是要解救的女娃娃。再一次沙玛尔呷去福建龙岩解救一个被拐少女,那家人正做丧事,人来人往一片喧哗。沙玛尔呷学着别人的样子买了床踏花被当祭幛,扛了个花圈径直去到那家,一番披麻戴孝磕头作揖,便和被拐少女用家乡话接上了头。接下来的事就好办多了。
末了,坑卫东正正色,认真说:“这个菊子不知得了啥病,躺洪椿坪卫生院要死不活的。沙玛去了几趟,啥法子用了,油盐不进。你知道为啥?攻心是门技术活,这是沙玛的软肋。我看你长得秀气,眼善,任谁也不会相信你是警察,说的又是一口四川话,兴许你真能套出她的话来。”
“这……”我有些犹豫,也有些动心了。
“你爱去不去吧!”坑卫东站起身,拿手掸掸屁股上的灰土,淡淡说,“沙玛尔呷不是给你们摆谱吗?你手里有了线索,就该轮他围着你转了。”说罢,头也不回出门去了。
“死马当活马医!做算医死了也比困在这儿强!”想到这里,我心一横。出门招了辆电动摩托车,一路突突着到了洪椿坪。
洪椿坪是一个小乡场,在乌江支流六曲河北岸。早前这儿是一个乡政府的所在地,由几条小溪冲积而成。这是个真正算得上坪的坝子,河滩开敞,四周青山森然如墨。凛冽的风从六曲河谷刮过来,落叶翻飞,寒气逼人。刚下麻木车,一颗颗冰凉的雪籽就似有似无地从天上抖落下来,掉进颈窝了。
乡卫生院是一个四合院,菊子住着一间单独的病房。病床靠窗,就她一人。“论说也不是啥疑难病,一般的心衰。刚开始还可以楼上楼下走走,转天便卧床不起了。兴许是找她的人多了,心理负担重吧?”当班医生咕哝道。
我犹豫一阵折回卫生院天井。进门时我见院坝有几兜结香,金黄色的花朵在枯叶满地的院子里格外艳丽。我走过去,也不管有没有人看着,伸手掰了两枝攥在手里。
菊子脸色惨白地躺在床上。兴许是冷,脖子让被单严严实实捂着,头上戴了毛线头套,整个人像一条肚皮朝天、泅在水槽里奋力喘气的鱼。见我进来,微微动了动脑袋,一动,脖子上围着的一条围巾露了一角。围巾已经泛旧,俗气的大红却让菊子的脸稍稍有了些生动。我把结香插在她床头柜边的水杯里,菊子偏头端详一下,喑哑道:“好乖的花哟!只是我不认得你呢!”“我认得你就好了。”我掩饰着掏出支烟,问,“我挨窗边抽支烟可以吗?”菊子眨了眨眼算是作答。只一眨,长长的睫毛带动下,眼睛似乎也生动了。她依旧沙着嗓子说:“好想抽一口烟。”我想了想,探过身把烟嘴递到她嘴边。“谢谢!”菊子拿发绀的唇碰了碰过滤嘴,轻轻摇了摇头。
我们再不说话。菊子一直看着窗外远远的、黑黢黢的山峰,翻过山峰该是四川地界。她一定是在想着家乡想着胡锅巴了。我心一悠,有些后悔不该来这儿了。这么想着,只好和她一起把目光投向同一个方向。
半晌,菊子才有气无力地问:“你也是来找东儿的吧?”“东儿”是胡锅巴在东莞的诨名。菊子主动提起他,那就有戏了。我压住暗喜,诚恳地点了点头。
“也难怪!谁会来真正看我呢?除了鸡头、混混就是警察,都想找到他。你是唯一一个带花来的人……其实,我也想见到东儿!不为别的,只为我为他落到这步田地,为了我们的当初……我也是有心一了百了了!他是我太多太多疮疤中的一块。疮疤结壳了,摸着痒碰着了痛,要有心揭了它吧?恐怕还会带出些血呀肉的来……”菊子一口气说完,腮上洇出两块红红的血晕,瘆人得慌。
我忙倾了倾身子,止住她说:“菊子!先不说东儿,喘口气好吧?不管我是做啥的,眼下我都不关心东儿在哪儿。”
“你说假话了!你把假话说得真!”菊子苦笑一下,喃喃说,“噶哒场母猪街,‘月月红’有个洗头妹叫红月。说是贵州女子,其实是四川妹……你要是找到他了,告诉他,‘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不管下场如何,我要送还一样东西给他……当年多好哇!一条十块钱的围巾能让我快快乐乐过一个年……”
菊子的话像还没说完,却又虚弱地闭上了眼睛。我一时不知道该走还是留下,满心像亏欠了菊子一样。好一阵死一般的静寂后,菊子喃喃道:“你走吧!风大,带上门。”我背心一凉,伸手替菊子抻抻被角,压了压那条围巾。“谢谢!他杀过人不假,可他也没多大蛮劲儿,你们抓他的时候下手轻点儿……”菊子吐口游丝样的气,细声说。
我缓缓退出房间,轻轻带上房门。房门咔嚓一声锁上,我贪婪地深吸了一口门廊里潮乎乎的霜气,心里却空落落的了。
三
“我把线索转告给沙玛了,沙玛好像兴趣不大。”两天后,坑卫东开了辆破破烂烂的警车来到旅社。他熄了火,摇下车窗懒洋洋地和我说道。我还没醒豁过来,坑卫东又说,“我猜他也不是不感兴趣,只是怕人抢了他风头。他说他就在噶哒场,说不定是摘这个桃子去了!”
我没打算坑卫东能带来啥好消息,只等他接着说啥。“杨大菊死了!”坑卫东重又打燃车子,冷不丁说了句。

“啥?你说菊子?她死了?”我脑袋嗡地响了。
“嗯!死了!”坑卫东伸手递过那条红围巾,淡淡地说,“她用这条围巾系在床头,身子一歪,就这么死了。”
我接过围巾。围巾暖暖地贴到掌心的一刹那,我像被电击了一般。还没回过神,坑卫东的车已缓缓开走了。
“请你转告沙英雄,我这就去噶哒场,我要会会他!”一股莫名的怨气涌了上来。我攥着围巾几个箭步追上去,冲坑卫东大声嚷嚷说。
我回旅社给老邓打电话,墙上贴着一张贵州省地图,那个噶哒场就在水西西北角。我三两下收拾了东西直奔火车站,赶一辆绿皮车到了一个叫石坪的小站。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举目四望,到处都是乳房一样高耸的小山包。这儿也没啥坪,石山倒是满山遍地。站前坝子泥泞不堪,阵阵寒风夹杂着碎雪扑面而来,我打了个寒战。
坝前一小饭馆开着门,一个小姑娘拿了把篾笆扇使劲儿往蜂窝煤炉子里扇风,我问了好几声她才应声。“噶哒场?我哥跑这段路的。”接着,小姑娘扯起喉咙叫了几声,不一会儿,一个瘦精精、黄泥鳅样的小伙儿揉着眼睛钻了出来。
“噶哒场?你是‘色狼’吧?”“黄泥鳅”打着哈欠问。
“地图上看这名字好耍,说来就来了。”
“啥子好耍哟?噶哒就是噶哒,噶哒是哪里的意思,你这也不懂?”“黄泥鳅”嘲笑我没见识。说归说,还是领我上了一辆破破烂烂的面包车。
面包车哼哼呛呛上了路,癞蛤蟆样跳着。“黄泥鳅”嘴里哼着歌,大口大口吧嗒着叶子烟。窗外不时有穿着破旧,背着小山样的柴草、红苕藤的砍柴人和农妇侧身让路,大多穿着粗布彝装。胡锅巴选这种地方隐姓埋名,也算是下苦功夫了。我心里叹说。不一会儿,前面出现一块敞亮的坝子和一片紧凑的房屋。“黄泥鳅”转头对我说:“噶哒场到了。”
下了车,我一片茫然。前方蹲着一个穿右衽大襟、披擦尔瓦(一种彝族服饰,形似斗篷)、斜挎烟包的彝族汉子——裙裤宽大,头上的天菩萨直直地指向天空,嘴里的烟绺儿一口口吐出来又被狂风转瞬间刮得无影无踪。我踌躇着往前走,刚过那汉子,那汉子兀地起身把我轻轻一搂,低声说:“沙玛尔呷!跟我走!”猛一听沙玛名字,我的心炸了一下。不好看他,只和他肩并肩往前走。
进了一家小院,一个标标致致的彝装女子迎了过来。沙玛尔呷过去和她说了几句当地土话,女子马上改用普通话热情招呼道:“欢迎欢迎!先歇息歇息吧。”她嘴上“请,请”着前面领路,带我们穿过一截灰暗的走道上了楼,眼前豁然开朗。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亮堂。窗外是大片收割后的稻田,黄灿灿的谷茬儿间一群群麻雀飞来飞去。“师傅,您觉得怎么样?”女子问我,眼睛却望着沙玛尔呷。
“你就说贵州话,我表弟走南闯北瞎照相,能听懂的。”沙玛尔呷像不耐烦地说。我便知道我该是沙玛尔呷表弟,一个摄郎表弟了。
“还行!也住不了多久的。”我含混着说。
“好的,我沏茶去。对了,我叫小桃,师傅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女子甜甜地说。这次是望向我了。
待那小桃走了,沙玛尔呷掩了门,解了擦尔瓦,我这才细细看了他的容貌。岁数看着比我大不了多少,五短身材,背脊微驼,脸庞瘦削黝黑,稀稀拉拉的胡须微微发黄,布满血丝的小眼睛深深地嵌在耷拉着的眼皮下,慵倦无神。这种人撒人堆里,真是一点儿不起眼,却能装啥像啥,天生的刑警料子。我还没开口,沙玛尔呷却先说:“这个小桃,早年去南方攒了不少钱,前几年回到噶哒场,开着这爿小店,做的兴许还是老本行!”
我莞尔笑笑说:“难得她这样刻苦!和特区相比,这儿实在是太苦寒了。”
沙玛尔呷低声说:“老弟!母猪街不在噶哒场,在天叫水附近一个坝子。原来就一个乡场,这几年矿山多了,云贵川的洗头妹来了不少,逐渐成了条不是街的街。你那线索不新鲜,我早有掌握。你既然来了,就场上等着。”
我心一沉,接着就有些火气了。正要发作,沙玛尔呷突然没来由地问舅舅身体还好吧、表妹婚礼几时办,等等。问着问着门就开了,小桃用托盘端了两小碗黑乎乎的东西进来。我敷衍着和沙玛尔呷搭讪,接过小碗说了谢谢。小桃刚走,沙玛尔呷说:“我晓得你心里有气,你要嫌冷清,先回水西等着也行。”
“沙英雄!”我开口想说点儿啥。
“就这样定了。”沙玛尔呷举举手,口气是不容商量的。见我一脸尴尬,沙玛尔呷挤了丝笑容,指指小碗说,“尝尝我们贵州擂茶吧?吃完我要睡一会儿。你要有闲心,可以出去转转,记住紧开口慢开言就行了。”说罢,沙玛尔呷狠狠打了个哈欠,有气无力地端起自己那只碗,连刨带喝吃了大半。放了碗,两脚后跟一蹭脱了胶鞋,扯过被子搭在肚子上闭了眼睛。旋即又睁开,懒洋洋说,“楼下那妖精,小心点儿。”
我苦笑一下没有搭腔。肚子也饿了,干脆用心吃起擂茶来。茶还没吃完,沙玛尔呷已经打起了呼噜。兴许是他脱了胶鞋的缘故,屋子里有股死鱼的味道。不敢久留,我端了空碗下楼。
楼下没见着小桃。我放了碗筷,走出小院,信步到场上走了几圈。没啥去处,便站在场口土坡上发呆。想这沙英雄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我想申辩一下也找不着人。正懊恼着,听得附近有女子在哼唱山歌:
郎骑白马过大山,
脚蹬木叶对对翻。
走遍千山来约妹,
问妹心欢不心欢。
妹骑红马漂过江,
踏起浪花声声响。
四海漂流和郎见,
强过家里天天想……
搭眼一望,正是小桃。小桃蹲在溪边,正涮洗一筐萝卜青菜。想过去搭搭讪,脑海里闪过沙玛尔呷刚才说的话,忙缩了脚往回走。风越刮越大了,朔风搅动高天上的乌云,翻江倒海般涌动着。要下大雪了!这么想着,心下更灰灰的了。
四
回到小院,小桃和一个打下手的小姑娘不紧不慢张罗着饭菜。见我进门,伸手递过一个小筲箕,装着满满的刺梨。刺梨是长在大山上的一种刺果,金黄金黄的像极了熟透的山梨,味道酸甜酸甜的。
“哦!谢谢!这东西我们那地方也有,叫‘糖果儿’的。”我接过筲箕,随手剥了一颗。
小桃扑哧一笑,说:“四川人就是斯文。‘糖果儿’,好雅!”
“还是你唱的山歌好。”我笑笑说。
小桃脸一红,扫我一眼道:“你听我唱歌了?嗯,还是小时候听的歌。”
我记着沙玛尔呷的话,不再多说,抓几颗刺梨返身上楼。沙玛尔呷已经醒了,正在换一双登山鞋。见我回来,头也不抬说:“那小妖精没怀疑你吧?”我依旧苦笑一下算是作答,顺手递过刺梨。沙玛尔呷抬眼看看我再看看刺梨,抓过来一扬手扔窗外了。
“看样子你要进山?我为啥不能一起去呢?”我壮着胆子问了句。
沙玛尔呷看也不看我说:“你不行!你不像干我们这行的。我第一眼看你就不像,和小坑一样。”
“沙英雄!你实在是门缝里看人了。告诉你吧!我警校毕业驯过警犬照过相,大小案子也见过不少的。杨大菊那儿是我做通的工作,这你不怀疑吧?”我赌气说了通话。见沙玛尔呷也没啥不自在,索性说,“你玩的这些套路我也懂,不过换身行头罢了。我天遥地远地来贵州,来这鸟不拉屎的噶哒场,是因为我是一名刑警——唯一见过胡锅巴的警察。换你,你会转头回水西不?我只送你一句话,我不是累赘,绝对不是!”一口气说完,我的胸口差不多要迸裂了。菊子的那条红围巾像一颗烧热了的鹅卵石,一直揪着我的心。我想告诉沙玛尔呷,我要亲手把围巾丢给胡锅巴。我没好说出口。
沙玛尔呷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一番,带上门走了。我不觉无名火起,你端哪样架子呀?不就翻墙揭瓦玩变脸的功夫吗?耍啥大牌吗?还不好发作,毕竟是在人家地面上。再说,沙玛尔呷这会儿好像也是焦眉愁眼的,我添啥乱呢?这样胡思乱想着,小桃上楼招呼我吃午饭。下楼一看,沙玛尔呷已端坐桌边,身边放着双新胶鞋。看码子正合我这双不大的脚,心里一喜。
“乡场小店,有好客无好菜,将就对付一下。彝乡人说怪酒不怪菜,米酒是我们自酿的,请多喝几碗。”小桃拿了罐米酒过来。酒刚倒上,淡淡的醇香直往五脏六腑里钻。我担心喝酒误事,拿眼看沙玛尔呷,沙玛尔呷已经把自己的碗伸给小桃了。接了酒,爽快说:“喝点儿酒好,一会儿你要拍小韭菜坪远景,要走不少路呢。”我知道这是沙玛尔呷在放烟幕弹,便支吾着说好。说话间,小桃自己也倒了碗酒,和我们碰了下碗口挪一边去了。贵州菜又酸又辣,很提口味。我和沙玛尔呷闷头喝酒吃菜,倒比平常多吃了些。
吃完饭回到房间,小桃已经生了一盆炭火放屋里了。
“试试看,合脚不?”沙玛尔呷把胶鞋往我脚下一扔,扯过被子又打起盹儿来。
“你这瞌睡也是没完没了的啦。”我嘴上说着话,一边试了鞋,好合脚的。想说声谢谢,沙玛尔呷又打起呼噜来。
风是越发地大了,窗外一簇枫叶在狂风中剧烈地摇曳扭动着,窗棂也跟着啪啪直响。可只要风一停,屋里就会有一种让人窒息的寂静。床铺很干净也很暖和,试着和沙玛尔呷那样闭上眼睛,没过一阵,还真睡着了。正迷糊间,听得有动静,起身一看,沙玛尔呷已经穿戴齐整了。一看时间,刚下午三点。
“嗨!三十九码的鞋也能穿,我十三岁就穿这码子了。”沙玛尔呷见我蹬上胶鞋,嘲笑道。
“‘脚大江山稳,手大定乾坤。’所以你是沙英雄我是无名小卒!”我调侃说。
小桃又没在院里,沙玛尔呷给小姑娘说了声房间留着,我们去去就回。不待小姑娘搭腔,沙玛尔呷头里走了。
天空纷纷扬扬下起了鹅毛大雪,我俩下到溪边,迈过溪水上的石跳磴,往对面的山沟走去。山沟很深,空荡荡的山谷只有我俩走着。积雪已经没过脚背,凄厉的雪风在我们身上揉来磨去,像要把我们当洗衣桶里的湿被单扭干甩尽一样。走了十来里死一般沉寂的山谷,来到一面斜坡上。沙玛尔呷指指远方,说:“你看!那就是小韭菜坪。”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一道起起伏伏的雪山出现在混沌一片的天际,银装素裹横陈天穹。“好个贵州屋脊!可惜我不得相见哟。”我叹道。
“这也不难,今晚抓不着胡锅巴,你只管去爬小韭菜坪好了。”沙玛尔呷看看表,幽默道。
“那我宁可留着下次上去,也要逮着他。”我喘着粗气说。
五
不知不觉中,我们走了快三个小时,天已经暗了下来。沙玛尔呷加快脚步,我紧赶慢赶跟上,一会儿出了沟谷。
“母猪街到了。”沙玛尔呷嘀咕一声。
不远处陡然有了块平坝和一片片砖瓦房。雪风刮过,炊烟裹着黄叶和雪花飞沙走石一般。沙玛尔呷寻了个背风处一屁股坐下,从烟包里摸出对讲机,调了频道开始用土话呼叫。没呼几声对讲机里有了应答,声音清晰,看样子对方也不远。“我的人!我有一帮人马,我们给自己取了个名字,‘林猫突击队’!”沙玛尔呷咧嘴一笑说。我心里一喜,看架势今晚有戏。果然,沙玛尔呷站起来,从烟包里又摸出望远镜向母猪街张望。看了会儿顺手把望远镜递给我,指了他看的方向说:“看丁字路口,那儿是‘月月红’!我的人已经到位,我们只管接应。”我举起望远镜,眼前除了尘霾一般的雪雾,啥也看不清楚。还不好疑问,细细看了一阵才放下望远镜。
“好吧!让那家伙快活快活,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快活了。”沙玛尔呷收了望远镜,递给我一块面包和一小瓶酒,我们一块儿一口面包一口酒吃了起来。没吃几口,对讲机里突然急火火地有了声音。沙玛尔呷呼地站起来,把面包、酒瓶往地上一扔,大声说:“走走走!到手了。”
我随沙玛尔呷高高低低往前跑,不一会儿到了一条机耕道边。对面窸窸窣窣疾步走来七八条汉子,都一身黑衣黑裤,中间夹着个戴手铐、穿红色羽绒服的人。近得前来,沙玛尔呷一把拽过羽绒服,打开手电筒照到他脸上。“是他吗?”沙玛尔呷甩头问我。我一时不知咋办,只盯那人眼睛看,希望他能剜我一眼。可那家伙犟着脑袋,看也不看我。沙玛尔呷狠狠瞪了我一眼,像要喷出火一样。情急之下,我用我们干坝子土话大声问:“胡锅巴!认得我噻?我是‘狗娃’!”那家伙显然愣了下,脑袋还是耷拉着。我再没了主意。沙玛尔呷没了耐心,他从腰间抽出把五四式手枪抵住那家伙脑袋。不待沙玛尔呷问话,我牙槽一酸,嚯地摸出红围巾,猛一下塞到那家伙眼前。“胡锅巴!认得它不?”那家伙像被围巾烫着了一样抖地闪了闪脸,转头剜了我一眼。我惊奇地看到,他的眼神除了惶恐,竟然还带着一丝惊喜。只这一眼,我确认他是胡锅巴无疑了。“胡锅巴!跟菊子一路回四川吧!”我恨恨地说。话音刚落,沙玛尔呷一挥手,一行人把胡锅巴连推带拽地照原路往回赶。匆忙间我回头望了望母猪街,那儿一片人喊狗叫,似乎灯火也亮了起来。不敢多看,我紧紧跟上沙玛尔呷。
沟里的雪更厚了,一行人牛一般喘着粗气跑出沟谷回到噶哒场,一个个差不多都挪不动脚了。我更是双手撑着膝盖,喘得直打干哕。沙玛尔呷也喘得不行,却一直用对讲机不耐烦地吆喝着啥。一会儿,两辆面包车飞驰而来,沙玛尔呷吆喝着让人把胡锅巴往车里塞,然后指挥另一台车扑向小桃的院子。我一时不知咋办,猛听得那边小桃呼天抢地在哭喊,便本能地跑了过去。

小桃的店外边围了不少的人。坑卫东带着几个便衣刑警正把小桃往外拽,小桃双手抠住门柱子,死活不撒手。沙玛尔呷几个箭步过去,扬起手照小桃肩膀重重一拍。小桃回头一看,刹那间就愣了,双手也撒开了。趁这当儿,沙玛尔呷瞪了眼坑卫东,劈手夺过他手里的手铐麻利地给小桃戴上。场上的人越围越多,小桃又开始号叫起来。沙玛尔呷和一个林猫突击队员半拖半架地把小桃拉到车边推进了车厢。我还在犹豫,沙玛尔呷一掌把我拍进车里,然后自己跳了进来。车灯大开,朝着渐渐聚拢的人群冲了过去。
车越开越快,沙玛尔呷佝偻着腰还在一个劲儿地催促。车前车后三三两两有了奔跑的人,不一会儿越来越多,有人用土话大呼小叫,小桃也拿脑袋往车上嘣嘣撞。沙玛尔呷探出头高声吼了些土话,不大奏效。他侧身掏出手枪,拉上膛后朝天上扣动扳机,偏偏卡壳了。他转身瞪了我一眼。我急忙抽出我的手枪,探出窗外,朝天放了几枪。火光闪过,车里弥漫起一股淡淡的硝烟味儿。尾追的人渐渐稀少,小桃也安静下来了。
面包车一前一后很快到了石坪,沿着河岸顶风冒雪一路向东,车速也渐渐慢了下来。沙玛尔呷这才颓坐到我身边,接过一个队员递过的烟,咧嘴笑了。他一笑,车里其他人也跟着笑了起来。驾驶员拧了下音响,车里猛地响起罗大佑的《恋曲1990》。我一直不太喜欢这首歌,这下听得,格外地带劲儿。我一时忘了胡锅巴忘了小桃,也跟着沙玛尔呷和林猫们吼了起来。歌声响亮,仿佛要把车顶掀翻一般。
六
车到水西城,办完关押手续,天已放亮。连续十多个小时奔跑,我们又累又饿。瞥见看守所对面有家米粉店,不由分说进去,每人要了两碗双料的遵义羊肉米粉,吸吸溜溜吃了。我坚持付了账。沙玛尔呷打了饱嗝打哈欠,拍拍我肩膀,笑着说:“现在我该叫你狗娃还是徐志摩呢?”
“叫我表弟好了!只当我真有了你这个彝族表哥!”我哈哈一笑说。
“我让人把杨大菊的骨灰带来了。你把她带回四川吧!”沙玛尔呷脸上掠过一丝忧色说。
“嗯!我也有这意思。”
“来吧表弟!用你的相机我们合个影。”沙玛尔呷振作一下,拽过一旁的坑卫东,指着我脖子下的理光KR5说。
“相片冲出来后寄我一张,记住……”沙玛尔呷提醒说。
“我晓得!你是马赛克人物。我珍藏起来,一个人看好了。”我打断沙玛尔呷的话说,“但愿你和你的‘林猫’能追到四川追到我们川东来!还有小坑,我请你们喝酒。”
“你也随时来黔西北,韭菜坪还等着你呢!”沙玛尔呷朗声说。
照完相,我和沙玛尔呷站在雪地里握手告别。四下浑浑茫茫,影影幢幢,一派雪国景象。沙玛尔呷的手,火钳一样瘦巴巴的。坚硬,也暖手。
责任编辑 谢昕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