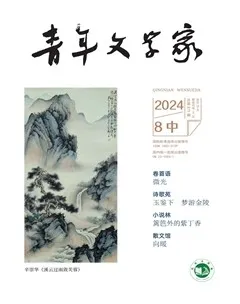无足轻重并不是艺术家的宿命
西班牙港,一个被热带海洋暖风所包裹的城市,既有加勒比土著,又有印度、非洲迁徙来的移民。贫民窟与贫民窟之间,除了特立尼达英语与多巴哥英语以外,还有乞丐、混混,充斥于V.S.奈保尔的童年回忆之中。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一边走,一边向“我”(指的是V.S.奈保尔的作品《B·华兹华斯》中的小男孩,这部作品正是以这个小男孩的视角所写)的街坊们乞讨。街坊们似乎也习惯了他们的存在。不过,今天有一点儿不同,来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人,奇怪到让“我”的妈妈想要赶紧赶走他。
这个人穿着讲究,“头戴礼帽,身着白衬衣和黑裤子”,说话斯文,“缓慢,而且字正腔圆”,不像是米格尔街平常会出现的那一类人。更加奇怪的是,他不仅不需要物质层面的施舍,反而还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请求—看“我”家的蜜蜂,并且一看就是一个小时。他一边看,一边抓着“我”讨论他的古怪爱好。不过,“我”不感兴趣,只想要知道他是谁。“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他很自信,而且还将自己与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联系到了一起。眼见“我”和他开始逐渐地熟络起来,华兹华斯用着开玩笑一般的语气,八卦“我”与“我”的母亲之间的关系,并且和“我”说:“这张纸上有一首最伟大的写母亲的诗歌,我打算便宜点卖给你,四分钱了。”结果,在“我”的母亲的“威胁”之下,华兹华斯灰溜溜地走了。虽然他就这么走了,但“我”很开心交到了一个新朋友,期望可以再一次见到他。
后来,“我”和华兹华斯又相见了,他其实并不穷,甚至还有一个位于“阿尔贝托街正中心”的家。“我们”一起去他家,一起品尝芒果,一起“躺在草地,仰望天空”,一起讨论猎户星群。而且,“我”还听说了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因意外而夭折,最终只能够留下一片绿地的爱情故事。在这期间,“我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同时又感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骄傲和痛快。我忘记了生气,忘记了眼泪,也忘记了所有的不幸”。然而,“我”和华兹华斯唯独无法回答上那一个警察无意之间问的问题:“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是的,我们在人间,到底应该干什么?一瞬间,华兹华斯苍老了许多。
后来,“我们”又一起“走很远的路”,“去植物园和假山花园”,还爬上过“大臣山”,一边吃着冰激凌,一边“看着黑夜降临西班牙港,看着城市和港口的船只逐渐地点亮灯火”。这一段时光,“世界变成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终于有一天,华兹华斯向“我”透露了他的理想—写出全世界最伟大的诗歌,并表示自己已经坚持了五年,一个月写一行,再花二十二年就可以完成了。
我看到这一段文字,不免会回想起从前的自己也特别自信,认为自己只要每一天都坚持阅读和创作,迟早有一天可以写出完美的作品,又在看到了华兹华斯可能只写出了那一句“往昔是幽深的”之后,想到了自己尚未有很好的发展,更妄论社会之认可。华兹华斯先生正在慢慢地老去。
正当“我”开始认为,原本沉闷无比的世界正在变得有意思起来的时候,华兹华斯先生永远地离开了,爱情故事变成了假的,最伟大的诗歌也变成了假的。世界重归于混沌,就如同V.S.奈保尔的精神世界一样,而“一切都好像在表明,华兹华斯从来没有到过这一个世界”,只有“我”仍然记得他。
一直以来,华兹华斯所秉持的,其实就是作为一个诗人的尊严—不想要去迎合,只想要被理解,想要找到一个懂他的人。这一个人,从前可能是女诗人,现在可能是“我”。某一种程度上,华兹华斯可能是V.S.奈保尔的心理投射,是他在紊乱的身份认同底下,在强烈的创作欲望之上,渴望得到理解的侧写。我们在人间到底应该干什么?兴许,就是应该找到一个能够理解自己,抑或能够陪伴自己的灵魂伴侣吧。
V.S.奈保尔曾经在他的另外一部代表作《大河湾》写道:“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华兹华斯的生命到底有没有重量?在我看来,是有的,因为一个人只要被理解过一次,无足轻重就不再是他的宿命了。
——以柏林Kreuzberg 地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