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山海经》书前提要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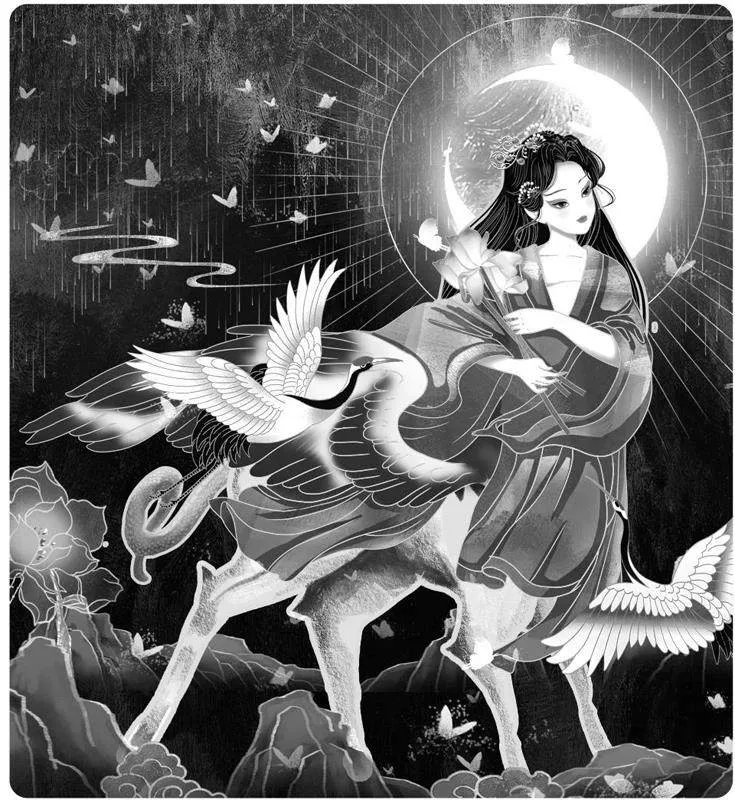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大型丛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曾下诏要求“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随后制定著录存目之规制,进行编目工作。提要能够宏观地把握学术史的师承和走向,介绍图书的内容,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体式。《山海经》篇幅不长,全书三万多字,却包含了地理、植物、医药、矿产、神话、人物、方国、祭祀、风俗等方面的内容,是研究中国上古时期社会历史文化必不可少的文献,具有史学、文学、语料、地理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四库全书》将《山海经》归入子部小说家类,馆臣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山海经》一书作提要,主要阐述了其成书、卷数和归类问题。本文以中华书局1983年版《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山海经》书前提要作为研究对象,就上述三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一、成书
提要中开头部分主要论述了《山海经》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一)《山海经》的作者
对于“《山海经》作者是谁”这一问题,馆臣十分重视,共征引了六部古籍,分别为刘秀《上山海经表》、司马迁《史记》、列御寇《列子》、王充《论衡》、赵煜《吴越春秋》以及《隋书·经籍志》。
《四库全书总目》关于《山海经》的书前提要,开篇提到晋代郭璞给《山海经》作注,同时提到刘秀的《上山海经表》,此表首次对《山海经》之成书及作者做了说明,认为此书出于唐虞之际,伯益所作,多为搜奇志怪之举,袁珂《山海经校注》引《上山海经表》云:“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表述与此同;提要指出“山海经”这一书名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司马迁因《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内容太过怪诞而不敢妄加评述,至于《山海经》的作者,《史记》中并未提及;《列子·汤问》记载了商汤和夏革之间的问答,并讲述《山海经》撰写过程是由大禹见到上述“异物”,伯益知道后给它们取名,夷坚听说后将其记载下来。《列子》原文中此处前后并没有提及《山海经》,但夏革在回答伯益的提问时提到的“颛顼”“共工”“不周山”“大壑”等内容均在《山海经》中有所体现,晋人张湛在给《列子》作注时也多次引用《山海经》中的内容,提要所说禹、益、坚三人所作之书即为《山海经》有文献可支撑;提要中还引用了王充《论衡·别通》的说法,即《山海经》于上古治水的过程中,由大禹和伯益合作而成;《吴越春秋》中提及《山海经》成书的语句出自《越王无余外传第六》,其论述《山海经》是在治水的过程中由大禹和伯益合作而成,这与《论衡》中说法近似;此外,《隋书·经籍志》卷二中记载,“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由此可知,《隋书》认为《山海经》相传为大禹所作,后为萧何所得。
(二)成书
1.成书时间
除《山海经》的作者之外,其成书时间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山海经》成书时间这一问题上,自古及今说法不一,迄今尚无定论,馆臣们根据《山海经》中部分人名和地名推断其问世不可能早于周代,提要中此部分列举的人名、地名仅出现于《山海经》中的《海经》,并没有与《山经》中相对应的内容。万群《从汉语史角度看〈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一文从语言学的角度推断《山经》成书于战国中晚期,《海经》和《荒经》成书晚于《山经》,大致成书于战国末秦汉初。
2.与《天问》的关系
提要中提到《天问》中的部分内容与《山海经》相对应,经笔者查阅,《山海经》中所记载的上古传说中的人物、动植物、地名、神话故事等均与《天问》的内容相对应,但提要否定了朱熹在《楚辞辨证》中提出的《山海经》是根据《天问》而作的观点。现代学者胡远鹏于《〈山海经〉与〈天问〉》一文中从客体范畴和成书时间两方面展开论述,阐明《山海经》成书缘由并非解《天问》而作。
3.因图而作《山海经》
关于“《山海经》是否因图而作”这一问题,提要引用了王应麟先生在《王会补传》中的观点:“《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曰‘东首’,疑本因图画而述之。”晁福林先生在《“山海经图”与〈山海经〉成书问题补释》一文中将“山海经图”存在过的证据按照时间顺序归纳为十二条,其中第一条便是“《山海经》诸篇记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东首’,当是依图画而为之”,这与提要中王应麟先生的观点高度吻合。此外,晁福林先生还列举了其余十一条依据,并认为从《山海经》文本内部和郭璞注中寻找证据更为直接有力。如此看来,提要中讲到《山海经》“因图而作”存在一定的依据。但“山海经图”今已不复见,“因图而作”的说法是否成立还有待商榷。
(三)小结
提要至此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山海经》的问世,即作者、成书年代、与《天问》的关系及“山海经图”的问题。提要中征引了六部古籍探讨《山海经》为何人所作,除《史记》外其他五部古籍都提及了《山海经》的“作者”,但这些古籍中的说法都十分类似,不外乎传说中的大禹、伯益、夷坚,且古籍中多有托名的现象,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托名的现象在先秦时就已出现,《山海经》的作者现已无从考证,故馆臣最终推测大抵是周秦之间的人讲述,经后人记录、整理、附益而成书;至于《山海经》的成书年代,提要将《山海经》中的内容与有关的信息进行比较,并使用排除法推断其大抵成书于周秦之后;此外,《山海经》中部分人物、动植物、地名和神话故事与《天问》相对应,但馆臣们否认《山海经》因《天问》而作,二者关系如何还有待考证;馆臣据《山海经》中表方位的词推测其很有可能是因图而作,但“山海经图”至迟在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古籍之时便已散佚,故“因图而作”只是推断。
二、篇卷数
提要中提到《山海经》的篇卷数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分别是“隋唐二志”二十三卷、刘秀《上山海经表》十八篇、《汉书》十三篇。
(一)刘秀《上山海经表》
刘秀《上山海经表》中有云:“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此处“一十八篇”即指其搜集到的各种写本的篇数总和。清代学者毕沅认为刘秀《上山海经表》中“三十二”当为“三十四”之误,其篇目包括《五藏山经》二十六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不含《大荒经》以下五篇在内;郝懿行计算的篇目数与毕沅相同,对刘秀得到的结果也感到困惑,“然则古经残简,非复完篇,殆自昔而然矣”(《山海经笺疏》)。今本《山海经》包括《山经》五篇、《海经》八篇、《荒经》五篇,共十八篇,与刘秀所校定的《山海经》篇数相同,但在汉之后出现了比刘秀勘定的《山海经》多或少五篇(卷)的《山海经》。
(二)班固《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云“《山海经》十三篇”,与《上山海经表》中的说法相比少五篇。《汉书·艺文志》是在刘秀《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以备篇籍”,本不该“自相矛盾”。提要中并没有针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解释。李零先生在其著作《兰台万卷》中提出《汉书》中《山海经》的篇卷数是有五篇去而不录的结果。
(三)“隋唐二志”
“隋唐二志”确为何书?隋唐时期收录《山海经》的官方目录主要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经查阅,《隋书·经籍志》中收录《山海经》二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中收录《山海经》十八卷,《新唐书·艺文志》中收录《山海经》二十三卷。故此处的“隋唐二志”应为《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
据提要可知,清代的《山海经》多为十八卷,而“隋唐二志”却是二十三卷,提要认为可能是后人将二十三卷的《山海经》“并其卷帙”,以求与刘秀《上山海经表》中所说的“一十八篇”相合。
(四)小结
关于《山海经》篇卷数的问题,袁珂先生做了合理的解释:《山海经》篇目古本为三十四篇,即《南山经》三篇、《西山经》四篇、《北山经》三篇、《东山经》四篇、《中山经》十二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刘歆《七略》以《五藏山经》五篇加《海外》《海内经》八篇为十三篇,《汉书·艺文志》说法与此同;刘秀校书,乃分《五藏山经》为十篇而“定为一十八篇”;郭璞注此书复于十八篇外收入“逸在外”的《荒经》以下五篇为二十三篇,即《隋书·经籍志》所收录《山海经》的篇目数;《旧唐书·经籍志》复将刘歆原本所分的《五藏山经》十篇合为五篇,加《海内外经》八篇、《荒经》以下五篇为十八篇,求符刘秀表文所定篇目,即今本。
三、分类
古籍分类始于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七略》。我国历代书籍的分类标准不一而足,《山海经》因其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而成为“上古三大奇书”之一,但这也导致其归类问题历来都有争议。《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数术略中相地形的形法家;《隋书·经籍志》认为《山海经》是类似于《尚书·禹贡》的地理书,因而将其归入史部的地理类;《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与《隋志》同,均将其归入史部地理类;而《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归入子部的小说家类;提要中提到的《道藏》是汇集收藏所有道教经典以及有关书籍的一部大型丛书,文渊阁本《道藏》书前提要中提到“《山海经》旧入地理类”,因《山海经》“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将其收入其中;馆臣们“究其本质”,发现“实非黄老之言”,在此基础上,结合小说家类提要中的“定义”,《山海经》满足“叙述杂事”“记录异闻”和“缀辑琐语”三要素中的“记录异闻”,故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并冠以“小说之最古者”的头衔。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鲁迅先生认为《山海经》中的神话具有小说的性质,其观点与四库馆臣们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通过对《山海经》书前提要的划分、解读及论述,本文可得知以下信息:《山海经》大致成书于周秦之间,且并非一人所作,传说中的大禹、伯益、夷坚等人作《山海经》当为托名之举,其成书缘起尚有待考证;今传《山海经》由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刘秀校定,共十八卷,历代篇卷数差异当为分“卷”“篇”方式的不同;根据《山海经》中部分关于地形地势的叙述可知其极有可能是“因图而作”,但“山海经图”在刘秀校书时就已失传,甚至“山海经图”是否存在过至今依旧存在争议;提要最后馆臣们对《山海经》的类属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将前代归为地理类的《山海经》划分为子部小说家类,并称其为最早的“记录异闻”的小说类书籍,此当与《山海经》一书收录大量神话故事有关。
《山海经》成书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从未停止对其进行研究:古人对《山海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征辑、考据校注等方面;进入现当代,对《山海经》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近现代以来,国内对《山海经》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以《山海经》中的异人异兽形象作为切入点,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意蕴,从而探求先民们的原始意识;二是从《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切入,探究神话故事所反映出的历史形态;三是从语言方面入手,对《山海经》文本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研究。而这一切研究的开展均建立在古人对《山海经》征辑、考据、校注的基础上。《山海经》是我国一部重要古籍,记载了上古时期的文明与文化状态,关于它的一些问题学界至今依旧存在争议,隐藏在其背后的秘密还有待学者继续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