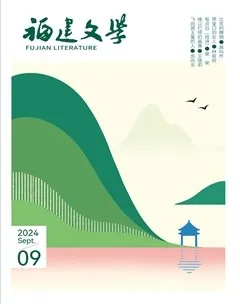一曲终了,病退人安
1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有两架非凡之琴被砸碎,且乃抚琴者自己做出的决断。说它非凡是因为它的演奏者及其演奏的曲调均高蹈得世间无二。我想象,两个抚琴者在砸琴之时一定是拊膺之极,并因之使尽了浑身气力。这历史性的拼命一砸,琴会碎成什么样子?有火光?有哀鸣?是逃逸?是颤抖?据《伯牙碎琴》载:伯牙痛失知音,一曲《高山流水》过后,于衣夹间取出解手刀,割断琴弦,双手举琴,摔向祭石台,摔得玉轸抛残,金徽凌乱。而《广陵散》后琴被砸时,更是三千太学子为之流泪跪拜。我想这样的场面历史不二,其断弦颤动之态一定胜于哀鸿,其音洞穿时空,千年不散。只要我们仔细认真听来,它依然在我们耳畔周遭响彻。
古时,弹琴完全不是一项简单的技艺,它超越一切世俗表演。弹奏者在弹奏时对时间、地点、环境及其心境都有着近乎苛刻的讲究,淋浴更衣,焚香定神。忌大寒、大暑、大风、大雨、迅雷及大雪,同时,闻丧时不弹,奏乐时不弹,事冗时不弹,不净身时不弹,衣冠不整时不弹,不焚香时不弹,不遇知音时不弹,此统谓“六忌、七不弹”,神圣之极呀!焚一炷香,整一整衣冠,既是对曲调的肃然起敬,也是对听众观者心中不染一丝纤尘的尊重——我想,那样一个神圣的场合应该没有一名违和者。抚琴者的心境应是静如止水了,且那水也是清澈见底的。
它直接浸润着听众与观者。
如此天人合一的环境,那两个高蹈的抚琴者是如何违和地将自己的情绪来个一百八十度的惊天大逆转,将虽非商彝周鼎却也能通天地,甚至泣鬼神的心爱之物自毁呢?
两琴相继被砸时间间隔应有四百余年之久,即便是抄袭,那也是早就揳之于骨髓后的油然而生。四百年足可以翻天覆地,没有翻动或者翻不动的始终是那两曲天籁。我想,也不是没有翻动,而是努力地千方百计地接续,于一团乱麻中梳理出一根根经或一根根纬,然后织成锦绣。
而锦绣永远都不会司空见惯,就如这《高山流水》,这《广陵散》。
君子以琴养德。君子在,琴就始终在,反之亦然。琴棋书画,琴所以居其首位,当然有它首位的理由。班固在其所撰《白虎通》中称:“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而医学家发现,人心并不在身体中间,它偏左。因而以琴正人心是妙方之一。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心都适合此方,也不是所有的琴声都能正那偏向左侧之心。它们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可匹配的端口,那便是从高山而来,在低处汇合的知音了。知音都是自动适配的,否则就是两条相距甚远的平行线了,互不相干,兀自前行。
以琴正人心的一个绝妙例子莫过于孔子以琴退兵。蔡邕在《琴操》一文中,有一段对孔子及其弟子一行去宋国游说时,莫名其妙地被宋人甲士围困的记载:孔子到匡郭外,颜渊举策指匡穿垣曰:“往与阳货正从此入。”匡人闻其言,告君曰:“往者阳货今复来。”乃率众围孔子数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军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圣人,自解也。
孔子琴音退敌,为孔门弟子解围除厄。《三国演义》中武侯弹琴退仲达如出一辙。罗贯中说得有板有眼,诸葛亮坐于西城城楼之上,整襟而自若,用他的古瑶琴弹奏了一曲《梁父吟》,解了十五万大军兵临城下之围。空城计的虚实虽难以详考,但也符合司马氏疑心病十足的逻辑。疑心病十足的司马懿居然成了诸葛孔明的知音,这样的知音虽匪夷所思,却每每合情合理,甚至就合了天道,或许冤家路窄可能窄就窄在知音这根弦上。
伯牙与钟子期也是如此!
伯牙弹奏用的同样是一架古瑶琴。古瑶琴又称七弦琴。据传,古瑶琴为伏羲所做,原为五弦,因周文王、周武王分别加了一文弦与武弦,遂成七弦琴。由于古琴的琴弦大多为蚕丝制作,加之几千年之前,环境应是原生态,否则便没有一呼百应之说。即便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仍然如此。记得那时候我家湖对岸有人喊田间耕种的人回家吃饭,大声疾呼一下,我们这边竟然听得一清二楚,恨不得开个玩笑响应一下,要知道那是连两省通四县的一片大湖。正因如此,古琴方音域宽广,音色深沉,音质悠远传扬。我想也正因如此,仲达才有机会听清楚辨明白那曲《梁父吟》,并探出其真正内涵。
俞伯牙为战国时期晋大夫,既演奏,又作曲,《高山流水》便是他的成名作。伯牙并不姓俞,姓伯,说他“姓俞名瑞,字伯牙”是明末小说家冯梦龙在小说中的以讹传讹,不可详考。伯牙一直被世人颂为“琴仙”。他与打柴人钟子期相遇,成为知音算是天地配了。天地配既有天壤之别的不可能,又有天地相合相因的独到情理,高山之水只有在这里才能奔流,放笔直干。钟子期离世,让伯牙悲痛之下将瑶琴毁去。世间再无知音。当时或许落日残照长长的孤影,天地死寂,电闪雷鸣,黑云翻动整个旷野。
我一直没有想通,伯牙在得到钟子期这个知音之前一直在苦苦寻找知音,为什么钟子期离世后便不再寻找知音呢?他依据什么断定世间再无知音?大约我们的祖先遵循的都是不二法则,从一而终。仔细想来,罗贯中的确没让诸葛亮再次弹奏《梁父吟》退却仲达,也未读得孔圣人再次用琴解围除厄的案例。《高山流水》在伯牙创作之初可能就设定了这样一个死节:世间只有一个绝对的知音,只能正一人之心,其他皆为赝品。
这便是《高山流水》以及所有“高山流水”之高了,高到了空气稀薄。我在想,人心被正之后,身体是不是就受到了重创?钟子期自成为伯牙知音之后不久便匪夷所思地病了,以至离世,爽约中秋。
那个中秋之夜,伯牙比之那轮明月,实际还要孤独。
2
高山总有流水不断向下流淌,流向四面八方,流向江河湖海。
它在寻找。
江河湖海总是波浪汹涌,浪花激溅,即便是平静的,也仍然有看不见的涌动,鱼儿溅起的水花仍能让一切不肯止息!
谁在呐喊?我感到是呐喊,而非鸣叫。鸣叫的只有麻雀。任何时代都有的麻雀、总是飞一下停一下的麻雀,是否也是从战国时伯牙那座高山上飞来?
风也在呐喊。风入松,风吹动一枝一叶,卷起尘土。
尘土不通音律,尘土只是相反地将一切包括音律覆盖。
是否覆盖了我们的梦?
高山仍然耸立,千年万年。
这是我为《高山流水》写就的一首散文诗,估计我也没听懂《高山流水》。按照伯牙的逻辑,我注定不是他千年后的知音,《高山流水》难以纠正我们这些平凡人的那颗平凡之心,所以我们的心仍然偏向左侧,所以我的身体目前仍然健硕,我的这首散文诗因此应属偏左而出的赝品。
世间本就赝品多。现在我们听到的《高山流水》可能也是赝品,因为是真是假,只有伯牙知道,钟子期知道,而伯牙钟子期不再,所有当时的听众也都不再。可《高山流水》却一直在被演奏,除伯牙之外历朝历代数不尽的人在“一片冰心”地演奏。谁是第二个听懂它的人呢?感觉比伯牙寻子期更难了。据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只有几人能读懂。别问这是不是诳语,阳春白雪,鹤立鸡群,知音总归是稀疏的,何况是从高山上流淌下来的呢!
伯牙毁琴并非事先有准备,他是在访子期的路上得知子期已故,乃往祭拜。由于事起仓促,伯牙未备祭品,乃置琴于祭石台上,盘膝坐定坟前,挥泪操琴悼后,断弦毁琴,以此为祭。《伯牙碎琴》中的这种解读方式似更为合理,那就是对知音以特殊的方式纪念:将彼此心爱之物赠予知音。赠予,便不可索回,不可逆,阴阳之隔呀!
但我们却在不断找寻。我常常想发问:找到琴道了吗,或者说找到知音了吗?孔子听韶乐,三日不知肉味。估计韶乐是道,孔子是韶乐的知音,这似与《高山流水》的相似度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身边没有关于第二个听韶乐三日不知肉味之人。记忆中我从来就没有因为听音乐而忘记吃饭,尤其吃肉,无论是哪种音乐,西洋的、古曲的、现代的,哪怕《高山流水》,哪怕《广陵散》。听到最后,只知肉香,而忘记弹了些什么。我等因此从未得道,包括琴道。
高山之巅,当然人迹罕至。也许正因如此,高山之上便有那不竭的清澈之水不断从高处流下。智者爱水,尤其来自高山之水,与道等高,与德同质,润河谷,茂草叶,滋心田,抚慰五脏六腑,通畅七脉八经,世代不绝。
想起卢梭描述华伦夫人时说过的话:“我完全成了她的作品。”这话适合高山流水,也适合伯牙子期,还适合诸葛孔明与司马仲达。我有时暗暗发笑:诸葛孔明与司马仲达至死也绝对不相信彼此竟然是一对知音。想起老家的妇女们挂在嘴边的话:你这个挨千刀的!他们其实爱得死去活来。知音就是彼此的冤家,这也算是一个真理式的谬论。这意味深长的真理式谬论合调、合情,甚至都不是和而不同,而是彼此征服与被征服得畅达无阻。我敢肯定,他们完全就是彼此精心打造出来的完美作品。想一想,《三国演义》如果没有空城计中的《卧龙吟》,司马懿如果听不懂《梁父吟》,那便如何是好?
据《吕氏春秋》的记载,伯牙子期相遇之地应是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龟山西脚下的月湖之滨,其东对龟山,北临月湖,被今人授予“天下知音第一台”,成为被修复的文化古迹。今人爱挖掘古迹爱修古迹,修得繁华,修得理直气壮,应该也是觅知音的手法之一,但我感觉都是些钢筋水泥,外加含铅含苯的装饰物,修不成正果的。不过,现代人总是执着,以至到处都是盛景之下的人头攒动,一片哗然。我常常在这哗然之处听得出我们的先人发出的一两声微微的悲鸣。
或许这微微的悲鸣是历史断弦之后发出来的感叹。无论怎样地挖掘与修复,历史之弦仍然是断的,或砸碎,或兵燹,或自焚,或被时间风化,基本祭祀于大地,如伯牙,似嵇康。
想起周时商的三大重臣之一箕子扶仗朝周过殷墟的故事,据传,当时箕子看到自己熟悉的宫殿陵墓已不见踪迹,大邑商似不曾有过,一片黍离麦秀,绿油油铺天盖地,欲哭无泪。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讲述了这个故事:“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则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如此情景,历史不断重演:西晋八王之乱,《晋书·谯纵传》称:“生灵涂炭,神器流离,邦国轸麦秀之哀,宫庙兴黍离之痛。”南北朝时期,侯景之乱后,《梁书·武帝纪》描述:“天灾人火,屡焚宫掖,官府台寺,尺椽无遗,悲甚黍离,痛兼麦秀。”
我在想,箕子他们的知音到底是宫殿陵墓还是黍离麦秀?一切均不可否认地以大地为依归,大地是我们最初与最后的知音。这太多的黍离麦秀,均为大地千年万年真真切切的回响。
3
嵇康,其弹奏《广陵散》时用的也是一架七弦琴。
比之伯牙,他不仅精于笛,妙于琴,还善于音律,且工诗善文,著书立说,其草书时人皆称妙品。他弹琴研琴,对琴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见解。在《琴赋》中,他认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还说:“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钟。”这种对琴曲的礼赞与班固的“正人心”之赞应是相承的。
公元263年,人生对于嵇康来说已走到了尽头,《广陵散》因此也走到了尽头。但与伯牙不同,嵇康的《广陵散》一直弹得万人空巷,也就是说大家都能听懂,能真正听懂并做出反应的当然就是知音了。史载,嵇康弹奏《广陵散》,整个洛阳城为之倾倒。
我有些不解了。同为阳春白雪,《高山流水》除了大地外,只有一个知音,而《广陵散》却万人空巷。难道《广陵散》是一曲通俗乐典,如现在的摇滚乐吗?肯定不是。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古时亦名《聂政刺韩王曲》。“聂政”曲何以名“广陵”?唐代韩皋曾经给出一个颇为可信的理由:“扬州者,广陵故地,魏氏之季,毋丘俭辈皆都督扬州,为司马懿父子所杀。叔夜悲愤之怀,写之于琴,以名其曲,言魏之忠臣散殄于广陵也。盖避当时之祸,乃托于鬼神耳。”“散”之意,魏氏散亡于广陵始。“止息”,晋虽暴兴,但必终止于此。《梦溪笔谈》认为,散为曲名,如《梅花三弄》之“弄”名。我想,此为嵇康《广陵散》的引力所在。有了如此引力,当然就会有如此众多的知音。史载,《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之气、战斗气氛浓烈的乐典。嵇康刑场上弹奏时,铮铮的琴声,神秘的曲调,铺天盖地,让在场的每个人的心弦为之颤抖。弹毕,嵇康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遂砸琴,从容引首就戮,时年仅三十九岁。
“《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这最后的悼词既是为自己慨叹,也是为《广陵散》慨叹。虽然,嵇康承诺秘不授人,但《广陵散》却一直流传。《广陵散》并非嵇康原始创作,它应该是经嵇康加工再造、调整充实而成的一首曲子,正如一首民歌,凝聚着历代传唱者的心血。《神奇秘谱》所载《广陵散》为最早,北宋《止息序》称“纷披灿烂,戈矛纵横”。我现在理解了《广陵散》之所以知音众,而《高山流水》知音稀。《广陵散》实际也只有一个知音,那便是嵇康。只有一人能将其弹奏成妙品,几无人能出其右,其他皆为听众,听者众而已。
《广陵散》《高山流水》是否都是流浪儿?历史总是收留一切流浪儿。大地是所有流浪儿的知音,并以黍离麦秀清一色馈赠。
一个标准,一把尺子。
现代人似乎不相信这一切,他们甚至是一往情深地将一切历史演奏,将一切物什打捞,并傲慢地立志修复,年复一年地演奏、考释,千回万转,似乎他们拥有起死回生之术。
但毕竟世间嵇康仅一人,伯牙与子期也仅一例。
多么可怕!每一部历史都是知音的历史,而每一次杀戮又都是对知音的杀戮。砸琴也是在杀戮。
“《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在刑场上砸琴时说出的这句话肯定不是妄言,亦不是以讹传讹。史载,嵇康赴刑,洛京三千太学子联名请愿,为嵇康鸣不平,并要求嵇康入主太学,为其师,甚至嵇康在狱期间还有大家豪门自愿陪狱。如此众多虔诚的听众,实属历史罕见。但嵇康仍然决绝地走了,头也不回。
头当然不回,他与《广陵散》一起悄然落入大地深处并侧目而视后人。
所谓侧目实际都是素食动物。目生两旁,视觉范围广,便于寻找食物对象,而肉食动物的一对眼睛长在脸的前面,聚焦正前方,便于锁定攻击目标。如此推断,嵇康是个素食者,必被肉食者锁定。《广陵散》执行的是散射,遍地开花。肉食者,不喜花,他只喜欢吃肉,尽管“肉食者鄙”。
我疑惑的是,嵇康为何不顾这些听众,不怜惜他们的感受而将《广陵散》自毁呢?是《广陵散》要毁他,还是他要毁《广陵散》呢?人去、琴砸、音绝,这不就是那个钟会的目标吗?嵇康居然顺藤摸瓜式实现了钟会的目的,这又是一对冤家,两颗怪味豆。在知音这个行业里,此等怪味豆始终存在着。钟繇算是家门不幸,自己位列三公之首,人颂“正书之祖”的一代风流人物,其后代居然人不正、心不正、术不正,是个顶尖小人。小人钟会与大人钟繇也是一对冤家,一个自立家门,一个自毁家门。那个毁家门的让我们这些后代不再有《广陵散》可听、可怡、可传。
我曾经发问,《广陵散》为何正不了钟会之心?他们不就是一对冤家吗?《广陵散》或许有它的“扰乱层”。钟会听到的领略到的可能就是“扰乱层”这个层面上的东西,他甚至就处在那个“扰乱层”。心胸必然狭窄,内存肯定不够,肯定常常开机便死机,比不了司马仲达的机子,比不了伯牙子期的机子。基本就是毁人亦自毁,所以他在自毁的同时先把《广陵散》毁了。《广陵散》的粉丝却立志要毁去《广陵散》,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古人研究所得,音乐像药物一样,可以治病。“一曲终了,病退人安。”
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角为木音通于肝,徵为火音通于心,宫为土音通于脾,商为金音通于肺,羽为水音通于肾。这也应和了现代科学理论:声音是一种波的振动,波也是一种物质。清微淡远的古琴之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其无过无不及的风格与传统养生观是一致的。中正平和的古琴,与宇宙同呼吸,让人气定神闲。
但《广陵散》为何就治不了钟会的病呢?我猜测,钟会定是病入膏肓了,神医神药对于他都是无效的,尤其像《广陵散》这样的猛药,于钟会服下,必是痛苦不堪,并进入他的死穴。
水一定是有缺陷的,尤其高山上的水,所以高山流水,高山之上的水一直向下流淌,寻找它那残缺的部分,这个残缺的部分就是它的知音。榫卯结构,合而为一是它们的目标与归途。所以子期不在,《高山流水》几为未亡人,于是伯牙摔琴,“留之何用!”所以嵇康将去之时,《广陵散》便不必孤存于世,“《广陵散》于今绝矣!”《广陵散》成为嵇康的陪葬品,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它们都合上了榫卯,彼此成就,一同羽化。
其实历史上与《高山流水》《广陵散》命运几乎一致的还有一个著名例子,那便是楚庄王之于绕梁琴,据说绕梁系一名叫华元的人所赠。楚庄王得到绕梁后,整天陶醉于它,竟连续七天不朝。如此知音让其妃樊姬感到了危机。天不绝楚而绝琴,楚庄王听了樊姬之劝,遂忍痛割爱,用铁如意将绕梁捶为数段。从此,绕梁绝响。一对冤家、一对知音从此飘零。
高山流水之于大地之于我们均为一地的黍离麦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