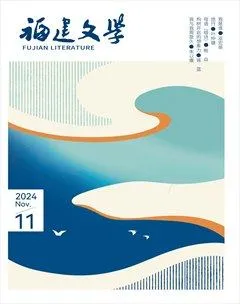荔枝三百颗

这是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知了在荔枝树上不知疲倦地聒噪,我一直都认为,夏日的炎热有一半是被它们叫嚣出来的。我把吊桶的麻绳坐在屁股下,这样就可以把手释放出来,人趴在井台沿上,刚泼过水的老石板虽不那么烫了,但脸靠着还是不舒服,两只手枕在上面,再把头靠上去,舒服多了。井筒湿漉漉的,井壁下半截是嫩黄的青苔,上半截是幽绿的凤尾草。也是怪了,村里就只有这口井,这口井有多老,谁也不知道,据说就因为有了它,才有这个村庄。海边村庄,很难得挖到淡水井,村里人日常的饮用洗刷便都仰仗这口井了,可就是使用频率这么高的井,天天麻绳水桶跌来撞去的,竟然还能长出密密的凤尾草。井底里,我刚刚放下的吊桶静静地没在水面下,隐约可见那束荔枝的暗红。谁都知道,那井水浸过的荔枝那份清甜甘爽,是人间至味。为了求得这口甜,我也是拼了。此刻,平静的水面上,映出了我裂开的碎脸,还有井边人家飞檐上的一角,仿佛那边也是一个村庄、也有成片的荔枝林。
1
农场小学下课的钟声刚敲响,所有孩子一溜烟往红土坡上跑,靠速度抢占最好玩的阵地。坡上是一片荔枝林。在我儿时的印象里,唯一的水果就是荔枝。那时的荔枝树都很高大,人们一旦种下了,就舍不得砍它,所以房前屋后几十年上百年的荔枝树随处可见。学校边上这一片荔枝应该是开垦农场的第一代人种下的,有十几年吧,不是特别高大,却够强健,可以任我们游戏折腾。以荔枝树为标杆,玩“走国”,一棵树就是一国,看谁跑得快,先占到树的就是赢家“占国”了。或者爬到树上玩“相捉”,谁最先被抓到,谁就输了。爱刺激的,还爬到那斜伸出来的树枝上,上面坐一两个,地上几个把树枝拉到极限,然后把手一放,这树枝一反弹,飞得老高,上面下面的人都尖叫。那种刺激与快感,没经历过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一年年下来,这些荔枝树干都被我们摩挲得油光滑亮,就连树下的红土地,也被我们的光脚丫踩得硬邦邦,像打了蜡似的。尽管被我们如此蹂躏,这些荔枝树也是不长记性的,来年春天,依然会开满密密麻麻的花。玩是孩子的天性,开花结果是荔枝的天性。
在开满花的树下玩时,常常沾了一头的细小浅绿的花蕊,蕊还带着蜜,总是把头发弄得黏黏的,这也没什么,最讨厌的是,会引来那么三两只蜜蜂嗡嗡嗡围着转,让我们从小就切身体会到招蜂引蝶是一件烦人的事。我有时良心发现,会很担忧,掉了这么多花朵,如果一花一果的话,那要损失多少颗荔枝啊。后来我才知道,荔枝花开太密也并不是好事,反倒会影响挂果的质量,所以常常得人工去掉一些花蕊,小孩儿们在树下、枝头的折腾,无意间也帮荔枝去掉一些多余的花蕊,所以果农们才不管不顾听凭我们胡闹。
到了初夏,荔枝已经挂满枝头了,虽然还青涩着,却已经有淡淡的果香了,半熟的果子格外馋人。戴着斗笠的果农们成天在树下巡视着,只要我们稍一靠近荔枝树,就会被他们恶声恶气地赶开。我很佩服这些果农们,在这样诱人的果香里,他们就这样看着,却不吃一个果子,这该有多大的忍耐力呀。我们没有这样的忍耐力,于是,常常有几个胆大的,假装内急,提着裤子匆匆往荔枝林深处跑去。果农知道肯定有猫腻,就在后面跟着。也就在他转身追去的那一会儿,几个小孩儿已经飞快地蹿上树,折下一串荔枝飞也似的逃离,当果农们明白中了调虎离山计时,已经来不及了。也有手脚慢一点的孩子,被抓到了,逮到学校办公室,写了好几张检讨书,期末的成绩单里老师就会很客观地加上一句评语:“该生头脑灵活,手脚麻利,若能用到正路,定能取得更大进步!”偷来的荔枝是得平分的,荔枝还没红透时,可真酸。不过对付再酸的果子我们也有办法,那就是嚼的时候闭上眼睛,这样就可以忍得住了。也许是小时候吃多了这种未成熟的酸荔枝,到后来,在荔枝可以随便买随便吃的日子里,我仍然喜欢吃带酸味的荔枝,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舌尖上的记忆”?
6月底,荔枝一串串地在枝头妖艳招摇,满园的香气让人心痒,鼻子发酸,走路就像坐船,晃晃悠悠的。一开始我还以为只有自己这样,问了小伙伴们,他们也差不多。可是这会儿看园子的人多了,我们再也没有下手的机会了。父亲是开拖拉机的,经常四处跑。有一天晚上据说从乌石带回一袋最好的乌叶荔枝,人们都说乌石村的荔枝是最好的,壳薄、汁甜、肉结实。可是我却没吃到,我非常生气。结果我妈说:你吃了快半盆呀,看把衣服前襟都滴满荔枝汁,洗都洗不掉……原来父亲到家时已经晚上,我已经睡着了,想着荔枝放隔夜了就不好吃了,父亲就把兄弟姐妹们都从床上叫起来吃荔枝。我是在半睡半醒之间把该吃的都吃了,至于乌石荔枝的滋味却浑然不知,这跟没吃有什么区别呀!所以,我还是很生气。
2
那个暑假,低年级的放假早,母亲怕我一个人在家,或者是我玩疯了,或者是她会气疯了,就把我送回父亲老家,那边有我奶奶,还有二叔三叔、堂哥们管着我,再怎么疯也不至于无法无天。临行时,还塞了本铅印的《唐宋诗选读》,要我每天至少得背一首,她会交代堂哥督促我每天看书、背书。堂哥是我的宿敌,一向对我不友好,会把绑了线的金龟子缠在我的辫子上,我又爱哭,他们就一群人学我哭,奶奶就拿着棍子揍他们,他们就再次找机会作弄我,于是这仇恨就这么没完没了地恶性循环着。母亲让他们来约束我,那简直就是“助纣为虐”。尽管有讨厌的堂哥们,可我还是喜欢回老家。
老家本是个渔村,地少人多,很多人靠海吃饭。后来海边建起了大坝桥闸,拦住了汹涌的海潮,多了不少的田地,鱼虾却少了。只是这些土地并不肥沃,种番薯不错,水稻却总是产量不高。所以奶奶煮的粥里总是放了很多番薯签(刨成细条状的番薯),米粒却少得可怜。因为人多,柴火灶上总是熬着一大锅番薯粥,如果有贵客来,就用笊篱捞起干饭,其他再熬一会儿,还是一大家人的主食。这种番薯粥看上去黏稠,却特别容易饿,叔叔一家人多是干重活的,他们就特别嫌弃番薯粥。我没被饿过,所以不怕饿,无比喜欢这大锅熬出来的这番薯的甜。
海边丘陵地庄稼长不好,荔枝树却根深蒂固。村里有成片的荔枝林,那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一棵都是两三层楼高,有荔枝树的人家一般都是祖上比较富有的。我们家不富有,却因二叔在村里德高望重,有户人家因为生活在外地,就把祖产荔枝林托付给二叔照看,等到收成了再五五分。6月份暑假开始时,荔枝已经挂满枝头,只是还没熟透。却得开始看管了,不然会有人专门偷摘荔枝的。一些老枞荔枝树,也许是实在太老了,挂果不多,又高又粗壮,人们就在树干上围满了仙人掌、刺蒺藜,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防盗法,特别新鲜。二叔的荔枝林有一二十株荔枝树,有大有小,单靠围刺蒺藜是不够的,一些人梯子一靠,或者一根竹竿,就可以把果子捋走了。堂兄妹们就在林子里搭了个简陋的棚子,白天黑夜轮流着看管。偷果子的人也是比较文明的,只要有人在,一般就不敢下手。
我太喜欢看管荔枝的生活了,整个林子的荔枝都在我眼皮底下,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有了选择的权利后,我也开始挑三拣四,因为季候未到,多数荔枝都还青涩着,只有向阳处的果子早早地由青转红。可这样的果子多数在树梢头。荔枝的枝干多是旁逸斜出,到了树梢,那枝丫就细长柔弱,一般人是攀爬不到的,只能靠工具。尽管靠工具,但每年因采荔枝而摔伤的人还是挺多的,有些枝干看似粗壮,却是“鸡腿枝”,底部粗壮,却与主干联系不够,特别容易开裂,人一旦踩上去就折断了。还有一些用梯子的,枝干太柔韧,一压一晃,人就摔下来了。荔枝还没全面开采前是不能用工具的,因为怕影响了果子成长。爬树是我的专长,再细的枝干我也敢上,不知道是身子轻还是真的有神相助,在那颤巍巍的枝丫上,我竟然都能得偿所愿。不知道是嫉妒还是真的担心,堂哥竟然跟奶奶告状,说我为了采荔枝“惊死人”,哪天摔死了都没人知。为了安抚奶奶,我带了一堆书到荔枝林里。奶奶虽然不识字,可对于一个爱看书的孩子她还是不会阻拦的,何况还能帮忙看管荔枝林。那堆书里就有母亲交代的唐宋诗选,可是在诱人的果香里,除了那首很应景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外,其他的我根本就无心背诵。倒是从村里租来的那几本金庸武侠小说,尽管字还没认全,我却都看进去了。以至于我后来在枝头上蹿下跳时,不再有当初的沾沾自喜,而是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什么时候我才能像段誉一样凌波微步呢?如果我有那样的功夫,我想我就可以终日栖息在荔枝树上,壮志饥餐荔枝肉,笑谈渴饮荔枝蜜了。
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会腻,荔枝是吃不腻的,但至少不像当年那样的迫切。无聊时,我会把荔枝上的硬壳小心剥掉,把白色的薄膜留着,这是很考验耐心的工序,如果荔枝红透了,薄膜也会沾上一点紫红,特别可爱,我们称这种脱了壳的荔枝“电灯泡”。可“电灯泡”也就只能维持一二十分钟,半小时后,它的白膜就会发黄变硬,一碰就破。如果剥得好的话,去掉白膜的荔枝,里层还有一层透明的膜,牢牢裹住荔枝的汁液,这层透明的膜的厚薄松紧直接影响荔枝口感。薄膜紧实的荔枝剥开,晶莹透明、温润如玉,不仅肉筋道,汁甘甜,单就外形上就特别赏心悦目。后来上初中时,生物课上讲到细胞的结构,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时,我总会吞着口水想起荔枝,那活脱脱就是一颗大细胞。
3
因为爬得够高,我看一切的角度都跟平时不一样了。在树梢上往南看,可以看到很远很远处的一道白光,那应该是传说中曾经奔涌到村口的海潮。往北看,就是后山,那里是我们村庄多数人最后的归宿,山上除了石头灌木,最多的就是坟头,我曾经跟着堂妹们去放过羊,也跟着二婶去打过绿豆。此刻,有个人影正扛着铁锹晃悠着从山上下来,那是我三叔。三叔很少干农活,这会儿扛着农具出现可真是奇观。三叔在村里被人称为“歹仔”,类似于北方人说的“二流子”。我爸和二叔提到他们这个弟弟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我们这些侄子辈却都跟他亲,因为他没架子,不像二叔总是板着脸,他有什么好吃好喝的都会跟我们共享。特别是我那几个堂兄,跟着他抽烟喝酒做小生意,比自家亲爸还投缘。小叔从荔枝树下经过时,一个荔枝核精准地砸在他的脑壳上。三叔一抬头笑了:“阿阔啊,不怕你叔我捏死你啊?”我因为额头开阔,老家人叫不了我那文绉绉的名字,干脆就叫我“阿阔”,这样形象好记,可这对一个女孩而言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谁这么叫我,我都翻白眼,或者就当作没听到,只有三叔这么叫我时,我不跟他计较。我把手上那串好不容易摘到的鲜红荔枝朝他晃了晃,想想这些大人笨得很,肯定爬不上树的,就一溜烟从枝头滑下来。
“阿叔你又去掏老坑了?”有一阵子听说三叔勾搭上一伙邪道上的人,他曾经给奶奶一个奇形怪状的黄豆大小的东西,说是珍珠,完全颠覆了我对珍珠的印象,如果不是中间有个穿孔,我都觉得它就是我刚掉下的乳牙,更不要说什么洁白晶莹。可三叔说那是老坑货,埋土里沁久了发黄,金贵得很。奶奶给了他钱,他收下了,二叔就骂他是来骗老人家的钱。可我妈说,你奶奶能给他多少钱呀,你小叔那些东西放市场上卖,都是古董,可以卖更高的价。小叔后来还给奶奶一个玉镯子,也不是我印象中玉该有的翠绿颜色,而是泛着黄,中间还有一丝丝血红,三叔说这才是真正的老坑货,做旧做假是做不来的,那是玉几百年上千年在古墓里深埋,沁了土色与人的血色才形成的。有点瘆人,可奶奶却欢喜得很,把那黄中带黑的珠子串在她黑不溜秋的银耳环上,还有这玉镯子,一直都戴着,直到去世。
“细囡儿不要乱说话!”三叔剥了个荔枝塞嘴里,敲了敲我的大脑壳。
“我那天在后山看到又有个墓被挖了个洞,黑乎乎的,半块棺材板都被掏在外头了。”后山那些古老又无主的墓,杂草总是很茂盛,羊特别爱往那儿拱,我总是又害怕又好奇。
三叔笑嘻嘻的:“囡仔有耳没嘴,看着听着不乱说哦。那些坑是他们掏的,挖人祖坟的事我是不干的。”停了下,又说道,“这种力气活,我才不乐意呢,我也就帮他们看看货的品相,联系下家。”这我们是知道的,二叔常骂三叔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
三叔是个绝对的现世论者,总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他才不想讨论那些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无聊话题。吃完荔枝,拍拍屁股,扛着铁锹,晃着三角肩回家喝酒去了。
留在我手里的是几个还沾着泥的老铜钱,上面写着“咸丰通宝”,虽是繁体字,但那会儿这种铜钱很常见,所以我都看得懂。那是三叔今天的战利品。我用细铁线把它们绑在一起,上面再绑上几根鸡毛,就是一个完美的鸡毛毽子。每当在树上荔枝吃撑了,我就在树下踢毽子消食。叠压着的铜钱一踢就发出清脆的响声“嚓嚓嚓”,和鸡毛一起飞上了天。在氤氲的荔枝香里,随着毽子往上飞的有古人的阴魂,或许还有鸡的灵魂?
4
那些日子里,我尝遍了荔枝林里不同成色的荔枝的滋味,是乌叶还是早红(品种名),不用剥开,瞄一眼壳上刺头的深浅就知道。荔枝的果核是大是小,看果尖就辨个八九不离十,就连并蒂的双胞胎,哪颗向阳,哪颗背阴,一尝滋味便知道。堂哥们说我是吃得精了。“日啖荔枝三百颗”,岂止三百颗!
据后厝叔公讲,荔枝性热,阴虚火旺者慎服,小儿最不宜多吃,一方面上火,一方面伤肠胃。我姐吃多了会流鼻血,有时还发烧,时不时得熬柴胡、黄连水。父母对她的关爱明显比我的多,我曾经很羡慕她有这样娇弱受宠的身子骨,偷偷尝了一口她喝的黄连水后,一口吐出来,呸,还是荔枝好吃。我还是当我的野生放养娃快活。
6月初,满树的荔枝都挂着或多或少的红。这时的荔枝果肉已经饱满,甜中带酸,一般要等它整颗泛红,那时的甜度达到峰值才采摘。此刻却是最需要看顾的时候,一是防盗,另一是防天气,如果大风暴雨就得赶紧采下,不然等风雨摧残后,果子就不值钱了。大人们来园子看管的时间多了,我也没那么自在了,刚好村里过王公生日,我的战场就转移到奶奶的灶台边上了。
“王公生”是村里的重大节日,不知道是为哪个王公过生日,每个村庄的“王公生”日子是不一样的,刚好可以轮流“吃节”。每到过节我就对奶奶无比崇拜。一样的米,她可以做出许多种糕和粿。一样的糕点她做得都比别人家的精细,好吃、好看。奶奶娘家以前是卖米糕的小贩,有一手糕点好手艺,只是后来粮食吃都不够,这好手艺就搁置了,只有年节时才得以施展。
大灶大锅,放着大大的竹蒸笼,铺着已经泛黄的蒸笼布,带水碾好的米浆,倒进去一层,等米浆稍凝固后,再倒一层炒过葱头的香油,那油混杂着猪油、花生油、芝麻油,不是一般的香。一层米浆一层油,一层层倒进去,足有七八层。蒸熟后,切开油粿,颤巍巍的,米白油黄,软糯鲜香。除了油粿还有米糕。碾细的米粉,蒸过炒过后,和上炒好的花生粉或者绿豆粉,在精致的模具上压实拍下,一个个小米糕便排列在簸箩上,再用裁好的五色纸,五六个小米糕包成一包,五颜六色,打开来,花生糕香、绿豆糕冰爽,入口即化,真的是人间美味。此外还有花生粿、凉粿、松糕、油片糕……
最耗时耗心思的是水粿,一样是米浆,要不停地搅拌,让它筋道有韧性,还要加上适量的碱,保证它的口感Q弹冰爽。分时分层倒入,每一层倒入的时间火候都得刚刚好,这是最考验技术的时候,因为这直接影响最后的揭层。蒸熟晾凉后,用线切成大小块,每块都可以一层层剥离,一片片的白中带着浅绿,好看又好吃,比后来哪一种果冻都好吃。我母亲最爱吃这一口。我曾经把一片片剥下来的水粿与去核的荔枝肉拌在一起,一样的晶莹透亮,一个寡淡中带着碱味,一个香甜,吃过的人都夸好吃。后来在市场买到所谓的水粿或者叫“碱粿”的,外形看差不多,可是切开,却怎么也剥不了层,那便是手艺不行,火候把得不够,每一层都粘连在一起了。
最神奇的是石花粿。说是粿,其实跟米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熬煮出来后的外形相似而已。石花是长在海里石头上的一种藻类,富含胶质,有点像切碎了的白木耳,渔民们采上来后,晒干了,可以搁置很久。石花在干净的锅里小火慢煮很久,里边的胶质慢慢地释放出来,捞出残渣,汤汁放盆里晾凉后,倒扣盘上,就是一个巨无霸果冻。用一个带细孔的刨刀,轻轻一刮,就可以刨下一条条细长细长的石花条,加水加蜜,吱溜一吸,好玩又好吃。如果再加上剥好的荔枝肉,放玻璃杯里,那就是满杯的晶莹剔透、流光溢彩。
5
王公生日过了,6月底,荔枝终于熟透了,主人家、二叔家,所有人扛着梯子、板凳,还有大大小小的箩筐,都到荔枝林里。古人说荔枝“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其实即使在枝头,成熟后没摘下,靠近蒂头、核壁处的荔枝肉也会因为过于成熟而发黄变硬。叫这么多人手的目的就是要在一天内都采摘完。
我是个人来疯,大家忙着采摘时,我就在高高的树冠上,帮忙着把那些长在最顶端、梯子也靠不到的荔忙枝采下来。主人家的大姐姐指着我问堂哥:“这猴子是哪里窜来的?”我想如果我哄她是从古墓里窜出来的,会不会吓得她明年不敢来呢?明年她有没有来我不知道,因为在那年之后,我再也没机会在那个最好的时间去遇见最美妙的荔枝了。
荔枝都采完了,被收购走了。二婶挑了串最好的给了我,我把它们放吊桶里,在井底里冰镇着。
浸过井水的荔枝清甜甘爽,可我竟然吃出了一点点甜蜜的忧伤。
责任编辑 韦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