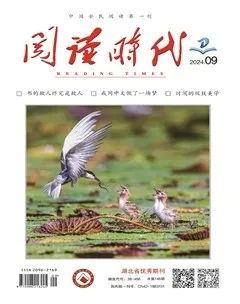孙髯翁:万树梅花一布衣
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时任云南巡抚的王继文在昆明兴建大观楼。大观楼建成后,历经康熙、雍正王朝近半个世纪,所有为之题赋的诗文均未能给大观楼添彩。
直至乾隆年间,一介布衣诗人孙髯翁登高远眺五百里滇池,一时心绪激荡,提笔一挥,成就旷世名作: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全联一百八十个字。此联一出,谁与争锋!尔后,孙髯翁大观楼长联被冠名“天下第一长联”。
这或许是布衣诗人孙髯翁从未想到过的。
孙髯翁何许人也?
关于孙髯翁的现存史料,多出自与孙髯翁同时代人师范于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纂写的《滇系》和《云南省志·文物志》。师范与髯翁属于忘年交,故所写史料可信度较高。
据传,孙髯一生下来就有胡须,故取名为“髯”,字髯翁,祖籍为陕西三原人。因其父以武职宦滇,随父寓居昆明。
髯翁自幼聪明,博闻强识,熟读经史、习诗古文,每次出游,总要带着几卷诗书进行阅读背诵。由于髯翁从小就受到诗书的熏陶,写的古诗文极好,可说是年少成名。
史料记载,髯翁早年去参加科举时,看到科场搜身,愤然曰:“是以盗贼待士也,吾不能受辱!”从此不问科举,终身布衣。暂且不论此史料是否真实,髯翁一生虽富有才识,却无意于仕途是亲友们的共识。时任云贵总督示意云南府太守和书院山长催促其应试科举做官,皆遭拒绝。
事实上,髯翁之所以不愿出仕,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历代文人雅士们都喜欢以花草言志,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们的一大特点。髯翁也不例外。他尤为喜欢梅花,曾自制一印章,刻有“万树梅花一布衣”,自号“梅花大布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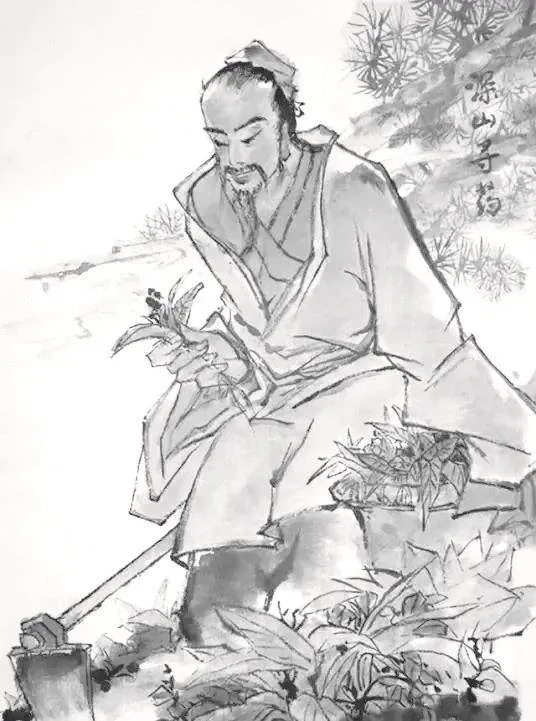
梅花,乃四君子之首,其代表着高洁、风骨俊傲、不趋荣利的品格。故此,髯翁以梅花明志,表明了自身不慕名利、不陷世俗、安贫乐道的人生志向。
孙髯翁虽未为官,但却有着一份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自元、明至清以来,昆明虽地处西南偏僻之地,但经与中原文化、经济、政治的交流融合,社会得到发展,城市的规模逐渐扩大。然而,贯穿昆明古城的盘龙江水患却严重地危害着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一到洪涝季节,河堤经常决口,给两岸的黎民百姓造成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据《新纂云南通志·地理考》记载,河水往往“冒城垣,荡居民”,给昆明城郊造成严重损失。清朝初年,由于六河年久失修,不仅在降雨量过多的年份“洪涝为患”,即使在干旱年份也因各自为政,纷纷筑坝抢水,导致一旦坝倒,泥沙石块就淤塞填河,稍遇大雨,上游河水就泛滥成灾。
髯翁目睹水患过后“举凡环江之屋,倾坏者十之四五,致使老少男女,失所飘零,婴童处子,负携巷哭”的惨象,内心便燃起“为生民立命”的宏伟志愿。
为求根治水患的方法,髯翁溯江而上,“穷岁月之跋涉”,经过实地考察,仔细研读,“闲披禹贡、桑经、邮注之书”后,最终完成水利著作《拟盘龙江水利图说》。他在书中提出五点水利治理建议:一是“疏壅畅流”;二是“分势防溢”;三是“闭引水为害”;四是“改一水,锁群流”;五是“因时得所”。
然而,当髯翁极为兴奋地将所著《拟盘龙江水利图说》呈与官员时,却被置之高阁,令髯翁极为愤慨。这些官员们只忙着如何搜刮民财、中饱私囊,以便任满时满载而归,哪会去管百姓的疾苦和痛痒。河道得不到整治,惨剧依旧继续上演。
直到髯翁逝后55年,昆明乡绅筹划整治盘龙江,士子林松无意间从朋友处见到《拟盘龙江水利图说》,如获至宝,评书道:“自源至委,凡利之所在,害之所积,言之最详。及疏之何方,导之有术,亦靡不筹之最当。”尔后,此书也成为后世治理盘龙江水患最宝贵的实证材料。髯翁苦心孤诣所著之书终于为百姓作了一些贡献,算是圆了先生之夙愿。
按理说,髯翁所具有的才华、能力以及人脉,外加在大观楼所留的一百八十字长联名震天下,足以让其衣食无忧,但事与愿违,髯翁中年丧妻,晚年穷困潦倒。
据有关史料记载,髯翁回到昆明后,生活极为窘迫,好友圆通寺主持怜悯他的境遇,就让他住在大殿后螺峰山之阳的咒蛟台上,这也是他自号“蛟台老人”的由来。髯翁在蛟台处摆了个招牌“蛟台老人测字占卜处”,以此营生。
当时来占卜的香客并不是很多,髯翁每日“求百钱不可得,恒数日断炊烟”,故而写诗自嘲道:“枕头肚里是秕糠,耗子因何少得粮?咬破任从天替补,空空如也又何妨!”
当然,他也并不是没有饭吃,只是拒绝了朋友的周济。每当友人来探望,总是说:“我是过得下去的!”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髯翁女婿为尽半子之责,接其到弥勒奉养,后髯翁受聘讲学,终老于弥勒。其生前自撰挽联曰:“这回来得忙,名心利心,毕竟糊涂到底;此番去正好,诗债酒债,何曾亏负着谁?”展示其一生旷达自守、不慕名利的清正之风。
纵观髯翁先生的一生,他虽没有如李白、杜甫、王勃等大诗人,一生著诗无数,天下闻名,但他却在大观楼题联一副,被后世传颂;他虽没有像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等人踏入仕途为生民立命,却在目睹盘龙江水患后,执笔著述《拟盘龙江水利图说》以求根治水患,为百姓求一方平安。
他这样的人不求名,亦不求利,“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他所留给世人的只不过是一个“布衣诗人”的称号。
而正是他这样的人,给世人留下了最为宝贵的东西。
(源自“知乎”,标题有改动)
责编: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