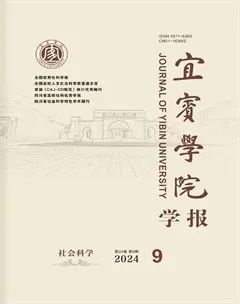从“绝对风格”看朗西埃对萨特的“哲人王”批判
摘要:福楼拜受“为艺术而艺术”思潮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绝对风格”式写作,他刻意保持一种客观的叙事方式,避免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意图。然而萨特认为,文学应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作者应借助作品传达相应的思想,因此福楼拜的“不介入性”成为萨特批判的重点。而作为相对晚近的思想家,福楼拜的“绝对风格”以及萨特的反应也得到了朗西埃的关注。基于“激进平等”的主张,与萨特针锋相对的是,朗西埃不仅认为“绝对风格”实际上解放了读者,他同时也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介入文学观是一种“哲人王”傲慢。因此以“绝对风格”为线索,可以管窥朗西埃对萨特知识分子姿态批评的根由。
关键词:绝对风格;福楼拜;朗西埃;萨特;介入
中图分类号:I01
DOI:10.19504/j.cnki.issn1671-5365.2024.09.03
朗西埃早年曾受到过萨特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不过对于后者的知识分子傲慢,朗西埃则将之形容为“哲人王”并予以批判。有趣的是,他们两位都曾对福楼拜的写作风格产生过兴趣,而两人对此截然不同的看法也成为朗西埃对萨特批判的攸关所在。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法国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其独特的“风格”(style)理念招致了许多批评与讨论。他将“风格”与形式挂钩,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1852年致露易丝·科莱的信中,他就曾说道:“风格只是艺术家个人独有的看待事物的方式”[1]461,这句话及其蕴含的纯艺术思想旋即成为福楼拜的代表性主张,对此朗西埃概括为“绝对风格”(style absolutisé)。还原到福楼拜所处的时代,他“风格的绝对化”的写法就是对既往文学等级制的破除,福楼拜在其信件中曾一再申明,“美”产生于形式,而他通过“绝对风格”将形式表现到了极致,因而他的写作充满了琐碎的细节,不掺杂任何主观的情感[2]77。这种写作方式招致了萨特的激烈批评,却被朗西埃视为文学平等的契机。
一、“绝对风格”的不介入性:萨特对福楼拜的批判
萨特早期对福楼拜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著名的《什么是文学?》一文中。由于福楼拜的“绝对风格”写法与萨特的文学介入观存在冲突,这一时期的萨特对福楼拜可以称得上是十分“厌恶”了,其中他对福楼拜的批评主要可以总结为两点:福楼拜拒绝承担作家的责任、拒绝与读者交流,因此作为作家的福楼拜,其存在是难以成立的。
萨特继承并发扬了胡塞尔的意向性主张。他认为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没有“我”的意识世界依然是存在的,所以主体只能被圈定于现实世界中。因此,其一,人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人需要承认自身在世界中的自为性,人(包括作家)总是要面对当下的世界和当下的人群;其二,客观世界与“我”密切相关,没有“我”的客观世界也就丧失了“我”的主体性。从萨特对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可以看出,在世界中存在的主体意识是经由肉身显现出来的,人的意识是肉身性的意识,“我”的世界通过身体向“我”涌现,“我”也通过身体向世界敞开,“我”的身体是“我”向世界展开的“意义和朝向”[3]48,“我”被世界所经历,“我”也通过身体与世界进行着互动。按照萨特三重意识的观点,原初的意识即前反思意识(pre-reileclive conscious⁃ness)离世界最近,但这时“我”还没有出现,到了之后的反思意识(reflective consciousness)和以意识为客体的自我反思意识(self-refle ctivecon⁃sciousness)阶段时,主体的“我”就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了。因此,对意识来说,“自我”(ego)和世界都是客体,前反思意识对“我”产生的斥力使“我”更接近外部世界,“我”因此和世界互相影响,“我”也因此更能够积极地介入世界。而审美喜悦就是一种位置意识①,这种位置意识使人感受到世界的价值,世界成为人的存在的方式而使人存在,所以这种位置意识越强烈、世界越外在于人,人也就越深刻地处于这个世界之中、世界也就越属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非位置意识将人和世界整个自由和谐地包裹了起来,所以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本身就要求人主动地介入到世界之中。同时,对于“我”来说,身体并非客体世界向“我”的简单投射,而是客体世界使“我”看到了我们的身体。“我”存在于我的身体中,身体是“我”的情境,因此“我”朝向客观世界进行活动就是对身体的超越,也即萨特所说的“自为”(for-itself),这一自为的过程就是意识到人的自由进而超越的过程。萨特基于“绝对自由”的观念而对人的自为怀有无比坚定的主张,认为人既然存在于世界之中就应该努力自为、努力朝向人的自由。人的这一努力就是对自己的存在负责的体现,人倘若不创造、不追求自由,就失去了在世界上存在的正当性。
这种绝对自由导致萨特产生了一种极端的焦虑。意识与世界的独特关系说明人在世上的存在是偶然的,人需要不断地保持清醒的意识,需要不断地依靠自己的意识作出决定。人生来所拥有的本体自由使人的行动具有一种紧迫性,人需要不断地行动才能不断地超越当下的情境。而对于作家来说,由于写作就是一种在场,作家的写作具备着揭示世界的责任,因此写作就是作家的自为,就是作家追求自由的途径,人要使有“人”存在的世界显示出来。在此意义上,萨特认为福楼拜的“绝对风格”只是揭示了万物的本原自在,他放弃赋予万物“人”的意义,这一行为也导致作家丧失主体性,以这种方式写作的作者根本无法对世界施为任何影响。
早期的萨特对情境和他者都持怀疑态度,他要求人不断地自为超越情境获得人自身的主动性。人首先面对的是自己肉身的情境,人的肉身同时又处在具体的时代情境之中,个人应融入时代,将历史肉身化(embody)、将绝对自由情境化,这时个体才是完全介入的。对于作家来说,他应当放弃自己的全知视角,虔心地下沉到时代中去书写自己所处时代的作品,作家须面对、承担时代的义务。作家是时代中的作家,整个时代就是作家要面对的情境:“既然我们在处境之中,我们惟一可能想到去写的小说是处境小说,既无内在叙述者,也无全知的见证人” [4]258。然而福楼拜的“绝对风格”却保持了一种全知的视角进行冷漠叙事,《情感教育》的主人公福赖代芮克看见闹革命的人群甚为冷漠,认为好像是在“看戏”,主人公拒绝与时代共情,法国的剧烈变动甚至抵不上他自己的感情私事重要。不仅如此,福赖代芮克身上展现的冷漠有时匪夷所思:他在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死亡的时刻想着的是情人阿尔鲁夫人;而同时他对她尽管爱得热切,却对其丈夫阿尔鲁毫无嫉妒之心。在现实中,福楼拜自己也说过想要“归隐田园,从事文学,无求于人”[5]33,他本人就具有一种诡秘难测的冷漠情绪,他不仅对他所处的时代厌恶,同时对自己所处的阶层厌恶,甚至对整个人类都存在一种厌恶之情:“人类给我们苦吃,我们也给人类苦吃!噢!我要报复!我要报复的!”[5]264福楼拜在这样的心态下毫不留情地审视人类,他的文字无疑也成为萨特所认为的拒不融入时代的样本。在萨特看来,福楼拜的“绝对风格”写法无疑是其主动采取的、规避责任的借口和手段,在其所处的风起云涌的年代竟不肯承担责任,完全避免将自己的人物与时代结合起来,这自然令萨特十分不满,而这种“绝对风格”自然也就不符合萨特所要求的积极介入的文学观念。
同时萨特一直怀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因此他也给作者提出了强力的人道主义要求。他认为人不仅要认识到自己的自由,而且应该给其他人带来自由,作家尤其应凭借其写作的能力不断地解放读者并从而实现自己的自由。故此作者应该让读者感到对这个世界负责任并主动地改造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在发明自己的出路的同时也就发明了自己。人需要每天被发明。”[4]306]因此交流在萨特的思想中是十分重要的,作家只有和读者在交流中才能构建情境,而有了情境人才有自我超越的可能。萨特认为,写作是作家正当化自己存在的方式,作家需要与读者对话,需要读者来使作家的存在合法化,即作家存在的正当性在于与读者交流。物在人的创造下通过人的想象抵达世界,人在这样的物上感受到审美喜悦,人感受到了有人存在的世界的价值,同时也就对此世界具有了责任。读者在阅读时会解除自身的人格以及自身的怨恨、恐惧等心理,这时读者就会在阅读中产生一种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自由意志。
同时,萨特还要求立足于现实,认为应该通过作者的作品使读者的“善良意志历史化”[4]293,使读者通过作品的影响把人的自由、被压迫者的自由视为绝对目的,进而产生拯救他人的愿望,这也正是萨特追求的“解放”:只追求个人的善良意志是不现实的,而追求普遍的善良意志才是人应该做的。
为了实现作家与读者的交流,作家的写作必须在场。萨特认为作家只有将自己置入人民之中,人民才会真正地去阅读作者的作品、才会反过来主动置入作者的情境,这也即萨特所说的“召唤”。为了“召唤”读者,为了在场,萨特具体讨论了文学创作所依赖的“想象”。萨特认为,想象是一种行动,是产生自人身体中的意识,因此想象以一种肉体意识意图其客体,“想象在肉体性上意图它的客体,意味着想象意识对它的客体是以其具体个性的占有,而不仅仅是一个拟像的生产”[6]423。想象的行动使被想象物先缺席后在场,这种“缺席—在场”具有一种黏合性,读者意识因此将被召唤于此种“缺席—在场”中,想象的行动性也因此可以被体认。而阅读首先应是一种感知的综合,作者应为读者提供这种感知的可能,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以想象的方式参与感知之中。在萨特的认识里,作者所揭示的世界“必须是一个生成”[4]139,作品不能只是描绘,而应当将描绘的世界视为一个目的。但是像福楼拜一样的“现实主义者”只是“用心观察”和“描绘”,只满足于“叫出对象的名字”,福楼拜的“想象”在萨特看来是纯粹的复刻真实而非真正的在场,这样的写作也根本无法实现对读者的召唤。因此,福楼拜的写作是非创造的,读者在阅读这种作品时也无法创造任何东西,读者因而也就无法感受到自由和人所赋形的世界的存在。
萨特不赞成彻底地描绘现实,也不赞成完完全全的想象。想象的意识是具有肉体性的,想象物是一种综合感知物,而完全脱离实际的想象物如“人马”(centaurs)则只能被意识但无法被感知。想象的世界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约定的世界,读者允许自己短暂别迷住,这时“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直到这种魔力结束”[6]433,所以具有适当想象且能够联系真实世界的作品能够将读者吸纳进作品的世界中去,形成良好的互动。故此,萨特主张艺术作品应该有内容(con⁃tent),有内容的想象性作品才不会被读者轻易洞穿。作品的内容由有意义的意识组成,有意义的意识常常来自角色的情感,萨特也就因此十分重视作品的情感问题。读者通过对作品人物的行动推断和情感推断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想象,这个过程是一个实现整体感知的过程(行动感知和情感感知),而他对福楼拜不满的原因之一还在于,福楼拜过于认真地刻画作品细节,而使得作品的主要行动和情感无法聚焦,难以形成被感知的整体,这就破坏了综合感知的形成,读者的参与感也就会被大大降低。
萨特早期对他者的敌意也是他对福楼拜产生恶感的原因之一。对于“他者”萨特曾举过一个偷窥狂的例子:当从门孔里偷窥的偷窥者被他者发现时,偷窥狂就瞬间陷入了极度的窘迫之中。他者的目光让“我”遽然意识到“我”自己的身体实际上是在“我”的意识之外的,在他者那里“我”的身体是作为自在而存在的,因此“我”的身体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意义之前的、是虚无的,“我”在被他人注视为一个客体时,“我”就成了为他人而存在的存在,对此“我”什么也做不了,“我”的意义只能由他人片面地赋予。萨特认为福楼拜的“绝对风格”导致的正是这样一种结果。福楼拜使用冷漠的目光观察一切,“上个世纪的枯燥乏味的描写是拒绝使用的表现:人们不去触动世界,人们只是用眼睛生吞活剥世界”[4]266,福楼拜的目光使事物变得无意指,剥夺了事物的情境,同时他的目光也进入了读者,他“绝对风格”的写法也削弱读者的存在,作为读者的萨特在这种被凝视中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福楼拜的目光使读者也进入了他的绝对凝视的情境之中,读者不仅无法和作者进行交流,而且读者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读者在他的作品中仅显现为一个切面,读者失去自为的可能因而无法达到其本真,这是萨特所无法忍受的。福楼拜的不作为不仅是不承认自己的本真性、不肯使自身的“作家”存在合法化,而且他还拒绝与读者交流、拒绝让读者去追求自己的本真。在福楼拜的这种绝对目光的逼视之下,萨特认为福楼拜不仅否定了自己,而且还以无意义的眼光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巨大的他者,从而冷漠地否定了他笔下的世界。福楼拜扰乱了事物的秩序,固定了人物和情境,他“绝对风格”的目光使人物和读者都失去了行动的可能,这自然违背了萨特要求的作者和读者互动的原则。萨特认为在福楼拜的绝对注视下,交流根本无法实现,他的目光使事物暴露为不能自为的存在,将作品呈现为一种不可阅读的石化和荒漠化。
二、一种别样的文学介入观:朗西埃与萨特的分歧
朗西埃的思想与萨特具有一定的亲缘性,他较早地接触了萨特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且后者对其激进平等的主张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朗西埃认为,萨特的人道主义有其虚伪的一面,其症结正在于其作为知识分子傲慢,亦或者说“哲人王”傲慢。他穷其一生都试图将福楼拜纳入到自己的哲学框架中,否则福楼拜就将成为其“知识分子雄心”的败笔。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表达出来的最主要的观点之一就是,文学不应只是否定性的还应是创造性的。萨特认为阅读就是创造[4]137,读者的阅读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因为读者的阅读是作者获得自由的关键所在。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既在揭示又在创造”[4]124,尽管萨特一再声称作者不应该引导读者,但是他还是矛盾地说道:“一句话,阅读是引导下的创作”[4]125。可见萨特虽然指出了读者的创造性,但是他仍然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不断揣测读者。萨特认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由于受到作品影响所以会降低自身的主动性甚至转变为被动性,他太过于迫切地想要实现作者的自由和自己的自由,所以工具化了读者,他的人道主义视作者为读者的解放者,作者是实现读者自由的关键,读者需要借助作者才能完成属于作者的艺术品创造,进而见到本属于自身的自由。萨特拒绝将读者视为情境,也否认情境产生作家,而只愿意将读者视为“另一个人”,即他者。在萨特的思想中,他者乃是“我”之存在、“我”之自由的实现的证明手段,因此早期萨特的读者论也可被认为是他的他者论,读者的阅读是作者通过意识在读者(即他者)身上实现作者自身自由的过程。因为他认为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只有主观性没有客观性,无法感受自己的作品,需要他者进入自己的作品才能形成完整的艺术品。“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4]124他把作家创作的作品视为一个事件并设想了一种“纯洁”的艺术品,读者的出现弥补了作者在作品中过分的主观性、通过读者的意识将书中的审美对象转化为客观存在,为此读者的意识至关重要,读者的阅读面对的其实是一种未经作者主观性“污染”的“先此存在的材料”,两个意识的相遇创造了“艺术品”。这一过程乍看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实际上读者不过是作者自我超越的工具而已。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自己的想法,不断与作者的想象交流、论证,证明想法的对错,最后只是帮助作者实现艺术品:
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4]126-127
写作是求助于别人的意识以便使自己被承认为对于存在的整体而言是主要的;写作就是通过其他人为媒介而体验这一主要性。[4]138
萨特所声称的交流,实际上不过是需要让读者印证作者的想法,作家对于自己作品的判断明显要比读者更具权威性,因此所谓的解放和自由其实都是由作者带来的,读者只是作者需要的一个解放对象而已,如果没有读者,那么解放就是不成功的,作者的自由也就无法实现。归根结底,与其说萨特更为关心全人类的解放,不如说他更在意自己的自由能否得到实现——这也是他千方百计想要“囊括”福楼拜的原因。当然,萨特的英雄主义使他认为,作为作者的哲人能够带给其他人解放,那么哲人的自由也就事关所有人的自由了。故此,萨特所谓的“读者自由”根本无法离开作者本身,其介入的文学本质上就是干涉他人自由选择的文学,因为对读者有自身之“自由”的承担能力,他始终持怀疑态度。尽管萨特要求作家应与人民站在一起、放弃作家的精神英雄地位,但是他还是认为作家本质是要“以一个自由为依据,把世界介绍给另一些自由”[4]210。故此,只有作家认识到现实的不自由情况,才能“呈现”自由。
朗西埃与萨特具有的巨大分歧也在这里,与阿尔都塞决裂后,朗西埃的许多思考皆是为了去反对那个“无知的教师”。他不像萨特一般将重心放在作者身上,他更为关心读者能够获得什么、读者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作者和作品不过是读者自由的中介。朗西埃批判萨特的“哲人王”立场,认为萨特为了维持他的辩证法门而不断地筑起高墙,劳动者被视为是生产辩证法的工具②,这始终是萨特无法摆脱的知识分子姿态,也是朗西埃对这一类“教师”类型的思想家反复批评的根由所在。朗西埃摈弃了萨特的英雄主义倾向,更加重视读者最终自身的主动性,而不是把读者视为作者自由的实现工具。
萨特对所谓“现实主义”的攻击中包含了对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攻击,这同样也是朗西埃对萨特思想有所发展的一个方面。萨特认为,“现实主义”只是“用心观察和描绘”但是不行动,而描绘无法提供作者进入的通道,描绘出来的事物虽然纷繁复杂但缺乏情感密度,读者只能处于事物的外部世界而不能深入到作品的内部世界,在这样的作品中读者仍处于前反思性的“非位置意识”中。因此“绝对风格”就是一种绝对的否定,萨特认为它使用精神(意义、句子)围困了现实存在(自在),在这种合拢的句子之下虽具体实在但完全丧失意义,成为前反思式的事物。他也因此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 福楼拜的句子既聋又瞎,没有血脉”[4]190,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本无法获得情感上的审美愉悦,故而也就无法承担起自身的责任,作品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其自身的艺术价值。朗西埃便是沿着这一条路出发,通过“感性配享”③(lepartage du sensible)的思想使事物具有了单独渗透进读者感知的可能,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是出自萨特的理路。萨特认为持有无阶级立场的作家应该放弃使用精神权力去压迫人民的做法,无阶级的作家应注意到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并主动投入人民中间去、展示这个世界的“惰性”和不透明性。从此作家不再是精神英雄,作家也不应再片面地崇拜那种单一的绝对精神,而是应该将事物精神化,将那些惰性事物和不透明事物写进书中去,以此使文学自由在场,同时也将自由呈现给读者,并让读者去评判。在这一意义上,萨特认为福楼拜具有一种资产阶级性,他认为无论文学如何声称自己的独立自主性,文学“它自己就是意识形态”[4]183,因此他否定了福楼拜追求文学独立的主张。由之,萨特指责福楼拜的“绝对风格”是一种将多样性统一于一种风格的观念,这样的文学把自身作为对象,抛弃了一部分“缺乏修养”的读者,并导致作品失去其多样性。
对此,相较于萨特要求介入当下的时代,朗西埃则更具有历时性的眼光,更为宽容地期待一种“未来的读者”。朗西埃通过“悬置”(suspend)的思想暂时绕过了福楼拜的阶级立场和政治主张,主要关注福楼拜的写作带来了什么。由此朗西埃解决了萨特所批评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问题,认为福楼拜的“绝对风格”实际上区别于完全无为的纯艺术者。朗西埃与萨特一样坚持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过朗西埃的理论主张是“艺术的审美体制”,他的“审美体制”本身就突出了“美学”自身的政治性,因此他的理论也就不需要像萨特一样一定要具体地介入了,所以福楼拜越是追求纯艺术,他的作品越具有政治性。值得讨论的是,萨特虽然也曾想象过“无阶级”的作者和“无阶级”的读者,这样作者面对的读者群就是处于世界中的人,不再有“阴性的”“海水的”部分,作者和读者也就真正重合了,从而也就实现了作者的超越性。可是他在表达这一主张的时候,又反对形而上的写法,这个“无阶级”的作者只应该也只能与同时代的人一起历险了。在他眼中,福楼拜想要用“绝对风格”获取绝对眼光从而有效地把握整个写作世界的做法,是脱离人群的做法,这就与萨特的想法相抵牾。萨特始终无法搁置福楼拜的阶级身份,而朗西埃的“暂缓”行为则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萨特“无阶级”的理想。朗西埃还更进一步,将“无阶级”的读者设想为更为普遍的、更被忽视的“无分者”。即便福楼拜保持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福楼拜的作品却恰巧置入了无数的不透明事物,在朗西埃感性分割的“微观介入”的思想指引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不透明事物是可以被感知的,这一点与后期萨特的“ 整体介入”有一定的相似性。
所以对福楼拜“为艺术而艺术”的不同态度,也进一步表明了萨特和朗西埃不同的历史观。萨特认为文学始终具有意识形态,批评福楼拜不是为大众写作,福楼拜的“绝对风格”体现出的美学追求仍然是一种观念性的美学。资产阶级崇拜无用的艺术,萨特批评那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作家对于下层仅限于想象而没有亲自去体会,他们的写作只服务于消费性的“美”而不需与读者相沟通。萨特认为福楼拜把资产者的定义仅仅局限在思想上、观念上、道德上,从而使资产者在“克服”了自己的思想问题、为这些问题找到冠冕堂皇借口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剥削无产者。福楼拜还从外部观察人,这也会导致读者也从外部观察人、以绝对真空的观点去看人。所以萨特认为,福楼拜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积聚就是为了消费的那一瞬间,一种对瞬间死亡之“美”的消费,而这种浪费的瞬间适合于王公大臣们的贵族游戏,下层人们没有等待过那么久的时间只为一个瞬间的消费。萨特过分相信主体的决定作用,坚持作者应该处于自身时代之内、作者面对的读者群(倘若有读者群的话)应该是自己时代的读者,他因此批判福楼拜的注视而不行动,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是存在与做的文学,是情境之中的文学。这样的文学由于在情境之中所以会不断地提问,迫使读者不得不与作者一同处于这个情境之中。萨特的文学观忽略了作品本身的历史流动性,比如对于福楼拜和他的作品来说,无论在萨特眼里福楼拜的思想多么不介入,然而在后世的流动中福楼拜并不能控制自己作品在其他时代产生的意义,也无法预料这些作品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例如在朗西埃在对工人档案的研究中曾发现,一名工人在繁忙的工作日结束后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抓紧时间休息以恢复体力,而是利用周末的时光进行审美活动和创作活动。朗西埃将“智力”视为一种实物,而“书”(livre)正是智力的凝结,人与书的相遇就是读者的智力与作者的智力的相遇。而在生活中,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兼具虚构和真实的人,每个人都是经由他人的话语塑造而成,我们都在阅读和表达,所以作为“智力”之言语的流动对人的主体性的形成至关重要 [7]215。在《无知的教师》中,教师雅科托“只让学生们的智力去对抗书中的智力”[8]17,这样学者和教师的职能就分开了,学习的“智力”与“意志”也就分开了。书是双方智力共同的载体,而书中的智力是可流通之物,学生和教师的平等的智力关联于此中实现。
对朗西埃来说,“书”能够实现各种感官经验的自由组合,其中不存在统一的秩序和规则,柏拉图式的合理秩序也在书写中被打破。由此,内部的书写具有混乱无序的特征,外部的书写具有无差别的流动性,所以书写是逻各斯的不规则分配,书写也就是感知的特殊分享。书写集中起来的感知并非“哲人王”安排的既定秩序的感知,而是作者随机的、不可控的感知,书写之中包含对“ethos”的重新定义,这种定义自然不会严格遵守现存的秩序规定或日常习俗,于是书写重新分配了被规定的“做”“存在”和“说”的和谐秩序。书写通过对个体“ethos”的影响进而影响整体的公共礼法,作为单独音符的公民脱离共同体的和谐乐曲(air),个体重新获得个体的节奏,公民不必再遵守哲人王所定下的道德标准。“书”既扰乱了公民的个人日常生活事务,也影响了公民的个人思想品性,同时“书”还潜在地挑衅了集体生活法律,可以说,“书”尽管是一种沉默的、孤儿的喑哑之物,但是书对统治秩序的侵扰是釜底抽薪式的。所以,朗西埃将“书”抬到了很高的位置上,“书”就是流动的感性,是任何人都可以接触、都可以写作的无主言语(parole)。书中的言语可以与任何人偶然相遇并发生重要的事件,如“僭越”阅读报纸和小说的艾玛、在书桌上通过书本进行实验的布瓦尔和佩库歇,而这些书本本身也将成为其他人可以阅读的“言语”以及“智力”本身,而这些事物,也正是萨特所质疑的惰性事物。
三、知识分子的傲慢:朗西埃对萨特的“哲人王”批判
萨特认为部分作家对资产阶级丑闻的揭露实际上正中资产阶级下怀,资产阶级对此无视甚至纵容。这样的作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谋,他们只是以揭露为任务,他们是反抗者而不是革命者,他们需要资产阶级,从而使他们的虚伪的反对意见站得住脚,他们刻意使自己显得与主流格格不入,但暗中却将不满和反抗、将所有否定性力量都收集进消费美学中并最终一同消费掉,这种反抗、这种唯美主义因此是虚妄的。这“助纣为虐”的反抗对资产阶级来说更好,因为这些力量一旦不消费掉而真正释放出来,便为被压迫阶级服务,那么造成的后果将是不可设想的。朗西埃正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这些力量释放了出来,这些力量不产生于萨特所担忧的消费掉的“焰火”上,而将产生自萨特认为不适宜的工人读者的力量。
萨特的文学观就是他哲学观的体现,在朗西埃看来他工具化读者的行为与他工具化工人的逻辑如出一辙。朗西埃指责萨特与试图建立由哲人王统治的城邦的柏拉图没有区别:柏拉图划分的城邦要求工匠只能做鞋,而不能脱离自己的身份,萨特的工人也无暇亦无力观看周边,只能埋头苦干。工人是疲惫的,工人的身体也是无力的身体。朗西埃认为,某些如萨特一般的知识分子持续将自己视为积极的,而一味地消极化工人。萨特将其自由观念阐释为政党的连续性,而处于情境之中的自由需要不断“应时”地筹谋,在此期间政党将被连续创造,政党将连续保持一种独立性。作为哲学家的萨特为自身找到一种看似合适的存在理由:知识分子自认为占有较高的地势,于是规定了处于最弱势位置的无分者们的目光;依据他所看到的无产阶级的目光,知识分子们作出判断并予以阐释,在这个过程中萨特式知识分子被形容为是“进步的”。简言之,左翼知识分子通过理论阐释创造了“弱势”的无产者地位,哲人站在墙的中间,看见工人正在两侧劳动,而他们无暇他顾、不懂得欣赏风景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这就是朗西埃所讽刺的“哲人王”傲慢。
朗西埃指出,在萨特看来政治行动的基础就是“人的异化—物和物的异化—人”[8]221。他的辩证法需要确切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质构成人的意义,人将自己解体、转化为无机物的形式从而对物产生作用。在这个辩证阐释的过程中,有人将自己独立出来、放在人和物质之外,这个人就是“哲人王”,即萨特自己。尽管萨特反对他者对其他主体的客观化凝视,但他还是在度假时通过对花园和马路的凝视确认了园丁与养路工人的主体身份,进而完成了自己的哲人身份。二者之间有一面墙,他们无法成为彼此的他者,却被“哲人王”这个他者凝视而不自知。朗西埃认为,萨特无意于消除这面墙从而实现两位工人的交互,他反而在加固这面墙。两者的相遇对朗西埃来说至关重要:同样的“工人”身份和不同的职业,他们将会在短暂的相遇中构成一个歧义的共同体。然而萨特拒绝了两个个体之间可能的黏性,因为两者一旦相遇产生朗西埃所设想的含混情况,那么方向将变得不那么明确。“哲人王”需要钢筋和混凝土使劳动者保持他们的孤寂状态,劳动者只能同死物(花园的泥土、马路还有分隔两人的墙)进行交换,实现萨特的明晰的纯粹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朗西埃还强调,即便两人将来在车间相遇,还会有第三个物质性他者出现,即一种“工时测量员”(在当今时代该职业越来越非人化),以及他所代表的规章制度,工人由此被纯粹分隔在物质性量化体系中。
常年工人档案资料的研究使朗西埃确信,工人就是拥有自主意识的“人”,工人在工作时并不会“全心全意”地扑在机器上,他们的目光和手臂并非是永远相统一的,他也会在工作中走神、会思考一些能够令他放松的事情。因此朗西埃指出,工人会遗忘乃至拒斥自己的工人身份。萨特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指出冶金女工在工作中也存在性幻想,但是萨特将之归于机器,“是机器本身在幻想着抚摸”[9]383。朗西埃指责这种辩证法太过机械,只是“辩证法的摹仿物”[8]226,机器使劳动即随之产生的一切都定型,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变得虚伪,萨特被异化的自由终究是某种无法逃离的永恒定型,故而萨特晚年从福楼拜的反抗中体会到除了一丝“殉道”的悲悯。他划定了人与物质的关系,又在他的哲人的窗前洞察了城市的运转规律,把集体体认为“无机物客体的外在性统一”[8]229,他攫取了哲人所拥有的“综合的权力”但剥夺了工人的这种权力。朗西埃特别指出,作为哲人王的萨特在进行这种工作总结时,他的目光无疑凝视着无机的社会和城市,在工作的窗台“自由”地思考,而在他眼中的工人却没有资格进行这样的思考,这无疑是矛盾的。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朗西埃认为,萨特的美学最终走向一种寂静主义。萨特固然拒绝全然充斥技术和机器的世界,但他确信普遍真理形成于人与物的本真交互之中。朗西埃认为萨特转化了康德的共感(sens commun),无关乎人的工人、哲学家还是艺术家身份,创作主体被视作是一种介质,通过创作主体的手、眼以及身体其他部分的协调综合劳动的诸因素(也包括萨特的读者和作者)被团结在一起,由此,创作者成为一个半人半物质化的介质,身体的协调劳动保证了多方的肉体在场,其前提就是手、眼的劳动必须一致。而“‘成为物质’,这是圣·安东尼·福楼拜的终极愿望”[8]255,福楼拜通过“绝对风格”消泯形式混淆物质,这也就解释了何以萨特会对福楼拜持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态度。
结语
从萨特的建墙逻辑来看,朗西埃认为萨特所谓的“情境中的自由”是极其吝啬的,他并不能接受工人的身体在劳动中享有的任何可能的自由,一旦处于劳动之中,工人的身体就是持续受到物质的捆缚,物质应该沾有人的气息、人也应该在劳动之中与切实的物紧密相连。因此萨特认为,福楼拜的写作是与物的极致纠缠,起先他认为福楼拜与物没有发生关系是匪夷所思的,后期萨特则认为福楼拜成为物一般的人,福楼拜的家庭因素和他从小对尸体的接触使他变成一个如物一般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能力以整体的方式介入充满“物”的文学世界。然而在这一点上朗西埃亦给予了萨特猛烈的抨击,朗西埃认为福楼拜是通过自己的写作将自己的思想化成微粒,黏附在了具体的事物上。朗西埃受到席勒影响,重新解释了席勒的“质朴文学”与“多情文学”,在席勒思想中紧张对立的物质与形式被朗西埃改写成紧密结合的形式,甚至某种意义上,他的“感性配享”就是携带着某种思想形式的感性微粒,所以在福楼拜的“封闭”的文学世界中,实际上充满了随时可以涉足的细小微尘,那些荒漠中的石子都是读者可以发挥想象力的地方,也是被凝视者对一切“教师”(包括哲人王、萨特式作者的教导者)的夺权。
注释:
① 关于“位置意识”,施康强解释为:“与萨特曾师事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认为,任何意识都是对于某物的意识,任何意识都不是一个超越的对象所占的位置。如我们意识到一张桌子,桌子本身并不在意识里面,它在空间里面。因此意识乃是对世界的‘ 位置意识’(con-science positionnelle)。”(参见让-保尔·萨特《什么是文学?》引自《萨特文集7·文论卷》,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136页译者注)
② 萨特原话为:“从我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路上有一个修路工人,花园里有一位园丁在工作。在他们俩之间有一道墙,顶端插满碎玻璃片,保护园丁在工作的那块地方的资产阶级财产。因此,他们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在场: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谁也不屑费劲去好奇另一边是否有什么人。这时,我却可以从隐蔽处看见他们……”(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37页)
③ 法语中“partage”既有分配又有分享之意,且朗西埃思想中存在某种观众主动参与而获得感性之分享的含义,因此本文采用台湾学者杨成瀚、关秀惠的译法。
参考文献:
[1] 居斯塔夫·福楼拜.福楼拜小说全集·下[M].刘益庾,刘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 居斯塔夫·福楼拜. 福楼拜文学书简[M]. 丁世中,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2.
[3] 克里斯汀·达伊格尔. 导读萨特[M]. 傅俊宁,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
[4] 让-保尔·萨特. 什么是文学?[M]//萨特文集7·文论卷. 施康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 李健吾. 福楼拜评传[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6] FLYNN T R. The Role of the Image in Sartre’s Aesthetic[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75, 33(4):431-442.
[7] FREEDGOOD E. The Novelist and Her Poo[J].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1975, 33(4): 431-442.
[8] 雅克·朗西埃. 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M]. 赵子龙,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
[9] 让-保罗·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上[M]. 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王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