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二题
(一)
我去图书馆,常看的主要就那么几个书架。架上的书或CD哪天多一或少一,差不多都心中有数。这些可爱的书和CD散落出去,无声地改变着一些人的生活,也可以想成,是改变着这个世界。我眼睁睁看着书架上的东西在变,好像凝视着大千世界的缓缓流转。
很久以前我借过一张“小双张”,马里纳指挥田野里的圣马丁室内乐团演奏巴赫《赋格的艺术》和《音乐的奉献》,听了惊艳不已,于是不停续借,续借,到不能续为止,只好还掉,然后梦想再借回来,却再不得见。我在计算机里的检索系统前发愣,想要不要“申请”这张CD呢?只要花五毛钱,便可向图书馆提出要求,这时手中有这CD的人就不能再续,到时必须还。
可是,还是不要打扰那个听巴赫的朋友吧。你且好好听,做白日梦,就像我。既然我们都痴情若此,让我跟看不见的你握握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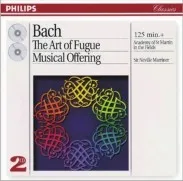
就这样,我每次去,都傻里傻气地在 CD堆里翻,巴望再次获得它,却不肯提出“保留”要求。就这样,几个月后,它才“顺其自然”地回到我手中。
《音乐的奉献》我花了好大力气才进入。通常,我在计算机的音箱里听。一会儿不理计算机,它就悄然进入“睡眠”了,此时屏幕沙地轻响,屋里黯然,而音乐依旧。有一天,在这“沙”的一声里,光滑的长笛勾出的曲折主题中蓦然凸现凄凉和安慰。一段段对位中,好像有欢愉,有痛楚。想起巴赫在那首著名的“吸烟诗”里倾诉过哀伤。可他其实还是安然的,心底近乎“仁者无敌”的自信。羽管键琴上,主题沿着琶音松弛地跳到最低音站稳,或者,它充当伴奏,用节奏轻轻抽打音乐滴溜溜前行。小提琴绕着长笛牵手,“絮乱丝繁天亦迷”,撩拨得人发软,心和眼睛却格外清醒。
《赋格的艺术》我一直很熟悉,主要是钢琴版本。而室内乐团演奏得太好了,好得让人忘了古尔德手下的钢琴和管风琴。想想这样的效果:哑然的地平线上,忽然升起来柔长的提琴声,像温润的手指轻轻托起晨曦。渐渐,鼓角共起,歌吹沸天,各种乐器舞之蹈之以后,薰歇烬灭,光沉响绝。天啊!也许巴赫真是在一心一意展现“赋格的艺术”,别无他想。他把自己淹没在一门细巧的手艺里,直到炉火纯青,直到没有自我。而他的纯粹让我们几乎不忍说出,这部作品听来其实如此多情,令人欲仙欲死。
这张CD现在还与我相伴。有一天它将悄悄走回图书馆的架子,走到另一个人手上。每当它被一个人听过,这个世界就会被掀动一点点。我真这么想。
(二)
你听没听过他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好的音乐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会“生长”。也许这是种迷信。真相是有些音乐两百年前就是这样子,变化的是耳朵。不过,既然音乐中有些无法用道理解释的东西,也许你会同意我用“生命”这么奇妙神秘的现象暂且类比。
一些音乐是水藻般的生物,飘着柔韧的触角,在一个你不可知的海洋里自生自灭。你知道它的存在,但不必牵挂于怀。偶尔,你突然瞥过去,从一个幽暗的角度见它已经形容大异。
马友友大约不会反对这种想法。他在一张名叫《巴赫花园》的DVD中肯定地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巴赫花园,因为他的音乐其实是在不停生长变化,如同大自然。”巴赫花园是以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第一首为主题建造的小小园区,园中之园各自以萨拉班德、库朗特等组曲中的“小标题”命名。它类似一个充满诗意的孩子气的异想天开,可是,我们在DVD上看到,1997年,这个花园当真在波士顿动工了。画面里,花园设计者和市政官员们一本正经地讨论。在音乐里,镜头慢慢移向了艳丽的花朵,还有一脸甜蜜笑容的小女孩。马友友坐在里面,以他平素的激情拉琴。

我的脑子里轰的一下。还是在国内的时候,我听着卡萨尔斯凝重的琴声,死盯着乐谱出神。我花了一个寒假辛苦地听,记住了旋律,偶尔也感动于那朴拙之音,可还是赶不走“枯燥”“单调”的印象。后来生活环境变了,我“趁机”遗忘了它。
而现在猛然发现它已经生长得美艳而温存。还有,它也常常很雄壮,很慷慨。“华丽”和“朴素”在这里汇到一起成为高贵。我坚强的时候它含着神性般的浑融安详,我脆弱的时候它是最柔软的人间之手。我把马友友、罗斯特罗波维奇、卡萨尔斯的录音找来,在屋里听,开车听。那浑厚、丰盈的琴声鼓胀成温风包住战栗的我,把我轻轻拢到他乡。曲中隐忍的激昂,宽广的叹息,在氤氲的想象里就着高高低低的烛光闪烁,而一把左突右奔的琴弓在眼前遒劲地勾画出孤独而挺拔的生命。大提琴组曲,我的“水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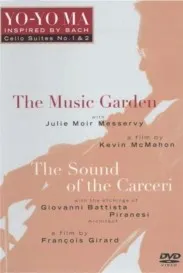
马友友为六首组曲录了三张DVD,以各种形式表达了他对这些音乐的理解和想象,其中包括舞蹈、花样滑冰甚至带有情节的短剧。我比较同意和欣赏的,除了“巴赫花园”,还有第三组曲的舞蹈和第五组曲的日本歌舞伎表演。第三组曲的舞蹈名为《走下楼梯》,从开头的下行琶音起,一群各肤色的男女从楼梯欣然地涌下,倒卧,聚散。其中最有趣的是《布列舞曲》,他们以手掌动作牵引音乐,看上去既玄妙又天真。第五组曲中,舞者阪东是个清秀的日本男子,扮演女人,举手投足柔媚如水,让人想起梅兰芳。大概这种怪诞不经的组合要招致非议,而且,它显得太“即兴”了些,舞者与琴声的配合不够精准。
从童年启蒙至名满天下一直拉这部作品的马友友,目击过这部作品生长的无数个瞬间,观察过它的枝干和花朵的各种表情,他有太多的记忆和幻想要倾诉。即使我们不同意他的解释,可是在这生生不息的音乐面前,我们应该同情他的“情动于中,不能自已”。

(本文原载于《音乐爱好者》200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