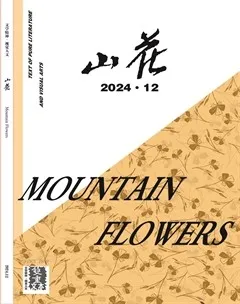两地书
阳明先生:
当我写下此笔的时候,我们已相隔整整四百九十五年了。
先生当然不可能知道我。这么漫长的时间,足以让很多的事情发生又消失掉了。死亡是经常性的,最关键的是,死亡之后的遗忘,更让人绝望,那遗忘充满了否定性。虽然,绝大多数的事物最终都将成为沙砾或野地里的狗尾巴草,但先生是极少数可以在肉身已去的情况下做到思想不灭的。
很多人拜于先生的门下。他们好像不只是为了求得学问,而是求学的路上,往往要走很长的暗路,但因为有了先生的存在,他们的心里便有了明炬。我和先生的缘分,其实在我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已是命中注定了。谁能够料到我会在一个叫“左营背”的地方出生呢?在多数人的眼中,这个地方,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它只是城乡接合部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居民区。生活在其中的人,往往比单纯意义上的城里人或者乡下人多了一重日常空间。他们的生活通常具有一种延展性,经常是兼顾两份工作,这里的一天,看起来就像是别处的两天。当然我对于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兴趣。生活的五光十色会让我觉得琐碎烦人,它们充满了各种假象,事情过后,都将回归于一个地名。地名才是我们有能力把握的一点。
左营背,可想而知,也便是左营房的后背。我在无意之中,看到过明朝天启年间修撰的《赣州府志》,地图上有一点被标注为大校场,校场也便是旧时军士操演或比武的场所。直觉告诉我,地图上的大校场距离我家的位置并不会太远。但这似乎也并不能说明什么——难道有了大校场,就一定能够遇见先生吗?先生的天地宽阔,京师、钱塘、绍兴、舟山,以及山东、安徽、贵州龙场……哪里没有留下过先生的足迹?
但我想,先生必定是来过左营背的。正德十二年(1517年),先生就站在这儿,靴底必定是沾着这里的泥土的。那时,先生胡须如刺,像一片茂密的森林,但森林早早地就已经呈花白色了。距离龙场的那段至暗时刻,一眨眼就过去了九年。不过时过境迁,当年处心积虑设法陷害先生的那些小人此时都已经命丧黄泉了。他们的德行不足以支撑他们活得太久,阻碍先生精进的负面能量都一点点退去了。而先生的心境也与从前大不一样了。经兵部尚书王琼的特荐,头一年,先生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这年,先生四十五岁。作为一个男人,你和妻子诸氏完婚至今,竟不曾让心爱之人怀孕,这让你感到沮丧,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呢?你来不及想。十万火急,这是赣州,闽粤湘赣往来的要津。这里的土地,除了盛产茶与采茶戏,也盛产流民与匪盗。而这些匪盗的成分往往又极为复杂,他们白天耕种,貌似良民,晚上却遁山为贼,甚至不少当地的里甲编户和土著也混在其中。加之此地又多是高山大谷,茂林荆棘,历任的地方官们对于清剿盗贼一事都颇感到头疼。
但这一次,你必须将他们给扳倒。时间一晃,你就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四十五载,你握笔的食指,胼胝厚了,因为舞剑,手心的胼胝也厚了。这些发黄的老茧,让你逐渐成了一个骚人,但一个骚人的外壳又岂能够装下你呢?现在,你不仅不再是早年耽溺佛老、求仙问道的那个王守仁,便连后来矢志倡明儒家WeXy6qE20HY0gWZ3hkZXKd6XJ471PryaL+wkbEHFa6w=圣学的阳明也不完全是了。你可是在龙场说出过“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样的惊世之语的。你说出那一等话的时候,整个人都好像被烈火淬炼了一遍。龙场的生活环境实在是太艰苦了,南方的溽热潮湿让你感觉到非常压抑,你四肢乏力,头脑昏沉。你被命运彻底地困住了,但外部环境对自己越是表现得不利,生命的内在能量就越充足。心外无物,说的并不是心外真的无物,而是心外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心是唯一能够被抓住的。一个有能力把握自己的人还有什么事物把握不了呢?你生命里的贵人王琼举荐你来南赣剿匪,其实看重的,不仅是你心里的那一股硬气与光明,也是你心里的仁慈与智慧。
向来被遏制、被封锁的内心一旦找到了释放的空间,人生便有了开阔的舞台。你锋利的剑终于有机会从剑鞘中抽出了。抬眼望,心中的光芒和火焰也一并抛向了天空。你终于获得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外部世界。你不仅要让那些山中贼感到惧怕,最关键的,是要让他们也能够“致良知”。所谓的良知,最简单的解释,便是分辨善恶的能力,一个真正的文明人必然是有着强烈的羞耻感的。在龙场那个漆黑的石洞中,困顿中所有的悟,最终都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与现实问题。先生是一个明白人,悟多少的道,关键还在于有用啊。这世间最怕的,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学富五车,终于无用,岂不悲乎?现在,先生终于可以用胸中的“自足”去收拾、教化那些贼匪了。我知道,先生其实也并不想把他们杀死。从根本上说,先生是一个儒者,始终讲求的,是仁义,是道德!对于一个传统儒家的人而言,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才是先生安顿生命的基本的方向。“悟”的目的,最终也便是为了抵达这个方向。
在南赣,先生主要的精力并没有花在平定乱事上,虽然你也下过狠心,擒斩了一批贼匪,但目的却并不在此。把贼子的头颅从脖子上拧下来有什么难的呢?要把一颗真正的仁义之心嵌入他们的身体才叫难呢。你所做的一些工作,包括确立南赣乡约、办社学、兴修书院,哪一件不起着教化人心的作用?你明白,所谓的贼,本质上也都是民啊。你像一个能撬动巨石的壮士,要把贼子已然偏离的思想扶正,真正的贼是在人的心里,在那个滚烫又柔软的部位,那才是真正的贼府啊。“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南赣,先生在写信给弟子薛侃之时,此行字必定是用朱笔写就的,那是心之颜色,是用心调成的黏稠的墨汁啊!
往事已矣,我从出生到十二岁都居住在左营背,后来左营背因为拆迁离我而去。我在很多份的简历中都会特别地补上一句,我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事实上,这个地名已不复存在了。城市日新月异地发展,曾经存在过的很多地址都找不到了。现实中的左营背我是永远回不去了,可是许多东西当弄丢以后,往往会成为一种更加深刻的记忆——先生曾经点兵用过的大校场虽杳不可寻,但我一直想象着它的存在。校场的功能远远不在于军士操演与比武之用,它也是一个出发地,浩浩荡荡的大军就是从这里奔赴战场的。旌旗蔽空,横槊赋诗,先生当年龙场悟出的那些道理,而今都将派上用场,日积月累的思想资源在实践中一旦证实了它的价值,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地就会被人奉为“绝学”了。初寒,不尽。
后世某某:
当你看见此书之时,我早已不在人间了。
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了。我对于这朽腐不能说欢喜,但也不至于难过。死亡是再寻常不过的。谁能够阻止死亡的发生呢?有生自然便会有死,有死亡的人生才堪称完美。命运既然将我安排到龙场这个地方,我便欣然接受。其实我早已经死过几回了——谁让我那么喜欢说真话呢,一个喜欢说真话的人所走的路注定要比普通人曲折多了。廷杖的滋味真让人觉得生不如死啊。这种酷刑也不知是哪个“聪明人”发明出来的,首先那杖的材料就非常考究,通常用坚硬的栗木制成,击人的一端削成槌状,外包有铁皮,铁皮上还有倒钩,如没有打点行刑人,往往一杖下去,再顺势一扯,尖利的倒钩就会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血肉之躯哪经得起这般折磨。很多人没等到行刑结束,就已经一命呜呼了。所幸,打我的那个行刑人是个新来的,打得太不用心了,我才因此逃过了一劫。伤口愈合之后的疤痕,长成了莲花的形状。
对于死亡,我并无任何的恐惧。我说“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所焦虑的并不是生死本身,我的胸中始终是一种“洒洒”的状态,只不过有些疑惑需要用更漫长的生才能参悟得透。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被思想的光明所照耀的死亡平静得近乎安详的水面。孔子最放不下的,是斯文与斯道,这是比物质和肉体都更加重要的事物。
现在,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什么依靠与着落都不复存在了。可是除了呼吸和心跳以外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呢?夜晚的山洞就像是一口幽深的古井,石头上水滴的声音充满了我的意念。此时我的头脑是另一个更加巨大的山洞,比白天要更加敏感、清醒。我睡不着,只好端坐沉默,空气与微风的荡漾都能够被我的意念捕捉。我设法让心彻底地静下来,回到“一”的状态。“一”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水平线,树叶落下来,水落下来,云落下来,倒影落下来,激动与悲伤的心情落下来,诗落下来,万事万物纷纷地落下来,它们最终都被这条清心寡欲的水平线稳稳地接住了,而私欲和障碍都被层层剥落了,心性的本体就像海底的红轮开始转动。所谓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其实是在意念彻底清空之后获得的另一种更加真实的“有”与存在。
每当我想起孟子说过的“万物皆备于我”,就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候格过的那一丛竹子,那些竹子现在从我的胸中旁逸出来,风姿绰约。竹子岂是用来格的?真正的竹子都青绿在人的胸中。而龙场周围的那些溪水与丘陵都可能成为我胸中的丘壑。
思想之间,饥肠已经有辘辘之声了。我得赶紧去淘一点米,毕竟“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谋食”终究是为了“谋道”。守仁,善自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