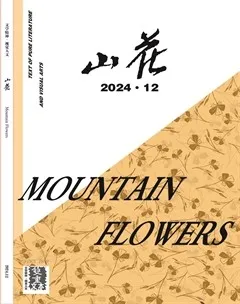勿作“枝叶花实”之悬想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所求,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去设定并努力实现自己的各类生活目标,希望自己的人生不断有所成就;但实际的人生中,不如意之事却是十常八九,很多时候设立的大小目标都会付诸阙如,于是乎人常常会产生失意的怅然之情、怨尤之念。如何应对这一常见的人生处境?王阳明“勿作‘枝叶花实’之悬想”的观念,便是劝诫人们在生活中立乎其大,不要孜孜于具体的目标成就、纠结于一时一地的所得所获,而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切实地循着正道而行,自然能够度过光明其心、充实其生的人生。这一观点,对于人们应对生活中阶段性的挫折、失落,树立圆融的人生德业观,颇有启发意义。
王阳明曾与门人讨论树立人生志业与实现志业功夫之间的关系,他说:“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果?”(《传习录》上)人处世上,为学、做事以实现成己、成人的志向与目标,这对于人生来说合理合情、无可厚非,好比种植一棵树,总是希望幼苗能长成枝繁叶茂、花果丰盈的参天大树,未有种树而望其夭折的。如同种树先要培根一样,王阳明强调为学、做事首要在于立其根本,“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传习录》上)。本原既固,还要有所坚持,如孟子所言,“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离娄下》)。有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水流在填满一个坑洼后才会继续向前流去,只要坚持用功填满生命历程上的每个坑洼,最终便能“放乎四海”。为学、做事也要“盈科而进”,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如何汪洋恣肆,而要先认真努力地把眼前的小坑洼填满。因此,在人生的进阶历程中,不要老是“悬想”如何去享受成就功业时的喜悦,就像种树时不去憧憬枝叶华实的未来景象一样,而应当只管循序渐进地做当下的栽培灌溉,久久为功,自然会在成人成事的道路上日益精进。对于王阳明来说,在生活中不问收获的着实用功才是修习正途,汲汲于小成而放弃用功则是“魔道”,“人若着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传习录》下)。如果人能够着实地在致良知上用功,关注自家德性,不在乎别人对自己无所成就的轻视,那么因一时无所成所招致的毁谤、欺慢也会变成自己的进德之资,反过来促进自己德性的养成和完善;反过来,如果人不能着实地用功,那些外来的毁谤、欺慢就会成为其心魔并将其累倒、摧毁,进而怀疑并丧失自己的德性志向。质言之,离开了切实的用功,只作悬想,终将一事无成。
对“枝叶花实”的悬想与人生中的速成之念常常是相伴而生的。“致良知”是阳明心学中最为重要的事业,但王阳明不主张在“致良知”上脱离现实而实现速成,“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传习录》下)。在这里,王阳明强调致良知要随各人能力逐渐成就,一日对良知有所体会就一日贯彻到底,这才是真正的“精一”功夫,不可超出自己的分限与能力,不切实际地追求速成。如同灌溉培育树木,要按照树木的生长境况予以逐渐灌溉,不可一时大水漫灌以求加快生长速度,这样反而会损害树木的生长。一般人可能认为,“致良知”为一蹴而就之事,故而怀有速成之心,生长出“枝叶花实”的悬想,王阳明觉察到了这个偏谬,故而提醒来学弟子,希望他们要随着各人的力量气魄来致良知,要将当下所领会的道理贯彻到底,切实地落实在应对事务上,不可贪多求快。如果不按照个体能力、分限来推致良知,反而会损害人们在良知上的功夫,阻碍人们德性的成就。就像有人去学孔子,只看孔子的气魄成就,而不看孔子的着实用功,也不考虑自己的能力,结果只能闹笑话,“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从那心上来。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从枝叶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学者学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却倒做了”(《传习录》下)。他认为孔子有着料理帝王事业的气魄,但孔子不是要从枝节、形式上学做帝王,而是从扩充心体上来涵括天地、包揽宇内,扩充心体才是圣贤事业的根基。这正如无论大树生长多少枝叶,都是从树根上培养得来的,固本培根,枝叶自然繁茂。稍微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不是从枝叶上求得树根,而是从树根上求得枝叶。由此,王阳明批评道,很多人学孔子,不是学孔子在心上用功,而是在外在形式上学孔子,甚至以“圣贤”的姿态面对世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当时很多道学先生在言行姿态上以圣贤自居,十分可笑,王阳明正是对此有感而发。王阳明反对人们急于求成,不只是功业上不能求速成,即使是德性上的急切也是值得警惕的。在儒家话语系统里,急于求成就是所谓“助长”。“助长”意味着在功夫上人主观地刻意求速、求全或伪饰,因此,王阳明特别告诫门人要克服“助长”心态,“诸君功夫,最不可‘助长’”(《传习录》下)。上智之人极少,为学之人不可能不经过循序渐进的功夫就能领略圣人之道,在为学的过程中有所起伏、时有进退都是正常的。有些人一段时间功夫精进,一段时间功夫平平,在功夫平平的时候偏要强行伪装成“没破绽”的样子,这就是“助长”,“助长”的伪饰会将前日精进的功夫一并毁坏。在王阳明看来,这种“助长”是大毛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王阳明告诫道:“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也。今便要责效,却是助长,不成工夫”(《传习录》下)。圣贤事业如果责于一时“枝叶花实”的成效,就可能造成“助长”之憾。
“枝叶花实”的长成伴随着栽培灌溉,人生的德业成就也就在切实的努力之中。对于儒家来说,人生的德业成就是具有“上达”的志向性意味,而日常生活中的不懈努力则体现了“下学”的功夫性意味。王阳明认为,崇高的“志向”就在日常的“功夫”之中,不必追问何处、何时才能实现“上达”,“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传习录》上)。孔子所说的 “下学而上达”,一般指循序渐进的修养功夫,“下学”是指学习具体的日用伦常、知识文化,“上达”是指通达精微的性与天道,下学之途与上达之境有着层次之分,这是普通的理解。而王阳明则认为,闻见、表达、思考的形式是“下学”,而闻见、表达、思考所达到的效果,则是“上达”,二者合而为一,效验就在“工夫”之中。譬如给树木“栽培灌溉”的具体工夫,是“下学”,而树木不断生长、枝繁叶茂,就是“上达”,不可分开。可感知、可言说、可操作的“具体”都是“下学”,而通过感知、言说、操作所能达到的效果,俱是“上达”。王阳明认为,圣人之义,看上去很高深精微,当人们去学习、理解圣人之义的时候,就是“下学”的工夫,当体会了圣人之义并以此提升了自己思想境界的时候,“上达”也就伴随着“下学”完成了,每一处“下学”都正在实现“上达”的效验。因此,王阳明告诫人们不要专门去寻找一个“上达”的工夫,“上达”本应伴随着“下学”的工夫而完成。栽培灌溉的努力,就是“枝叶花实”之效验生发之时,而关于德业成就的“上达”境界也只存在于日复一日的“下学”工夫之中。
勿作“枝叶花实”的悬想,更意味着人们不要纠结于“得”与“不得”,不在患得患失中消耗自己的心神。王阳明指出,“‘发愤忘食’,是圣人之志如此,真无有已时;‘乐以忘忧’,是圣人之道如此,真无有戚时。恐不必云‘得’‘不得’也”(《传习录》下)。孔子自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对此,朱熹诠解为:“未得,则发愤以忘食。已得,则乐之忘忧”(《四书章句集注》),而王阳明则超越了“得”与“不得”来予以阐释,在他看来,“发愤忘食”是圣人之志,故而不会有停息之时;“乐以忘忧”是圣人之道,故而不会有哀戚之色。就此而言,对于人生的修习来说,不必考虑“得与不得”,只是依照本心发愤、忘忧而已。发愤、忘忧是人心之本然,与“得与不得”没有关系。人只要循着人心蕴含的天理去处世接物,现实中的功业气节等“得”与“不得”的情况都“非所与论”,没有必要因之而忧结于心。正是如此,王阳明主张“功业气节”只是依循天理的自然效果,不能将其作为动机和标榜,“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着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传习录》下)。圣贤自然有“功业气节”之事,但是圣贤不将“功业气节”等外在性效用作为自己称名于世的追求,他们在生活中只是循着天理去做,这便是正道。在儒家的叙事传统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孔孟,其人生历程都展现了功业气节,但是他们没有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王阳明少年时所提的“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这一问题,也是说“学圣贤”,而没有将读书登第、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不把“功业”等外在性效用作为目标,不执念于“枝叶花实”之效验,自然就无所谓是否得偿所愿。
树木的“枝叶花实”引人注目,人生有所成就令人羡慕,但总有一无所成的时候,人应该如何应对“一时无所成就而为人非笑”的窘境?王阳明强调人们应该笃志良知、心无旁骛地实地用功,由此便可以度过人生中迷茫与失落时期,“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工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传习录》下)。人的灵根天植、主宰自作,在生活中,要放弃对可见性效用的执念,不要为虚名、浮誉所拘束,不管他人非笑、毁谤,也不纠结于工夫的一时进退,更不作“枝叶花实”的锱铢计较,只管坚韧不拔地履行职责,久久为功,个体的人生自然圆融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