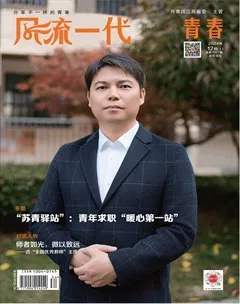中国千年吃蟹简史
先秦两汉:见过的人多,吃过的人少
中国人很早就见过螃蟹,被选进中学教材的《荀子·劝学》中就说“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这是教育我们做人不能浮躁。不过我们见到的螃蟹都是八条腿,《荀子》里却说“六跪”,为什么呢?答案当然就是,抄错了。
比《荀子》稍早的《庄子》,在《秋水篇》中说“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国语》里也有“稻蟹不遗种”的文字,可见春秋战国时期,螃蟹已经是个常见的物种了。不过正如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经常有人说中国人吃螃蟹始于周朝,更有甚者,言之凿凿,说周朝螃蟹已经是御膳了。事实上,整个先秦以至于到了两汉,文献中关于吃蟹的记载是非常少见的。
在《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中说“庖人”这个官职需要负责“祭祀之好羞(馐)”,这个用来祭祀的好馐有什么呢?东汉郑玄的注里说有“青州之蟹胥”,这种产自山东的蟹酱用于祭祀,有没有人吃就不知道了。《汲家周书》里说周成王时,“海阳献蟹”,但成王吃了没有,史无明文。秦代、汉代则几乎没有关于吃螃蟹的记载。总的来说,整个先秦两汉,看见螃蟹的多,亲自动口吃螃蟹的就很少了。
魏晋南北朝:有酒有蟹过一生
魏晋南北朝真是一个浪漫的时代,这个时候人们忽然就开窍了,吃螃蟹的记载层出不穷。最有名的莫过于晋朝名士毕卓。《晋书·毕卓传》中说毕卓一生的愿望:“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一只手端起酒杯,一只手拿着蟹螯,人生之乐,莫过于此,这是多么潇洒的人生。后来宋代苏轼的诗句“万斛船中着美酒,与君一生长拍浮”,用的正是这个典故。
吃螃蟹的风气大概始于南方,所以当时北方甚至有人觉得吃蟹是南方人的特征。《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北魏杨元慎奚落南梁陈庆之说:“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做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这里提到的“唼嗍蟹黄”,真是说出了吃螃蟹的精髓。嗍,就是用唇舌裹食、吮吸。
当时螃蟹的做法非止一端,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对蟹的吃法大谈特谈,有蒸、炸、面拖、酒醉等各种做法,还有用糖和盐腌制的“藏蟹法”。这其实就是后代的糖蟹,贾思勰还特别提到,吃这螃蟹要蘸生姜末和醋。15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吃螃蟹依旧还是用这样的佐料。
糖蟹是当时很受欢迎的一种吃法,隋炀帝很喜欢糖蟹,《清异录》记载:“炀帝幸江都,吴中贡糟蟹、糖蟹。每进御,则上旋洁拭壳面,以金镂龙凤花云贴其上。”就是说隋炀帝到扬州的时候,吴人进贡糟蟹、糖蟹,隋炀帝会亲自擦拭螃蟹的背壳,还要贴上黄金丝制成的龙凤花纹,足见他对这美食的酷爱。
蟹黄包来了,唐代蟹肉美食多
唐宋时期是中国美食史上的一个高峰,螃蟹的吃法也翻出无数花样。糖蟹依旧是受欢迎的做法,隋炀帝之后,唐代的皇帝也很喜欢这种美食。《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到沧州景城郡的贡物,其中就有糖蟹。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提到平原郡的贡品糖蟹通过快递直接送到长安。唐代段公路的《北户录》中专门一条有“糖蟹法”,介绍糖蟹的详细做法,和《齐民要术》中的“藏蟹法”大致相同。
唐代已经有蟹黄包了,刘恂的《岭南表异》中介绍蟹黄,说“蟹壳内有膏如黄酥,加以五味,和壳煿之,食亦有味。赤蟹壳内黄赤膏如鸡鸭子黄,肉白,以和膏,实其壳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饦,珍美可尚”。这里提到两种做法:一种是连壳带蟹黄一起,加上调料煎炒;另一种是把蟹黄蟹肉加上调料,用面粉做成“蟹饦”,后面这个蟹饦已经很像是蟹黄包了。而长安还有人销售蟹黄饆饠,饆饠也叫毕罗,是一种有馅的蒸成的面食,蟹黄饆饠其实完全就是蟹黄包。
宋人养殖螃蟹,还出了两本螃蟹专著
用一个词来形容宋代的吃蟹,那就是“专业”。五代开始,就有了政府安排专门养殖螃蟹的“蟹户”,螃蟹产业开始形成。最能代表专业性的,则是当时出现的两本螃蟹专著,北宋傅肱的《蟹谱》和南宋高似孙的《蟹略》。傅肱是北宋浙江绍兴人,《蟹谱》共两卷,上卷记录螃蟹的各种典故四十二条,下篇则记载其所见所闻的和螃蟹相关的趣事二十四条,书写得非常“雅驯有趣”。高似孙是浙江宁波人,《蟹略》有四卷,卷一有螃蟹传记、螃蟹起源和螃蟹的考察,卷二对各地和各时节的螃蟹进行详细品鉴,卷三特别介绍了螃蟹相关的美食,卷四则介绍螃蟹相关的诗词歌赋等文艺作品。
当时北方能吃螃蟹的,大概还是富贵人家,很多平民从没有见过螃蟹。《梦溪笔谈》里记载了一件趣事,当时很多陕西人从没有见过螃蟹,有个家境好一点的,弄到了一只,但直到这螃蟹变干都没有敢吃,挂在墙上当装饰品。邻居们见了,吓得掉头就跑,以为是妖怪。后来见得多了,慢慢就不怕了,但又觉得这东西可以辟邪。谁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就把这干螃蟹借去挂在门口,居然往往有效。原来不仅人没见过这东西,连鬼也没有见过!
清蒸,明清人的吃蟹之道
明清时代,螃蟹的吃法返璞归真,更多用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清蒸。记载中的各种“蟹会”(螃蟹宴),吃法都和今天类似。
晚明时期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当年的“蟹会”:“煮蟹食之,人六只,恐冷腥,迭番煮之”。还要配上各种美味佳肴,“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瓜以谢橘、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在《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宝钗提议设螃蟹宴,“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肥螃蟹,前儿送了几斤来。现在这里的人,从老太太起连上园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前日姨娘还说要请老太太在园里赏桂花吃螃蟹”,这就有了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一大家子吃螃蟹,也都是清蒸,描写得引人入胜。我每次读到这一回,都不由得垂涎三尺。
在明代以前,吃螃蟹都是用手。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发明了著名的“蟹八件”,有锤、镦、钳、铲、匙、叉、刮、针8种,有垫、敲、劈、叉、剪、夹、剔、盛等多种功能,吃螃蟹一下子变得优雅起来。据说在晚清时候,“蟹八件”还是苏州姑娘们出嫁必备的嫁妆。
“蟹仙”李渔,中国爱蟹第一人
中国古代爱吃螃蟹的名人太多了,比如宋代文豪苏东坡有诗云:“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再比如陆游吃糟蟹,写诗感慨“蟹肥旋擘馋涎堕,酒渌初倾老眼明”。但要论爱蟹第一人,还当数被后人推为“蟹仙”的李渔。
李渔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他对螃蟹堪称痴迷,自称“终生一日皆不能忘之”,家人称他是“以蟹为命”。螃蟹价格贵,他吃的又多,囊中往往因之羞涩,于是乎每年不到螃蟹上市的时节,他就开始早早存钱,准备用来买螃蟹,这笔钱他叫作“买命钱”,他对螃蟹的痴迷可见一斑。
李渔爱吃螃蟹,更会吃螃蟹。他认为最美味的螃蟹,就是简单清蒸,“蒸而熟之,才能不失真味”,并且升华为一种哲学高度,提出“世间好味,利在孤行”——世间的美味,其实以简朴为上,人间至味是清欢。他在《闲情偶寄》里写道:“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体,蒸而熟之,贮以冰盘,列之几上,听客自取而食。”
李渔为了螃蟹,专门在家养了一个丫鬟帮忙做蟹、剥蟹,取名就叫“蟹奴”,他还有专门用来做醉蟹的一整套物资:蟹糟、蟹酒、蟹瓮……这位爱蟹如命的大才子,真正堪称“中国蟹仙”。
(编辑 郑儒凤 zrf911@sina.com,西米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