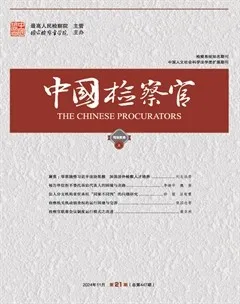网络贩毒规制路径
摘 要:当前,网络贩毒大量滋生,其具有犯罪主体低龄化、行为方式隐蔽化专业化、社会危害性大等特征,原因主要是网络监管力量不足、网络空间贩毒渠道广泛、寄递毒品存在监管盲区。网络贩毒治罪面临客观证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不力、法律适用标准不够统一等难点和困境。新形势下对网络贩毒的规制,应从技术监管与联动监管、证据收集与固定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行业责任与公众参与强化等角度综合进行。
关键词:网络贩毒 寄递毒品 法律适用 全链条打击
随着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及寄递行业不断壮大,利用网络空间进行毒品犯罪活动明显增多,网络贩毒行为大量滋生。贩毒行为人通过快手、抖音、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进行贩毒联络,同时通过邮寄方式寄递毒品,并利用虚拟币进行毒资结算,进一步加剧了当前禁毒形势的复杂化,成为新的治理难点。
一、网络贩毒犯罪案件的特征
网络空间具有联络方便、安全和网上支付简单、快捷等特点,行为人携带毒品、当面交易的接触式贩毒模式已越来越少,利用网络虚拟身份勾连、线上交易毒品的网络贩毒形式已成新常态。2021年4月至2024年上半年,浙江省Y市人民检察院共办理网络贩毒案件36件,涉案人员51人。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犯罪主体低龄化,文化程度偏低
据统计,犯罪主体中95后占比43.1%,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70.5%。具有吸毒劣迹、毒品再犯、累犯、刑事前科等情形占比38.9%。毒品类别由传统毒品逐步转向合成毒品及国家管制的麻醉、精神药品等。由于国家对冰毒、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管控力度逐渐加大,传统毒品流通空间越来越小,含合成大麻素电子烟油、列入国家管制的依托咪酯、复方曲马多等精神、麻醉药品在年轻人中较为盛行,尤其是含合成大麻素电子烟油。贩毒行为人基于行业性质、寻求刺激等原因并通过抖音、快手、百度贴吧等网络贩卖毒品,同时通过邮寄、平台购买方式交易毒品。此外由于监管不力及行业主体责任意识不强,致使含合成大麻素电子烟油、复方曲马多等毒品较容易获得。个别诊所存在贩卖国家管制精神药品情况,如孙某某贩卖毒品案,其利用开设诊所便利,短时间内向多名在娱乐场所工作人员贩卖列入国家管制的复方氨酚曲马多。[1]
(二)行为方式隐蔽化、专业化,犯罪成本低廉
网络贩毒最显著的特点是行为手段专业化、交易方式隐蔽化,致使犯罪成本低廉,打击难度较大。
1.毒品联络信息化,身份更隐蔽。行为人通常使用昵称、假名等注册QQ、陌陌、微信,进入各种聊天群或聊天室,还有行为人利用Telegram(具有阅后即焚功能)进行联络,下家往往并不清楚上家的真实身份,即使案发,仅有网络虚拟名的上家真实身份也很难核实。如袁某贩卖毒品案,其通过Telegram联系上家购买大麻进行贩卖,后通过邮寄方式在全国各地贩卖大麻。由于袁某设置了阅后即焚功能,致使无法查明上家身份情况。
2.对毒品进行伪装。行为人将毒品伪装成“商品”进行交易,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如伪装成衣服、鞋子、茶叶等。如姚某某贩毒案,姚某某利用自己开设的网店,将海洛因伪装成鞋子,通过快递邮寄方式将毒品贩卖给他人。[2]
3.交付方式物流化、虚名化。行为人往往会通过物流寄递方式,利用虚假身份及地址进行毒品交易,以此逃避侦查机关打击。随着网络购物的发展,网络贩毒活动中,毒品常混杂于普通物品进行伪装邮寄、托运,毒品交易从电话联系、直接接头发展到通过微信等通讯媒介或电商平台,采用化名取代毒品真名的方式,快递员上门取货,实现毒品送货上门,形成“人毒分离”“钱货分离”的交易方式,犯罪成本大大降低。此外,毒资支付方式虚拟化,购毒者先行支付货款给第三方,第三方收到货款后通知贩毒行为人发货,贩毒行为人以虚假的发件人地址,通过快递物流将毒品寄送至购毒者指定之地,购毒者验货后通知第三方支付毒资,第三方通过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以比特币形式转化毒资。
(三)社会影响面更广,危害性更大
一方面,互联网缩小了涉毒人员地域差别,铺宽了网络贩毒者的销售面,贩毒行为可以跨越多个省份,甚至不同国家,涉及群体规模也更大。网络勾连、快递交易、虚拟支付,使合成、新型毒品在年轻群体之间的流动性、便捷性大大增加,给侦查机关打击带来极大困难。另一方面,网络贩毒行为往往量小、次多,售卖的部分精神管制类毒品价钱便宜,很容易在普通青少年中以“减肥”“提神”等名目形成欺骗性消费,毒害未成年人。与此同时,不同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诸如“蓝精灵”“小树枝”等化学合成毒品,对大脑神经细胞产生直接的、不可逆的损害,影响人的中枢神经,导致神经中毒反应和精神分裂,吸毒者更容易出现兴奋、狂躁、抑郁、幻觉等精神病症状,从而行为失控,造成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有人利用毒品实施其他犯罪,如王某某等人贩卖毒品案,王某某通过微信向彭某某贩卖冰毒,后通过邮寄方式将冰毒交付给彭某某,彭某某在冰毒中加入艾司唑仑片制成赌博粉,在赌博时引诱他人吸食实施诈骗。[3]
二、网络贩毒高发的原因分析
(一)网络监管力量不足
囿于网络载体形式的错综复杂,网络环境已俨然成“信息海”,公安机关现有的网络监管力量很难实现对微信、QQ、网店等各类网络平台的全方位监管。社交平台运营商以及网络安全执法人员网络监察能力有限,大多数网络贩毒案件发生在一些极为常用的社交平台上,在这些社交平台上有关部门即使增加监管力度及监管人手,也难以避免一些漏网之鱼的存在。网络贩毒采用的隐蔽交易模式不同于传统相对固定场所的人货交易模式,毒品交易不需买卖双方实际接触,这也导致监管主体无所适从。
(二)网络空间贩毒渠道广泛
与传统小范围熟人交易形式不同,网络渠道客户可通过熟人或下家介绍,具有发散效应,很容易发展客户资源。部分网络贩毒行为人贩卖的曲马多等国家管制精神类药品及含合成大麻素电子烟油,批着“正规药品”“上头电子烟”外衣,从非正规渠道大量进货后在网上兜售,在短期内获取巨额利益。此外,随着司法机关近年来持续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导致贩毒分子的线下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转而向线上寻求新的空间。
(三)寄递毒品存在监管盲区
网络贩毒行为多伴随有“快递寄毒”行为,物流渠道已成为网络贩毒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重要一环。因快递收寄验视、实名登记等制度落实不够严格,加之快递业从业人员对毒品甄别能力不强,网络贩毒分子当下惯用的“零包分售”手法很容易伪装过关。有的行为人通过购买电子秤、真空压缩机等设备,将大麻包装好后藏入螺蛳粉中;有的行为人将小袋毒品封袋后,藏匿于鞋盒、衣服中,后通过快递寄出。
三、办理网络贩毒案件的难点与困境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隐蔽性、跨地域性加之寄递的便捷性,为贩毒行为人逃避打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办理网络贩毒案件存在诸多难点、困境。
(一)客观证据收集难度大
囿于网络载体形式的错综复杂,公安机关现有的网络监管力量很难实现对微信、抖音等网络平台的全方位监管。网络贩毒采用的隐蔽交易模式不同于传统的人货交易模式,毒品交易不需买卖双方实际接触。网络贩毒涉及多个环节,行为人通过社交软件、平台进行联络,以虚拟寄递方式邮寄毒品,后通过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等实现毒资转移。交易成功后,贩毒行为人往往会对交易数据进行删除,致使侦查机关不能在第一时间对相关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电子证据进行全面固定、提取。贩毒行为人到案后往往会否认贩毒行为,除言词证据外,无其他客观证据佐证贩毒事实,导致诉讼进程在证据环节遭遇短板,无法有效进行法律惩处。此外,由于技术水平限制及司法规范、办案经验欠缺,也导致客观证据转化存在重重困难。
(二)全链条打击力度欠佳
除客观性证据收集存在难度外,网络贩毒线索来源一般系侦查机关现场抓获、涉案人举报等,被抓获人员大多系层级较低贩毒行为人。由于联络行为、交易方式空间化、虚拟化,导致侦查机关无法或不能及时锁定层级较高上家行为人身份。此外,网络贩毒还伴随贩毒行为人通过视频平台、论坛等发布涉毒信息及通过寄递方式邮寄毒品环节,而对上述问题涉及领域综合治理也存在较大难度,导致对网络贩毒全链条、多方位打击效果不佳。
(三)行为性质认定存在争议
1.管辖权争议较大。网络贩毒上下家关系交叉,犯罪链条、层级复杂多样,同时毒品案件一般会采用技术侦查、特情和控制下交付手段,关联案件较多,分布区域广泛,网络贩毒管辖权争议颇大。实践中存在同一贩毒人员因不同毒品犯罪同时被多地公安机关管辖,也存在不考虑案件关联性,对上下游贩毒行为人强行管辖或并案处理的情况。
2.法律适用标准有待统一。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就是网络代购毒品与贩卖毒品区分,有的地方认为代购毒品认定为贩毒需要牟利,有的地方认为代购毒品仅指购毒人指定上家情形,而贩毒行为人到案后往往会以行为系代购进行辩解。网络贩卖毒品往往伴随邮寄运输毒品,对不以贩卖为目的,同城、短距离邮寄毒品,能否认定为运输毒品存有争议。此外行为人利用虚拟货币平台转移毒资的行为,认定为毒品共犯还是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存在争议。上述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导致相同情形可能出现不同判决,进而影响网络贩毒案件高质效办理。
四、网络贩毒的规制路径
(一)深化技术监管与联动协作
对网络贩毒的监管,要顺应数字化改革的时代潮流,运用“数字赋能”的方法,强化立体监管、联动配合。
1.运用先进科技手段。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境下,要不断提升信息侦查技术水平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通过数据综合分析比对,对网络交流平台及网络店铺等的异常词汇、敏感词汇、异常交易展开甄别追踪,准确定位可疑信息的IP来源地址,获取有用线索。
2.加强多部门合作。充分发挥检察监督作用,通过检察建议、检察白皮书等手段推动公安机关网监部门切实加强与电子政务管理部门、电信、移动等网络运营商及网络购物平台企业的交流合作,加大网络安全有效监管。
3.深化区域侦查协作。网络贩毒犯罪具有跨区域性,仅凭一地侦查机关的力量很难有效打击犯罪分子。检察机关基于办案实际,依托提前介入、案件会商等机制,引导侦查机关在跨区域协作上强化配合,使不断更换落脚点的网络贩毒分子无处遁形。
(二)强化证据收集、固定、甄别能力
1.建立网络贩毒证据全方位固定机制。一方面,提取网络贩毒证据时要注意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辨明证据是否经篡改,必要时建立提取清单。在侦查活动中,应当确保有专门针对电子数据的取证人员,一旦发现了电子数据立即进行提取和固定,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对电子数据加以保护,避免其发生损毁或者丢失,使得电子数据作为证据所应当具有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另一方面,注意收集网络贩毒分子使用的QQ及微信帐号、U盘、邮箱、支付宝、移动终端等载体储存的证据信息,必要时采用数据恢复手段,对上述设备载体上的信息予以恢复取证。同时,要加强网络技术、电子数据提取分析等方面的业务培训,不断提升办案人员对电子数据研判能力。
2.有效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功效。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方式,引导侦查机关积极有效调查取证,对获取的电子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夯实在案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三)进一步完善法律适用标准
1.妥善解决管辖权问题。基于网络贩毒特点、全链条打击需要,建立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贩毒行为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犯罪地,包括犯罪预谋、联络地、毒资筹集地、交易地、运输途径地及毒品生产地、藏匿地、转移地、目的地;居住地,包括户籍所在地、常住地和临时居住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法院可以就跨区域网络贩毒案件管辖进行磋商,明确操作标准。如多个公安机关具有管辖权的,由最先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同时强化网络贩毒信息共享,其他公安机关应当将查明的贩毒事实及时移送有管辖权或最先受理的公安机关。
2.明确法律适用标准。针对代购、居间介绍、寄递运输毒品等实践中法律适用争议较大问题,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以指导性案例形式指导基层实践。检察机关可以联合公安机关、法院就具体罪名认定、法律适用、量刑标准等达成共识。对事前同谋或事中参与的视频平台、寄递行业直接责任人员或实际参与人及利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转移毒资的行为人,认定为贩卖毒品共犯。对事后明知是毒资,利用虚拟货币平台转移毒资的,依法适用洗钱罪等罪名。
(四)深化行业责任与舆论引导
1.明确行业主体防控责任。针对网络交流平台等易成为网络贩毒的载体手段问题,网络交流平台一旦发现可疑群、账号等,及时进行封号等限制处理,挤压贩毒行为线上生存空间。物流行业主管部门和协会督促物流企业升级身份信息核实技术、包裹内容物检查甄别技术,对可疑的人或物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备。对通过夹带等藏毒手段甄别不到位问题,快递物流企业要严格执行开箱验视、快递实名制及X光查验等制度,并定期进行自查。对频繁被毒贩利用管理漏洞寄递毒品的企业,行业监管部门及时给予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暂扣、吊销经营许可证等相应处罚。
2.积极有效开展宣传。根据“谁执法谁普法”,借助“检察开放日”“观摩庭”等活动以案释法,依托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电子烟油”、复方曲马多等毒品的危害,不断提升社会民众的识毒、拒毒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