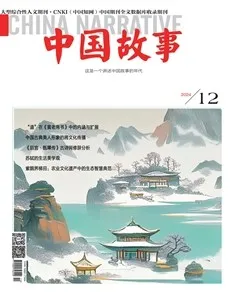晚清民国时期的柏林唐人街与中华饮食记忆
【摘要】自19世纪末起,伴随晚清民国时期兴起的留德热潮,德国首都柏林汇集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中国留德学人为主体的聚居区域。本文在柏林唐人街的历史语境下,以海外中餐作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彼时留德学人在柏林唐人街的历史足迹与中华饮食记忆,观照近代中德两国的文化交往与柏林唐人街的时代变迁。
【关键词】柏林唐人街;留德华人;海外中餐;饮食记忆
在中德两国长达几个世纪的交往历史中,中国人在德国的足迹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从19世纪末起,德国首都柏林聚集了一批近代中国文化与政治领域的风云人物,以康德大街为中心形成的柏林唐人街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的荟萃之地。近年来,随着德国华侨华人历史逐渐进入史学研究与公众视野,关于德国唐人街的历史书写与记忆实践亦呈现出丰富的文化与思想维度。本文以晚清民国时期的柏林唐人街为观照,通过留学或欧游日记、报道、回忆录等史料与文本,探究留德学人在柏林唐人街的历史足迹与中华饮食记忆,以此审视近代中德两国的文化交往与柏林唐人街的兴衰历程。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留德潮
仅就德国柏林一地而言,当地的华人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60年代初,1980年代至今。在此期间,又以第一个阶段的中国留德学生潮蔚为大观。晚清政治家、洋务运动领导者李鸿章1896年出使德国,在柏林拜访铁血宰相俾斯麦时,“斯普雷河畔早已有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自19世纪中期起,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出现了“睁眼看世界”的潮流,开启了近代中国人的海外留学史,可查证的最早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是广东籍人士陈观海。1867年,德国巴陵会(BerlinerMission)选拔并派遣陈观海远赴位于柏林的巴陵会神学院(SeminarderBerlinerMission)学习神学和语言学,从而使其成为史料记载的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德学生。此外,随着清政府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惨败和1900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近代的有识之士都纷纷“毅然走向与传统的决裂,开始新时代的真理追寻之路”。从19世纪末起,晚清的官派赴德乃至赴欧留学活动与洋务派派遣军事留学生密切相关,来到柏林求学的中国知识精英开始真正系统地登上近代中国与德国的历史舞台。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内部形成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自强新政”派,兴办洋务教育,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先后建立了外国语学校、军事学校及技术学校等三类在管理和教学方面都较为“西式”的新型院校,并在容闳的努力下从1872年起开始办理留学教育。1876年李鸿章首次奏准派遣卞长生等武弁七名赴柏林斯邦岛(Spandau)军事学院学习,为期三年。1877年清官员刘锡鸿也来到柏林,在动物公园(Tiergarten)大使馆区首次设立了中国驻德办事处。1881年清政府又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十名来柏林学习。1890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让出使德国柏林的大臣每届酌带两名学生,一边在柏林学习,一边协助大使馆工作……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年年失势也使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救国必须有新人,而新人的培养必须从教育入手。1901年逐渐将留学教学推广至各地,通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分长短期两类,学习重点也从最初的军事方面扩大到农、工、医及格致四科。
近代中国留学生汇聚柏林并非偶然,而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从外部来看,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在经济、科技、社会等方面发展迅猛,20世纪初的经济实力甚至赶上并超越英、法而仅次于美国。德国在数年间从一个分裂软弱的联邦崛起为走向现代化的世界强国,成为近代中国、日本诸国的学习典范。1913年出任驻德公使的颜慧庆这样记录德国首都柏林的情形:“当时的德国经济繁荣,国力鼎盛。从城市的清洁及整齐有序的角度来看柏林,其确是一座优美的城市……在柏林城内,使人驻足流连的是皇宫、博物馆、豪华大饭店、大百货店、剧场、歌剧院以及公园和花园。”作为西方文化重镇之一,德国还拥有丰富浩瀚的艺术文化,学术在世界上亦享有盛誉。德国的大学创办历史可追溯至14世纪,首都汇集了柏林洪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柏林工业大学、夏里特医学院等蜚声世界的高等学府。因此,留学德国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成为其学术文化视野中的一种自然选择。
就内部而言,近代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侮,在国家内外交困、民族风雨飘摇之际,作为精英群体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向西方学习,探索西方的文明之道,尝试中西文化的会通,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中国传统文化推力和德国文化的拉力在此期渐成为一股合力,是形成中国人留学德国热潮的一个重要原因”。彼时的留德热潮离不开清政府洋务派在政治、经济与制度上的扶持。1901年起,清政府颁布政策,提倡、鼓励自费留学,推动了国家的留学教育;1904年颁布了驻德公使吕海寰所拟定的《留学西洋章程》,对留德教育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指导、管理和推动工作。国内对促进留学运动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与支持,加之1905年孙中山因游说革命到访柏林,以及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游历柏林的经历,无不唤起了青年对于留学德国的向往。通过九次游历柏林,康有为在1907年出版的《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对近代德国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赞赏有加,他尤其推崇德国的教育和政治体制,认为中国最应当学习的西方国家并非英美,而是“一切以德为冠”——在他看来,中国最应以德国为现代化的借鉴与镜子,向其学习并派遣留学生至德国。柏林由此逐渐成为中国青年向往和求知深造的新目的地,在这股留德热潮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奔赴德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二、柏林唐人街与中国知识精英
直至1930年代,汇聚于柏林的中国学子以夏洛登堡(Charlottenburg)区域的康德大街(Kantstraße)为中心开展日常学习与生活,逐渐形成一条以中国留德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颇具规模的唐人街(德语为Chinesenviertel,直译为“中国人区”或“华人区”)。中国留学生在柏林的居住条件往往与当地中产阶级家庭学生看齐,一般“借住在身份相当的康德大街或临近街道的德国人家中”,其在异国的“新故乡是柏林的夏洛登堡区”。中国留学生聚居在这一城区更多是出于实际的原因。当时中国驻德大使馆和几所柏林高等学府都坐落于该区,附近旅店老板以低廉的房租向留学生出租较好的公寓,加之康德大街生活便利,因此得到中国留学生群体的青睐。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就曾提及自己抵达柏林之后安顿在康德大街的经历:“清华老同学赵九章等,到车站去迎接我们,为我们办理了一切应办的手续……老同学把我们先带到康德大街彼得公寓,把行李安顿好,又带我们到中国饭店去吃饭。”
离康德大街最近的高等学府是柏林工业大学,在这所大学深造的中国留学生(以工科学生为主)既是柏林唐人街的主要居住者,学成归国后也成为近代留德学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细分群体。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中国亟须救国兴邦的现代科技人才,这批归国的留德工科毕业生之中涌现出许多中国现代科技领域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或担任民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要职,或创办大学和担任大学校长,或引入现代教育理念,创办其他各类教育机构,“为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学德国的校长一代’”。例如曾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及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曾任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校长的宾步程、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曾任同济大学校长的阮尚介、曾任西北大学校长的李仪祉、曾任南京大学校长的朱家骅、曾任重庆大学校长的胡庶华等,均于20世纪初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
据统计,1901学年在柏林洪堡大学注册学习德国文学、哲学、政治学、神学等专业的中国人有120余人。此外,1912年至1920年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蓬勃发展,使得寻求救国“科学”与“民主”真理的有志青年陆续来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故乡,“形成了早期留德来柏林的中国人员中的新一类”。近代留德的中国留学生络绎不绝,1924年达到高潮,“仅柏林一地就有近千名中国留学生”;1930年代,留德人数从1934年的400余名,上升至1937年的700人,其中公费占20%,自费占80%。作为在柏林高校学习的中国知识青年,无论官费还是自费,他们大多来自富裕家庭,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往往德语流利,风度翩翩”。一份对柏林大学1898年至1945年中国留学生档案的统计显示,在此期间,仅柏林大学一所高等学府就共有近700名中国学生注册就读,其中大部分学习化学、机械、电机、医学和陆军,少部分学习文科。
除了中国留学生群体,彼时的柏林唐人街还留下了朱德、宋庆龄等革命先行者的红色足迹。他们先后来到柏林参加国际共产党和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的活动,积极地在政治圈内与爱国青年和同识之士讨论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国际无产阶级团体密切合作。由此,在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德国首都柏林,荟萃了大批20世纪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文化与政治风云人物。中国留德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当时德国人对中国人的族群印象,他们作为一个古老文化的载体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尊重’”。
三、近代留德学人的中华饮食记忆
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饮食是最早而且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海外中华文化的标志”,餐饮业也是华人在德国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构成透视柏林唐人街历史与文化的一个窗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中国学生的留学德国潮,柏林出现了一批新开设的中国餐馆,一份1931年的《留德指南》这样描绘道:“近年来以留学生增多,柏林中国菜馆的生意亦日兴月盛,现在已有天津、津汉、中国、东方等数家。”这些中餐馆正是集中于康德大街,其中最知名的为1923年开业的天津饭店。天津饭店由中国驻德前公使馆的厨师经营,既是柏林第一家中餐馆和德国首个面向当地顾客营业的中餐馆,也成为柏林唐人街上的标志性建筑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聚餐首选。1924年的《申报》特别报道了天津饭店:“此肆于上年春开张,系一咖啡馆之旧址,布置尚整齐,侍者均穿礼服,尚有柏林上等餐馆之规模……此馆之市口甚好,生意颇盛,主顾大半为中国学生,其他国人间有之。”
就中国留学生和其他旅德华人而言,以天津饭店为代表的中餐馆是他们一到柏林的必访之处。在诸多当时的留学或欧游日记中,都留下了此类记录。季羡林曾描写自己抵达柏林后去中餐馆:“老同学……又带我们到中国饭店去吃饭……服务极为热情周到,能蒸又白又大的中国馒头,菜也炒得很好,价钱又不太贵,所以中国留学生都趋之若鹜,生意非常好。”民国教育家董渭川在访德时也盛赞柏林中餐馆:“吃饭多半是到康德街中国饭馆里去……那条街上有好几家,也有南北口味的差别……居然可以吃到馒头、稀饭、饺子等,虽系‘逾淮之橘’,也大可解馋。”
柏林中餐馆之所以受到中国留学生和当地其他族群的欢迎,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食物除了其基本功能,还连接着烟火生活和故里他乡,透露出绵厚的风土人情。饮食承载人类的饮食记忆,也凝练出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的饮馔之道和文明智慧。对于在柏林的中国人而言,中餐极大地抚慰了他们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胃”,联结着自己思念故土家园的情感。对于康德大街中餐馆的其他食客,饮食是中华文明的具象表达,中国饮食文化的精致之美,色、香、形、器的统一之美,以及蕴含着深厚礼仪传统的礼仪之美,无不让外国食客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餐馆吸引了柏林的波希米亚人、德国人、蒙古人、印度人、日本人等来自其他族群的食客,受到德国当地社会的普遍认可。1925年,德国当地报刊《柏林日报》(BerlinerTageszeitung)形容天津饭店的饮食“也符合欧洲人的美学和肠胃”,在德国美食评论家的眼中“既高档又充满异域风情”。
其二,1920年代,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割地赔款,货币马克贬值,生活物价较之其他欧洲国家更为低廉,柏林唐人街的中餐馆对留学生而言并非一项高昂的经济负担,而是物美价廉:“他们在饭馆里或中国菜馆里,仅贵一二个马克,也可舒舒服服地吃一顿饱。用不着自己动手,却有堂倌服侍你非常的周到。并可选择你所喜欢的东西,还可喝杯酒,以助雅兴。”对怀揣美元、英镑的留学生来说,德国的物价更为便宜。彼时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每月八十美元的官费尚属拮据,但若在德国,每月二十美元足以过“上等的生活”。
其三,柏林中餐馆尽管不多,但在装潢、食材等各方面都颇为考究,不仅能提供优质的餐饮品质和服务,还别具特色,故而吸引了源源不断的中外食客。1935年访德的民国电影皇后胡蝶描述柏林的中餐馆:“内部的装修完全用中国的美术色彩……所用菜肉原料是由伦敦运往的……除了厨子之外,其他一切堂役都是德国人。其他的中国菜馆如天津,汉津,及南京等,都是一般地没有中国人的员役。”早在一百年前,柏林的中餐馆率先使用进口食材,完全雇佣德国员工,致力于打造高端的中餐品牌,这在全球唐人街和海外中餐馆的历史中别树一帜。曾于1920年代求学德国的水利专家沈怡、应懿凝夫妇在《欧游日记》中描绘了每日同中外友人出入柏林各大中餐馆的盛景。彼时柏林中餐馆甚至已开始供应中国江南地区的传统美食——大闸蟹,且品种、做法、味道都“真真道地”,其背后缘由不仅如作者所言,与“德国货轮常往来于欧亚”有关,蕴含着民国时期中德密切交往的经贸史与航运史,也折射出以中餐为视角的德国华人移民轨迹和柏林唐人街的兴盛历程。
此外,除了传承与推广中国饮食文化、提供高品质餐饮服务以外,近代柏林中餐馆还承载了重要的社会交往与思想传播的功能。一方面,包括留学生与餐馆经营者在内的华人推动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国际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常常与外国友人在中餐馆聚餐,向在德国的其他族群推广中国饮食,一如《欧游日记》提及的“约匈牙利人哈斯君在天津饭店餐叙,彼从未尝中国肴馔,食时啧啧赞赏不止”。另一方面,这些柏林的中国知识精英在中餐馆的聚会并不仅仅关乎日常生活,还往往涉及政治议题。留德的爱国学生普遍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问题,在中餐馆聚餐时对国内外政治局势高谈阔论,希望学成后“为祖国发展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化工业大国作出贡献”。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日本入侵中国,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开始进行政治抗争,他们出版反日中文报刊和传单并在中餐馆散发,“在天津饭店,客人甚至常常发现菜单里夹着反日报纸”,康德大街其他中餐馆也拒绝日本食客入内。爱国青年和左翼学生以中餐馆为政治和宣传阵地,积极地建立与德国左翼团体、学者和艺术家的联系。
二战期间,康德大街的中餐馆未能幸免于难。但在战后的德国,中餐馆仍然被视为广阔世界和国际化都市的象征之一。时至今日,随着1980年代以来新的留德求学热潮和华人移民潮,柏林的中餐馆不计其数,康德大街的中餐馆、中文学校、华人社团、亚洲超市、针灸馆等渐次复苏。即便规模远不及旧金山或纽约等地的唐人街,它依然以逾一个世纪的历史与文化底蕴,被视为柏林的唐人街或亚洲街。柏林唐人街的中餐馆变迁也为德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刻上了烙印,丰富了德国社会的饮食文化。
四、结语
作为中西文化交汇、博弈与融合的异文化空间,晚清民国时期的柏林唐人街与中餐馆既是中华饮食文化国际化的早期推手,亦成为近代赴德求知的知识精英、爱国青年和左翼学生的政治阵地,承担了重要的文化传播、社会交往与思想宣传的功能。康德大街的中华饮馔承载着近代留德知识分子的情感记忆,连接起异国他乡与故土家园,通过他们的饮食书写等文献史料,让人得以回溯近代留德学人的心路历程,重新审思柏林唐人街的历史变迁、群体记忆及其当代意涵。
参考文献
[1]季羡林.留德十年[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
[2]李雪涛.“人豪第一”的宗教改革家——康有为《德国游记》对路德的认识[N].中华读书报,2017-11-1.
[3]刘海铭,李爱慧.炒杂碎:美国餐饮史中的华裔文化[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1).
[4]刘悦.德国的华人移民——历史进程中的群体变迁[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5]孟虹.中国人在柏林[M].柏林:柏林市议会外国人管理局,1996.
[6]叶隽.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7]叶隽.主体的变迁: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8]叶隽.蔡元培的留欧时代[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21.
[9]伊莎贝拉·丹尼尔.听柏林第一家中餐馆讲述它的故事[OL].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微信公众号,2017-10-9.
[10]周松芳.饮食西游记:晚清民国海外中餐馆的历史与文化[M].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