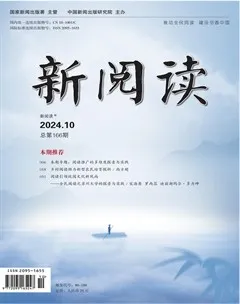乔传藻儿童文学中蕴含的生态教育观
生命意识是儿童文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也是生态教育观的重要体现。生命意识以生命为本位,关注人类及非人类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乔传藻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尊重儿童本位,将儿童解放到大自然中自由畅快地嬉戏玩耍。他关爱非人类生命个体,抒写动植物生命之美,向儿童传递着自然生命的整体意识和人类自我的反省意识。乔传藻通过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传达生命意识,完成了对儿童的生态教育。
儿童文学与教育观念的发展
在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走过的百年道路中,儿童文学发展理念经历了三次转型,分别是与世界儿童文学的接轨和学习、内容以儿童的生存与命运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生存结合为中心及儿童文学逐渐以儿童为中心,儿童本位,为儿童服务。[1]因此,儿童文学的样貌也不断发生着改变。“儿童文学”的概念是由五四启蒙思想家从西方译介过来的。启蒙思想家们发现了儿童,确立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这种本位思想强调儿童文学属于儿童,要求作家以儿童为本位创造出儿童喜欢且能看的文学。于是,当时出现了一批尊重儿童、崇拜童心的儿童文学作家,如叶圣陶、冰心、王统照等。他们书写自然,通过表现自然中的美好诗意来保持纯净无暇的童心。然而,基于中国20世纪前半叶动荡的社会现实,儿童文学中的教育理念与社会问题有着紧密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儿童文学立足于“为人生”配合革命现实的需要,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直到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再一次回到了“为儿童”的儿童本位。
鲁迅认为过去西方对于儿童的误解,是把他们当作是成人的预备,而中国人对于儿童的误解在于把他们视为缩小的成人。但是,儿童的世界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儿童既不是成人的预备,也不是缩小的成人。儿童是区别于成人独立存在的生命个体。乔传藻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儿童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富含自由的天性。他笔下的儿童在自然中得到了解放,独立畅快地做回了儿童自己。
时代的进步及前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社会对儿童天性的压抑日趋严重,部分家长对儿童过多的控制与要求导致儿童心理和生活压力过大,生态教育便应运而生。生态教育树立人与自然的整体主义。首先,它突出了人和自然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互动作用,反对二元对立和一元价值观。其次,它注重人的精神生态,强调对儿童深层心理进行教育。因此,对儿童的教育观念必然是立足于具体的儿童发展实际。
乔传藻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生态教育
基于“生态教育”这个词语,生态批评学家提倡把生态学和教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儿童对生态建设的参与。儿童教育者相信,引导儿童们到田野中去,可以促进生态教育的实施。他们鼓励儿童亲身体验大自然,欣赏花草树木的五彩缤纷,观察动物们的生命活力,触摸自然大地的肌理。这样做,不但有助于儿童在早教中健康成长,还能提高他们阅读文学的代入性和想象力。只有对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进行反思,才能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乔传藻在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引导儿童轻松地、欢乐地走出课堂,走进自然世界,并从中获得了审美的力量。
乔传藻的儿童散文《醉麂》里面就包含了对生态教育的思考。年轻的女教师带领着小学生们坐在绿绒毯似的草地上,尽情地欢唱。她会温柔地将学生搂在怀里,愉快地给学生们打拍子。箐坡峡谷里水声潺潺,一只小黄麂从山林跑出,孩子们张开手臂热情地欢迎这位客人。女教师走在孩子们身后,她露出杜鹃花似的笑容。这幅其乐融融的景象不禁让人联想起《论语·先进》里孔子带着众弟子们到泗水河边春游的故事。孔子要大家谈论人生理想。曾点一边弹琴一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之时,能与青年朋友和儿童们结伴出游。大家在沂水中游泳,在河边吹吹清风唱唱歌。孔子对曾点的回答表示赞赏,其原因就在于从山水之乐中,人们可以体味生命情趣,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醉麂》中女教师没有局限于课堂的书本教育,而是引领学生们置身于大自然中陶冶情操。明媚的阳光、碧绿的草地、机灵的醉麂与充满活力的儿童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机无限的生命图景。在自然和谐的氛围中,女教师完成了对学生的生态教育。
乔传藻认为,在儿童的世界里,他们的想法都是能被允许的,他们的行为也是合理的。他们有一套较少受外界束缚的认知方式。儿童保留了人与生俱来的真实的性格特点,拥有挣脱束缚、憧憬自由的天性。相较成人,他们缺乏一定的自制力,克制不住嘴馋贪吃的天性。《吃算术》中,老师给赵小水做课后辅导。老师给了赵小水一把蚕豆,让他把蚕豆分作三份,数清楚每份有多少。赵小水在数蚕豆的时候竟然把这些小豆豆都放到嘴里吃了。老师发现时,赵小水只好羞红着脸说:“老师,你就教我数鹅卵石算了。”短短的描写中,一个天真调皮却不失可爱的顽童便跃然纸上。乔传藻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想玩的时候就要玩得愉快尽兴,有时甚至乐不思蜀、忘乎所以。他们在山场学校背后的栗树林里打架干仗,在波光粼粼的响水河里徜徉,在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中穿梭。抓鱼、摸虾、打水仗成了他们的拿手功课。20世纪70年代的云南边寨乡村,保留了原始野性的气息。乔传藻笔下的儿童在这里获得了释放天性的原初活力。
乔传藻笔下原始的云南生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云南的土地为当地的儿童提供了生长的场所,栖居于不同大地上的生灵万物,将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当地环境的影响。相比现代社会对儿童天性的压抑,儿童在大自然中的活动,更益于他们心灵世界的发育。
成人有责任通过一系列的引导教育来塑造儿童的品德。称职的家长会把丰富的人生经验传授给他们的子女。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把良好的道德品质灌输给了后代。在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看来,儿童的道德观全然有赖于自身的观察、体验、感觉与适当的引导。这些都是成年人应该予以提供的外部条件。洛克特别指出,家长必须引导儿童对动植物释放出善意,培养孩子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准。[2]如果没有成人的教育引导,儿童缺乏正确的善恶观念,可能会肆无忌惮地伤害和折磨那些落在他们手里的小生灵,并以此为乐。因此,儿童文学如何向儿童读者传达自然万物的整体意识和人类自我反省意识,便是其生态教育的题中之义。
乔传藻通过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描述,进行着对儿童的生态教育。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如沧海一粟,被保留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隅,存在于边远的密林乡村。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里的大象,默默守护着原始村落里的乡民,它们留下的道道脚印,震慑着豺狼不敢随意出没。(《野象谷》)身为护林员的“我”对一只野猴产生无限的挂念,因为我们彼此真诚用心的相处连接了不同物种的语言。几颗香喷喷的炒蚕豆,一株株娇艳欲滴的蝴蝶兰,是我们友谊的见证。(《野猴》)音乐不仅仅是人类才懂得欣赏的艺术品,深山里的猴子也会被优美的琴声所陶醉。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宇宙生灵整体之间都存在着普遍性和一致性的生命韵律?人与自然万物天然同一,密不可分。(《琴猴》)春日溪涧,善良淳朴的孩童,乖巧懂事的小黄麂,共同构成一幅万物有灵的生命图景。小黄麂似乎知道自己不能在学校里尽情撒欢,便乖乖地坐在了学校的大门前,安静地听着老师给学生们上课。(《醉麂》)乔传藻以满含爱意的目光注视自然主体。他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将具有生命意识的对象范畴从人类儿童扩展到了非人类个体。他没有带着人类的优越感去俯视众生,面对自然生命,他总是怀着敬畏和欣赏的眼光,与之平等交心。面对西双版纳热带丛林里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他不禁感叹:“‘打不死’啊,这就是你再生的秘密。你的信念正如你的根茎一样顽强。我敬佩你!”(《打不死》)“尽管我不是佛教徒,站在你的面前,禁不住也要双手合十了。”(《铁心树》)
敬畏生命是生态教育的基本道德原则。人类既然进化为思考型动物,就更加要懂得如何敬畏生命。人类应该去敬畏自然里每个独立存在的生命体,宛如敬畏自己的生命一般。人类需要将共情的对象范畴从人扩展到一切自然生命体。猎人扎山看到扭角羚趴在草窝中给幼崽喂奶时,他放下了举起的猎枪。(《黑眼圈》)生物系何老师见证了蟒蛇夫妇一里一外分工守护洞中的蛇蛋,喃喃道:“我们在这里做出的任何响动都是对大自然的亵渎。”(《采集标本》)而自出生便生长于此的山林儿女们早已同自然万物水乳交融。他们也更懂得如何敬畏生命、尊重自然。他们从不肆意掠夺,不恃强为大,从始至终都以赤子的心灵感悟自然,学习自然,用行动保护着自然。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让他们倍感珍惜这些和他们同呼吸、共患难的生命。
乔传藻笔下强烈的儿童生命
回顾历史,人类的生命力往往只有自身与生态万物置身于自然的生存环境时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自然环境能够激活人的生命力量。乔传藻对儿童形象的塑造,展示了人在自然环境中焕发的生命力。乔传藻在接受《民生报》采访时说过:“贫穷中的美丽是弥足珍贵的。”乔传藻笔下的儿童生活在云南边寨山区的原始密林里,拥有最充沛的活力和最自由的活动天地。他们宛如天地之间的精灵,无论是呈现的外在形象还是内在品质,都迸射出一种勃发的原始生命力。他们拥有健康的体魄,在大自然中学习到了生存的技巧和本领。他们把象耳朵叶折起来当杯子拿去舀山泉水喝,他们身手敏捷地爬到树上采摘牛肚子果来充饥,他们热了就跳进响水河里冲凉降暑。儿童们独特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与束缚。他们思想独立,勇敢正义,富有探险精神。正是在这种原始生命力勃发的状态下,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时显得愈发坚韧。
在相同的年纪,城里一些儿童被家长们众星拱月般呵护着,享受无微不至的照料。而乔传藻塑造的儿童形象,他们早已结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阶段。大自然促使他们迅速成长,也使他们具备了更加完备的生活能力以及丰富的生存技巧。这些儿童通过自我探索以及经验积累,在大自然中锻炼出了各种本领。
他们往往身穿青布衣裤,腰上斜挂长刀,背挎桑木硬弓。他们将象耳朵叶做成扇子,用长刀劈开拦路的刺藤,砍下一截金竹当作杯子。《箭蜜》中刻画了一个原始生命力旺盛的少数民族儿童形象。其故事背景是乔传藻年轻时上山下乡做知青时的地点——西双版纳。这些儿童生活在滇南野雾茫茫的原始森林。悬崖峭壁、参天古树、野生动物伴随着他们成长。在大自然的孕育下,他们获得了跃动的生命姿态。
昂扬的生命力使得乔传藻笔下的儿童面对困境时显得更加坚韧。当挫折和困难来临时,作为孩童的他们也会犹豫和害怕,但凭借着过人的魄力以及坚如磐石的毅力,他们选择勇往直前。在《鬼箐》中,基诺族儿童沙约遇到危险。他沉着冷静、从容应对,顺利解决了村民的心头“大患”。沙约的表弟把家中的小牛犊给放丢了。为了小表弟不被责罚,沙约带着黄毛猎狗便只身前往“克拉抠”山箐找牛。这条山箐的名字,翻译过来便是“鬼的峡谷”。平日里,几乎无人敢涉足这块禁地。沙约始终只是个儿童,他也考虑过折返,知难而退,但他意外地遇到了将小牛犊吃入肚中的白花黑尾蟒。联想起村里关于“山鬼”的传言,沙约智斗大蟒,不仅破除骇人听闻的传言,而且帮表弟解了围。
结语
生态教育为审美教育提供了指导,可以提高儿童的审美能力以及培养儿童的审美创造力。它能帮助儿童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难能可贵的是,它还可以发挥出一些特殊的作用。比如,通过对自然的审美活动来表现出对非人类生命的关怀,保证人类的精神生态平稳发展,彰显自然个体的生命光辉。对儿童来说,生态教育既为他们提供了参与解决生态危机的实践途径,又能培养他们的同情心和想象力,以及对生命的感受力。同时,生态教育也对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批评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乔传藻创作着具有能唤醒人类生命意识的儿童文学,强调尊重儿童的发展理念,用儿童文学创作与生态教育展开对话,引导儿童身心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楚雄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 王泉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与五代作家[J].长江文艺评论,2016(03).
[2] 付玉琪.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