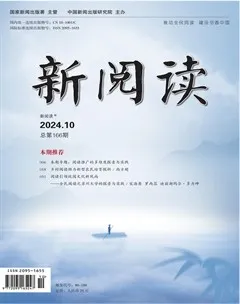一部西域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 众人谈邱华栋《空城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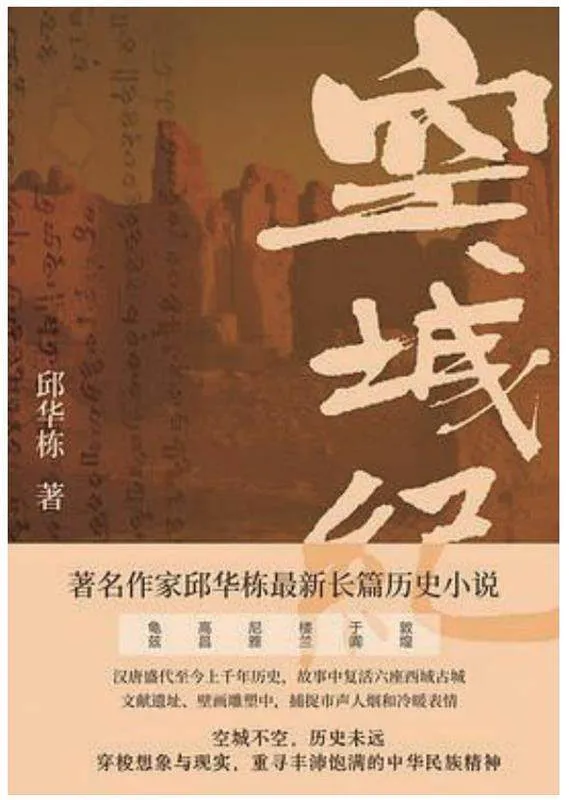

9月19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的《空城纪》新书研讨会在十月文学院举办。本次活动是第九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重点活动之一,由《十月》杂志社、译林出版社、《北京文艺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阎晶明、张清华、贺绍俊、梁鸿鹰、孙家洲等20余位评论家与北京出版集团、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领导共同研讨。与会嘉宾对《空城纪》给予高度评价,本刊选摘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交响乐般的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空城纪》这本书是在文化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格外强调的背景之下出版的,从创作的角度看是与当代重大主题相顺应的。这本书历时6年完成,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创作功力。
这部作品交响乐般的结构让人欣赏。书中的龟兹、高昌、于阗、尼雅、楼兰、敦煌这六个古都废墟如六个乐章,相当于六个独立的交响乐,是相对完整的、设计感特别强的布局。这些古都废墟有一些共通性,又有不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整体上看都是空城,空城里面有古代的往事,它是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展现了对历史的叙述和表达。
作者对历史的叙述是有主题诉求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融合过程的强调。这个主题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回响。这部作品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小说叙事方面得心应手的才干,叙述视角的绚烂、诗情,加之既有男性的视角,也有女性的视角,总体来说是很独到的写法。
地层勘探与知识考古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清华:通常来看,一个现代作家写作的地理空间都相当小。与古代传奇小说的广大地域空间不同,卡夫卡多限于狭小的公寓或办公室场景,博尔赫斯是着意营造他的“交叉小径的花园”,福克纳多流连于他的“约克纳帕塔法”的地方性,川端康成则常盘桓于日本中北部的几个城市。中国当代最成功的作家通常也是,莫言专注于“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余华也多写南方小镇。而邱华栋写作的世界是这样广大,从大都会的北京,到几千公里外的新疆;从后现代都市的玻璃幕墙,到古代的西域诸国。除了短篇小说,还有诗歌写作、长篇和非虚构,此外还有版本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对世界文学的广泛关注,等等。如此广阔的界面,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与吞吐量,在当代作家中堪称一个稀有的特例。
《空城纪》显示了邱华栋写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从现实越向历史,从当下穿向古代,从东转回西。我在想,其中固然有大环境的推动和牵引,比如对中华传统文明的探索与思考的使命感;但更多的还是源于他自身经验的发酵,他的童年经验,所谓“故乡”的与众不同,是根本的内在因由。在生命的原始方位中,天山南北,大漠西东,对于我们来说是遥远的异域,但对于华栋而言,则是魂牵梦萦的熟谙故地。这给他书写这片神奇的土地注入了原始的动力和源自生命深处的激情。在我看来,邱华栋虽然身居此地,但在其经验与文化、心理与性格的构造中,骨子里还是一个西部之子。他强悍的体魄,旺盛的精力,旷达乐观、豪气干云的性情,都像是一个来自西部的游侠。《空城纪》不是一部以故事的猎奇与穿越小说,而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历史怀想与文明探究,是对于我们多元文化的结构与源头的一次大规模的地层挖掘与知识考古。这是一部真正的实地勘探加知识考古的作品。其中历史的熟谙,语言屏障的逾越,风物的斑驳杂陈,生活方式的彼此亲近,不同的风习、语言、文化、信仰,是如何通过个人的血肉之躯、生命的桥梁,透过政治的博弈、信仰的交汇、战场的搏杀、宫廷的争斗,还有血缘亲情的生死连接,最后化为了斩割不断的共同体,融汇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庞大实体。作者巨量的知识,小说中所涉及的西部的地域知识、地理知识、风俗知识、风物知识,如星空般斑驳浩瀚。单是那些乐器、乐谱、乐理的名称与来历,比如关于历史上有名的“霓裳羽衣曲(舞)”究竟是何形构和阵势,透过这部小说,我们有了一个想象和概念;小说叙事的视角刻意使用第一人称来进入历史,不止作为人,还成为“物”,成为一枚铜钱的叙说,其中不断转换主体的叙述者“我”,仿佛一个个悬空于那沉默时空中的灵魂,在与千年后的我们诉说。这一叙事方法的难度可想而知,由此他让沉默的历史重新打开,让那“七月也会寒冷的骨骼”还魂复活,以此来超越“被编织或被讲述”的宿命。小说中广阔的诗意,是该部作品的气息与灵魂所在。这种诗意不是来自个人的感受与情志,而是来自一种历史的激情,来自哲学的追问、生命的顿悟、文明的怀想,来自其上天入地的追思,与自我生命的代入。除此,小说中还带着作者的故乡经验,带着生命原乡的悲愁,这一切的混合体,构成了这部小说中广袤而阔大的、磅礴而流动的诗意。
《空城纪》是一部富有匠心,结构独特的“橘瓣”式的作品,这在当代小说中当然并非孤例,当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即五个中篇小说的连缀与集合。但其整体性却是鲜明和不可替代的。《空城纪》也是如此,其互为镶嵌的、跨越时空的故事,其实是西域千年史的一种连缀。如此巨大的历史体量,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人物的悲欢离合来展现的,是将大历史还原为个人的经验史来实现的。这里有一系列的关于历史哲学、叙事诗学的问题都值得探究。此外,还有叙述难度的问题,单纯通过“叙述”而不是描写,来构建小说的细节性与生动性,这本身也具有极大的挑战。再就是“上帝视角”与“人物视角(限制性视角)”的混合交融,也是小说的一大特色。
西域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
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空城纪》以《龟兹双阕》《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六章结构了这部长篇小说。繁复的历史,苍茫的废墟,复杂的人物,瑰丽的风情和奇异的传说,构成了西域两千年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
说到小说的缘起时,作者有这样一段独白:“我出生在新疆天山脚下。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年放暑假我们一些少年骑自行车、坐长途车到处跑,喜欢探寻周边的世界。我们到了一个废墟,那个废墟我后来才知道是唐代北庭都护府的废墟遗址。那个废墟十分荒凉,荒草萋萋,有野兔子、狐狸、黄羊出没,我们几个少年也不知道是什么废墟,突然之间,迎着血红般的晚霞,眼前出现了成千上万只野鸽子,从废墟里飞起来,在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心中第一次留下新疆大地上的对汉唐废墟的印象。它非常美丽,甚至是有点壮美感,飞起来了。”这是一个画面,这个画面镶嵌在作者的脑海经久不忘。我们读到他的描述,也会为他盎然的诗意深深感染。那个真实的西域,也是被想象的西域,实在是太美好了。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一个情缘,“千卷书我已读过,万里路我已走过”,但如何实现他的愿望创作出一部作品是另外一回事。读过《空城纪》之后,我为作品描绘的西域深感震撼。我们知道,历史的写作也是一种虚构,对历史书写的选择就是虚构的形式。比如,在《龟兹双阕》中,小说选择的是西域音乐,是贯穿小说中汉琵琶的声音和形状;在《高昌三书》中,选择的是历史人物和帛书、砖书、毯书等记录、书写和流播的方式;在《尼雅四锦》中,选择的是汉代丝绸在西域的发现及背后的历史信息;在《楼兰五叠》中,选择的是楼兰历史层叠的变迁,贯穿其间的是一只牛角的鸣响;在《于阗六部》中,选择的是于阗出土文物背后的想象可能,涉及古钱币、简牍、文书、绘画、雕塑、玉石等附着的故事;《敦煌七窟》涉及的是佛教的东传和敦煌莫高窟发生的人间烟火故事之间的联系。因此,《空城纪》在结构上是一个并置结构,这与我们常见的线性结构、复调结构等小说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结构方式,使小说有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结构,为作家的虚构和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作为历史小说,它不止是要还原或激活历史。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克罗齐看来,编年史是没有生命力的死的材料的编排和堆集,而真历史则是活生生的历史。我们总是从现在的立场出发,以当前为参照来观察和认识历史的。过去的历史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关切,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与我们当前的生活无关,它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只能是死的历史而不能成为活的历史。克罗齐的这个看法,既证实了历史叙事的虚构性,也证实了历史的当代性。小说中对出使西域的著名人物如张骞的讲述颇具代表性。他曾被匈奴扣押13年,逃离之后,不是奔向来路回到长安,而是为了完成汉武帝交给的使命持续西行。这是一种操守,一种情怀和一种凛然的气质。我们之所以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表示倾心认同,就在于作家在选择他书写的人物及品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汉唐气象,同时与当代有关:我们在当下还能看到多少这样的人物。
小说的讲述者是“我”。但是“我”的身份极为特殊,我可以是一个女人,可以是一个卖香料的商人,可以是在大牢里等死的囚徒,可以是释迦牟尼的好朋友,可以是一枚铜钱、一匹野马、一匹渴望在岩画中躲藏获得更长生命的马,也可以是在“798”游荡的当代人等。“我”可以是任何人与物。这个变幻莫测的讲述者在《空城纪》里获得了最大的自由,他天上人间天马行空,他所到之处或目光所及,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作者对这个讲述者的“人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西域成为传奇,与这个讲述者的存在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叙述学的意义上说,邱华栋对故事和讲述关系的理解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小说文无定法,敢于为所欲为的作家,敢于突破界限的作家才有希望、有可能成为大作家。
如此遥远和宏大的历史小说,虚构能力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和挑战。要填充如此巨大的空间,除了历史文献资料,实地勘察外,更重要的就是作家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力。如前所述,讲述者的“人设”使其无所不能,他成了一个“在场”的讲述者,这种“仿真”式的讲述和渲染,犹如身临其境。比如《霓裳羽衣舞》的演出,龟兹古乐的演奏以及锦裤、锦帽、复生的女尸、微笑的佛头等,除了文献资料的基础,艺术想象的权重更重要。此外,作者选择知识讲述,比如,“白衣秀士用的是枫香调,等于是羽调的转调,他弹的还是《绿腰》,可调子一变,那整首曲子的风格就大变了”。如果没有西域音乐知识,这样的句子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可以说,邱华栋竭尽了对西域赞美之能事。他无论抒情叙事,对曾经家乡的赞美不遗余力。因此,西域在他的赞美声中如诗如画大美无疆。于是,《空城纪》就是一部名实相副的西域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