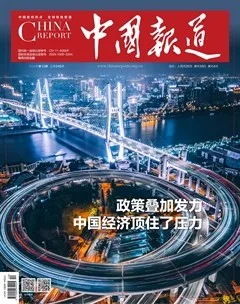加强国际合作,为全球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近年来,我国海洋油气装备设计建造能力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重要突破。尤其是这10年,中国海上油气开发实现“造船出海”,建设“海外大庆”的路线越来越清晰,全球性技术资源整合能力持续加强,共同开发海洋能源的友谊之花开遍世界各地……
“海上没有路,海上也全是路。海洋能源开发凝聚着全人类的智慧,我们有信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海洋能源开发与国际合作之路,这个路会越走越长、越走越实。”海洋油气田开发与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九届中国科协副主席周守为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专访时说。
海洋油气开发艰难起步
在自主油气开发的道路上,中国曾经备受“卡脖子”之苦。
新中国成立前,外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没有油,“中国贫油论”甚嚣尘上。然而,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高瞻远瞩指出,中国油气资源蕴藏量是丰富的,特别是在广阔未知的海洋。
当时,世界海洋石油工业处于起步阶段,在被层层“卡脖子”的背景下,中国的海洋能源事业艰难启航,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海上石油勘察,1964年,在渤海发现了中国的第一个海上油藏——埕北油田,但一直到1979年整个渤海的石油年产量才仅有19万吨。
周守为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石油专业大学生,28岁考大学,毕业时已过而立之年。出生在四川、求学于西南石油大学的周守为此前的生活与大海几无交集,却义无反顾地选择海洋油气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
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周守为最难忘却,也最为引以为傲的是一位“老朋友”——“渤海友谊”号。
“渤海友谊”号是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建造的FPSO(浮式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它是集原油加工、海上油库、卸油终端等功能于一体的海洋石油开发重大设施。1989年,“渤海友谊”号开始投入生产,它的建成实现了我国FPSO设计建造零的突破,填补了中国造船工业的空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是全球首次将FPSO用于有冰的海域。
“渤海友谊”号是中国船舶工业在海洋工程领域的标志性产品,被选入中国百年造船历史上的十大名船,周守为就是这条船的首任总经理(船长)。
“渤海友谊”号服役30多年,截至2020年,累计完成外输642船次,外输原油约1796万吨。如今,功勋卓著的“渤海友谊”号已经退役,静静停靠在渤海岸边的母港,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继续向一代代青少年诉说着中国海上油气开发非同寻常的岁月。
从渤海采油矿长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守为的职业生涯一直凝聚着对海洋能源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他创新提出了建立四大油气开发体系、进行滚动勘探开发的思路,并开发了四大配套技术系列;他提出的“海上少井高产技术”解决了渤海大型边际油田开发难题,攻克了长距离稠油多相混输世界级难关;他探索出了优快钻完井成套技术,使钻井效率提高了近3倍。在周守为的领导下,国家“863计划”重大课题项目“深度调剖驱提高采收率技术”取得了成功,为我国海洋油气的高效开发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当前,能源安全成为很多国家的优先政策取向,保障能源安全的最大挑战是油气供给安全。“为什么会‘卡脖子’,归根结底是基础研究没搞好。”周守为表示,要长期重视油气基础研究,增强原创性技术攻关,以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十周年,“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着眼现实的深刻洞察,更是面向未来的深刻昭示。
大国重器征服“深海油龙”
近年来,我国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涌现出“深海一号”“海基”系列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深海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及装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也取得了有效技术突破。
2021年6月25日正式投产的“深海一号”能源站是世界首座10万吨级的深水半潜式储油生产平台,周守为在“深海一号”大气田的开发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深海一号”历时20个月,投资235亿元建造。每年可稳定供气30亿方,实现了我国油气田自主开发能力从300米到1500米水深的跨越。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建成50余座万吨级固定式海洋平台,成功掌握3万吨级超大型海洋平台和300米级深水固定式海洋平台自主设计建造成套技术。
2019年以来,国内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实施,提速“南海万亿方大气区”建设,计划2025年达成目标。埋深小于300米的天然气被称为超浅层气,勘探开发面临埋藏超浅保存难、远离烃源充注难、地层疏松钻探难等世界性难题。我国将国际业界普遍认为不具备大规模成藏条件的超浅层气作为战略性研究方向,对浅层气成藏机理和工程作业关键技术展开系统攻关,选定位于海南岛东南海域盆地平均作业水深达1500米的陵水36-1区块作为勘探目标。

据了解,陵水36-1气田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为全球首个超深水超浅层大型气田,中国海油作业团队创造性实施全球首例超深水超浅层钻井作业,顺利完成超深水超浅层气藏、钻井、取心、测试等多项作业目标,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自主建立的中国特色深水复杂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体系,补上了“南海万亿方大气区”建设版图的最后一块“拼图”。
“目前南海北部已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1万亿立方米,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优化我国能源供给结构具有重大意义。”周守为表示。
勘探难,开发更难。海底油气资源分散在不同地质储层的孔隙中,开采时要建立一条尽可能贯穿最多油气储层的“井通道”,打通这样一条通道需要精准控制钻头在地下几千米岩层中的钻进方向。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旋转导向钻井与随钻测井技术被誉为海洋石油钻井技术“皇冠上的明珠”,长期被美国企业垄断与封锁。2008年,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开始自主研发旋转导向钻井和随钻测井两套技术体系。2014年,两套技术体系合二为一后取名为“璇玑”的产品首次实现商业应用。中海油服由此成为全球第四家、国内第一家同时拥有这两项技术的企业,为世界油气勘探开发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海葵一号”和“海基二号”两大国之重器近期同时投产。“海基二号”是集钻井、生产、生活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海上生产平台,总重量超5万吨,导管架高度有338.5米,是亚洲最高最重的海上原油生产平台。其钻头通过300米的海水,在海底不到半个篮球场大的区域精准密集地打了24口井,每口井位置的精度误差不超过5厘米。“海基二号”通过优化钻进参数及钻具组合,同时应用水下微型机器人,让钻头在地下几千米之内实现精确控制,总钻进进尺超过了73500米。
“海葵一号”是世界上首个集成了海洋一体化监测、机电仪设备健康管理、三维可视化管理等多系统的“数智化”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每天,“海葵一号”都能处理超过5600吨的原油,相当于为90万辆小汽车的油箱加满油。
从海底采出的原油,经过“海基二号”4台原油外输泵的加压后,输送到2.5公里外的“海葵一号”进行进一步油气水三相分离后变成含水0.5%以下的合格原油,就可以通过油轮向外运输了。
“海葵一号”“海基二号”高度集成了超1000台关键设备,其中大约九成是由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目前,我国已完全具备了3000米水深以内的海洋油气工程装备的自主研制能力,海洋深水油气装备自主设计制造水平也正逐步进入世界第一阵营。”周守为说。
加强海洋能源国际合作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对于海洋能源的发展至关重要。周守为认为,“海洋油气是全球性的资源,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海洋油气开发国际合作成果卓著。以巴西为例,2013年10月,中国海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道达尔、壳牌、中国石油组成联合投标体,中标全球第三大盐下超深水油田——里贝拉区块。2024年7月31日,中国海油在巴西圣保罗证券交易所成功中标全球第三大盐下超深水油田梅罗油田1200万桶原油贸易长期合约资源。10月17日,中国海油所属公司与巴西国家石油管理局及佩罗塔斯盆地的合作伙伴就4个巴西海上勘探区块分别签订了矿税制石油合同。
巴西国家海洋研究所所长,巴西工程院、科学院两院院士赛根·法里德·埃斯特芬在10月18日举行的“中巴海洋科技创新论坛”上表示,希望双方在海洋油气可持续发展、海洋保护、能源安全、创造就业、高水平教育和研究、实验基础设施、海洋数字孪生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
周守为表示,在浮式LNG、水下压缩机及水下分离技术、水下采油树和防喷器系统研发、深远海浮式风电、干式采油树的浮式生产系统研发等方面,中国与巴西在深远海开发技术合作前景广阔。
2014年4月,由中国海油与国外能源公司联合研究、平行设计和共同开发的我国首个深水大气田荔湾3-1气田宣告投产。2024年3月,由我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首艘大型深水物探船“海洋石油720”,装载着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海洋拖缆地震勘探采集装备“海经”,高质量完成在印度尼西亚的深水勘探地震采集作业载誉而归。2024年4月,“璇玑”系统第二代旋转导向在非洲乌干达翠鸟油田项目应用成功。2024年8月27日,“璇玑”系统在伊拉克米桑油田实现累计总进尺40000米,总井下时间10000小时的新里程碑。目前,“璇玑”系统已在全球完成近2000井次作业,累计进尺近200万米。

周守为表示,海洋资源利用空间广阔,在发展过程中应争取实现多种能源统一开发,以实现高效开发利用,这需要在基础理论、关键技术、装备发展等方面加强科研攻关。
周守为建议,各国应共同努力,建立多边合作机制,为海洋能源的国际合作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可以就海洋能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制定国际标准和规范。各国应加强技术研发与共享,共同推动海洋能源技术的进步。通过跨国合作,可以实现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各国还应积极拓展资金来源与投资渠道,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海洋能源的开发与合作。同时,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对海洋能源项目的支持力度,降低投资风险。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海洋能源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寻求突破与合作。通过加强海洋能源国际合作,我们不仅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还可以为全球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周守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开创一个崭新的海洋能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