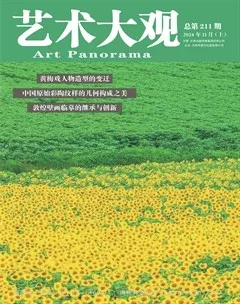徐悲鸿历史画《愚公移山》的主题内涵与艺术表现
摘要:《愚公移山》是徐悲鸿在20世纪40年代以中国画和油画形式同时呈现的特殊之作。该画以独特的人物场景设计与人物形象塑造展现出典型的中国绘画叙事范式,是中国油画和现代中国画本土化、民族化特色的具体呈现。徐悲鸿的历史画偏重于对英雄主义和行侠仗义道德精神的歌颂,同时也以描绘历史来隐喻现实,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荣辱观、节操、坚贞不屈、勇敢等人文精神,《愚公移山》堪称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活用。
关键词:徐悲鸿;愚公移山;作品主题;艺术表现
在徐悲鸿的大型历史画中,《愚公移山》是以中国画与油画两种艺术形式同时呈现的特殊之作,这一作品现存三个版本,两幅油画和一幅中国画。此作绘于1940年,相较于此前的历史画《傒我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的主题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即通过对寓言故事的视觉呈现,以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激励中国人持之以恒、不懈努力,争取国家与民族解放的坚定信念。
一、《愚公移山》创作缘起及作品主题内容
1939年11月,旅居南洋的徐悲鸿到印度国际大学访问并举办画展,抵达后受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热情接待。1940年2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甘地拜访泰戈尔,徐悲鸿乘此机会为甘地画像。作画时,甘地圣贤般的形象给徐悲鸿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通过甘地的精神气质仿佛看到了愚公的影子。此时,正是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刻,当徐悲鸿从报道中得知云南人民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力军,依靠最原始的劳动工具,仅用9个月就修成贯通南北的滇缅公路时,内心无比激动和振奋。中国军民万众一心、全力抗战的顽强拼搏精神深深感染了他,而以“愚公移山”为主题的史诗般的创作构思也在他脑海中应运而生。据吴作人回忆,该题材是徐悲鸿“早有构思”“酝酿已久”的。为了及时创作此画,徐悲鸿先在国际大学构思《愚公移山》草稿,完成后他便前往避暑胜地大吉岭继续写生创作。
《愚公移山》为古代寓言,见载于《列子·汤问》,讲述了古人愚公带领子孙不畏艰难、挖山不止,最终感动天帝将山挪走的故事。后世常用“愚公”比喻做事有顽强毅力、不怕困难的人,用“愚公移山”比喻知难而进、有志竟成的行为。1940年4月,徐悲鸿在给友人舒新城的信中曾谈起他的创作计划:“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日内即去喜马拉雅山,拟以两月之力,写成一丈二大幅中国画,再归,写成一幅两丈长之(横)大油画,如能如弟理想完成,敝愿过半矣。尊处当为弟此作印一专册也。[1]”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大吉岭写生期间,徐悲鸿率先完成巨幅国画《愚公移山》(纸本设色,143cm×424cm),随后又于8月至9月回到印度国际大学继续创作油画《愚公移山》(布面油彩,210cm×460cm)。
徐悲鸿的国画与油画《愚公移山》并没有描绘横亘在愚公门前的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画中山的具体形象被隐去,画面着重表现的是人们挖山的劳动场景和突显数位壮汉挥镐掘土的生动形象。徐悲鸿根据画面不同人物的设计选择了着衣、半裸和全裸三种视觉形式,即愚公与妇人着衣,两个挖山者半裸,其余四个挖山者和孩子则全裸。徐悲鸿考虑到愚公作为中华民族高尚道德和不屈意志的象征,未以裸体形式处理这一主要人物,而是选择了能体现其民族身份特征的着装。为了塑造出挖山壮汉的力量感,徐悲鸿突出表现画面中间几位壮汉的不同形象,壮汉赤身裸体鼓凸的肌肉和富有张力的体态构成了作品的叙事主体,愚公则隐在其后。这些裸体形象的表现,正如徐悲鸿所说:“不画裸体表现不出那股劲”[2],若处理为穿衣,画面所追求的力量感就会大打折扣。而画家对男性形体肌肉的充分刻画以及对蓄势待发力感的表现,也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象征。
二、《愚公移山》艺术表现手法
徐悲鸿画于1940年的国画和油画《愚公移山》从时间顺序上看,最先完成的是国画,其次是小幅油画(画稿),最后是大幅油画。《愚公移山》油画略大于国画,除尺寸稍作一些调整和剪裁外,两幅画的构图与人物形象布局大致相同。比较来看,油画《愚公移山》改变了中国画《愚公移山》的长卷形式,删减了中国画《愚公移山》左侧背朝观众挑土的壮汉与旁边的大象,将愚公与媳妇对话的场面情节移至画面左侧靠中间的位置,以衬托画面中央几位壮汉挥镐开山的形象。在主体人物的布局和安排上,油画《愚公移山》将中国画中近乎站立的挥镐壮汉进行了位移,使之和愚公成为画面的横向制高点。人物位置的调整与重组形成了从左至右、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回落的一条波浪线,人物间的搭配组合也显得更有节奏感。这些人物形象都是以印度人为模特画成,一字排开的六位壮年男子,右边三人以挥镐筑土的侧面形象为一组,他们或半蹲后仰,或弓步前倾,前后穿插、互为遮挡,也彼此呼应。站在画面最中间的三位壮士则依次形成了由低到高的体位变化,他们的动作从弯腰下掘到抬手举镐,再到挥起铁镐,连贯性的动作各自呈现,形成一组经典的造型,这一动作形态在油画与国画中都表现得较为出色[3]。
对于绘画空间的处理,油画《愚公移山》与中国画在形式上具有互通的特点,这也是徐悲鸿“中西融合”艺术创作手法的具体表现。他的油画大致是一种含有焦点透视的平面性布局,即主要体现平面的二维空间,而非西方传统绘画所惯用的三维空间结构。油画《愚公移山》大致承续了传统中国画的空间结构模式,主要体现含有焦点透视法则的平面性画面结构,但主体构图更接近于视点平行移动的中国画横卷形式。在油画中,人物形象虽然是依次排开,但又分前后两排,即挖山者在前,愚公与妇孺居后,且人物空间和纵深背景又是以焦点透视呈现。事实上,油画《愚公移山》的空间表现手法是中西绘画透视法的混用,仔细观察会发现,第一排人物形象虽是横向排开,但仍具有一定的透视纵深感。例如,位于画面中心的两位挖山壮汉顶天立地,离观者最近,而越往右则感到越远,这是焦点透视的处理方法。这些局部的纵深感描绘,并不影响画面整体的平面性处理,画家通过放大第二排人物的体量与高度,又使作为画面主体的人物群像从头顶看仍处于一条水平线。这是徐悲鸿以同一绘画题材将中西两种绘画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合二为一的独到之处,也是他试图平衡中西两种绘画透视空间的尝试和探索。
与徐悲鸿此前的《田横五百士》等大型历史画相比,《愚公移山》因20世纪40年代初画家旅居南洋所处创作环境的不同,画面更注重对印度高原气候下鲜明光色感的表现。油画《愚公移山》的天空色彩是高原地区所特有的蓝天白云,由于画面视点的变化,云层犹如从地面腾空而起,可见挖山地理环境的海拔。由于使用的印度男性模特,阳光下几位壮汉的肤色呈现出油亮的黝黑色和古铜色。画面中景运石的山路被阳光照亮,透现出远处乡野的田舍,与扑面而来的壮汉形象形成对比。在色彩运用上,油画《愚公移山》人物前景的草木与竹以中国画石绿的高纯度色描绘、点染而成,绿竹与绿草的形状以及在近景中的分布结合中国画的造型方式,用笔肯定、形塑具体、色层厚重而坚实,显示出徐悲鸿对油画本土化表现语言的自觉探索。
再从大幅与小幅油画《愚公移山》来看,两者的画面效果有着一脉相承的贴合度,可见画家艺术水平的稳定发挥。小幅油画《愚公移山》用来造型的轮廓线和块面准确而松活,笔触宽博、肯定、含蓄且富有写意感,颜色和谐自然,透明度较高,人物膝、肘、足等关系到结构和动态的部分有松紧、虚实和“表情”上的丰富变化,细节处理有很多“笔不到意到”的讲究,整体节奏感和一气呵成的完成度比大幅画更明显。这也说明,在技术层面上小幅油画比大幅油画更易于把握,画家从水墨语言转换到油画语言对这一题材进行再表现时更具有新鲜感,也处于情绪饱满并相对放松的创作状态。画大画时,可能因尺幅过大和创作条件受限而有所束缚,不容易施展得开,艺术上的发挥倒不一定更加出色。但综合来看,大幅油画《愚公移山》因其大尺寸的恢宏巨制具有无以替代的艺术价值,而小幅油画反倒更贴近画家一贯的风貌特征,不失为大幅油画的参照和视觉补充。
小幅油画《愚公移山》最先不太为外界所熟悉,因为徐悲鸿在离开南洋时将这幅画赠送给了新加坡友人崇文中学校长钟青海,他带回国内的是大尺幅的国画与油画《愚公移山》,他本人此后也未曾提及该作还有一幅油画初稿。徐悲鸿去世后,他在新加坡的友人于1954年2月聚集于维多利亚纪念堂举办“徐悲鸿遗作展览会”,小幅油画《愚公移山》首次对外展出,但当时尚未被关注。直到2000年6月,小幅油画《愚公移山》回流中国艺术市场,在北京瀚海春季拍卖会上以3300万人民币创下徐悲鸿单件油画成交价的最高纪录时,国内艺术界才有所了解和重视。在此期间,徐悲鸿纪念馆曾借展小幅油画《愚公移山》,将该作的三个版本安排在纪念馆同时展出,此景可谓盛况空前。
三、《愚公移山》三个版本的艺术特色
《愚公移山》三个版本的画面内容都是以横长构图安排主体人物的布局设计,数个全裸或半裸壮汉几乎占据了画面中部和右部的全部,尤以魁梧结实的挖山壮汉形象撑起画面的主要空间。这些以印度模特为原型的男性壮汉呈弧形分布,他们奋力开掘的连贯性动作极具动感和力量感,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排山倒海的气势。在表现故事内容时,徐悲鸿在壮汉形象身后安排的一组人物是愚公、孙子和“邻人京城氏之孀妻”及“遗男”。愚公与妇女在对话,虽然是背向而立,但身材被拉高,因此也较为突出。同时画面隐去了一位重要人物智叟,集中表现正面人物形象,以突显“愚公”精神的积极意义。
小幅油画《愚公移山》是徐悲鸿创作大幅油画《愚公移山》之前的预演。由于中国画横幅和油画横幅在比例尺寸上的既定区别,徐悲鸿在构思油画布局时,结合中国画的构图和人物分布做了一些取舍。相较于油画,中国画《愚公移山》同样是以近真人大尺寸进行构图,所用的人物形象体魄雄健、顶天立地,动作夸张,有呼之欲出之感。在中国画《愚公移山》中,徐悲鸿以沉稳挺健的线条勾勒人物造型,再加以皴擦晕染描绘形象的细部结构特征,其严谨的结构与用笔体现出画家高超的写生技艺和书法功力。画面中的人体结构组合及透视安排巧妙适宜,人与人之间的形态变化集中统一、力点一致、富有节奏和张力。而画面所呈现出的人们挖山不止、众志成城、所向无敌的那股劲儿更容易打动观众。
《愚公移山》三个版本在构图与艺术表现上的互通更反映了徐悲鸿对平面构置与纵深刻画两种表现空间的自由切换和平衡性追求。某种意义上说,他试图探索的是“观看”和“表述观看”两种模式混合运用的可能性,如果说徐悲鸿的油画对单个形象的表现是西方式的,那么他画面中的多个人物形象的组合则又是中国式的,这正如油画《愚公移山》的人物场景构思布局更接近视点平行移动的传统中国画横卷,而造型与色彩又具有西方绘画的特点。事实上,徐悲鸿这一时期所创作的人物、风景油画大致都以中国画横卷和立轴形式来构图,其整体视觉观感也更接近于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这可谓是徐悲鸿绘画寻求“中西融合”的重要特征,也是他为20世纪中国绘画提供的一个重要样式。
在创作三个版本《愚公移山》的过程中,为塑造好开山劈石的六位壮汉形象,徐悲鸿还以印度模特绘制了大量的素描,研究和表现他们或坐或卧或躺,或静或动,或挑担或持物的不同形象。这些模特不但具有典型的印度青年男子特征,而且身强力壮、筋骨结实,易于表现出男性的阳刚之气和力量感。在人物动态构思和组合上,徐悲鸿进行了一系列的素描分析,从直立举镐到弯腰举镐,再到屈腿举镐,以及表现屈腿的局部特写,描绘血管膨胀、青筋鼓起的腿脚、大腿与小腿的肌肉、筋骨的不同变化等,将劳动者脚踩大地、奋力开凿的动态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徐悲鸿曾说:“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他的中国画《愚公移山》将西方写实艺术观念和技巧融入其中,以写实造型为基础创造了新颖的画风,打破了传统文人画不擅于描绘大型人物场景画的局面,创造和发展了唐宋以来中国人物画题材和艺术表现的多种样式。同时,他又将中国书画的用线方式带入西画造型中,以意象韵味渗入油画的塑造与表现中,对中国式油画的创新路径进行了积极探索。
四、结束语
徐悲鸿以《愚公移山》为代表的历史题材人物画创造的是一个古典而浪漫的世界,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一个以写实形式营造的、与鲜活的现实生活看似遥远,但又有着内在联系的、活跃在画家心目中的世界。他创作的大型历史题材绘画取材范围不限于正史,更多涉及神话、传说、寓言,甚至演义和民间传奇。在作品思想主题上,画家一方面偏重于对英雄主义和行侠仗义道德精神的歌颂,同时也以描绘历史来隐喻现实,以及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荣辱观、节操、坚贞不屈、勇敢等人文精神,其大型历史画堪称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活用。
徐悲鸿通过大型历史画创作,积极探寻中国式油画与现代中国画的艺术表现语言。以《愚公移山》为代表的经史题材绘画不仅开创了中国画家以戏剧性场景设计表现中国古代历史与神话故事之先河,而且开辟了20世纪中西绘画的汇通融合之路。徐悲鸿的历史画创作以多人组合、大场景空间设计、特定的人物形象塑造为表征,形成了绘画形式语言、艺术表现方式以及精神层面上的中国叙事范式,体现出中国现代绘画的本土化与民族化特色。以《愚公移山》为代表的史诗般的巨制已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1]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艾中信.徐悲鸿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3]尚辉.自我与他者——徐悲鸿在动荡中的油画本土化之旅(1927—1941)[J].美术,2021,(12):86-93.
作者简介:邹佳凝(2003-),女,安徽淮南人,本科,从事西画(师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