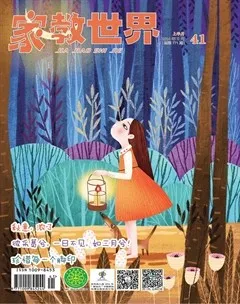《追松塔的爸爸》:属于红松林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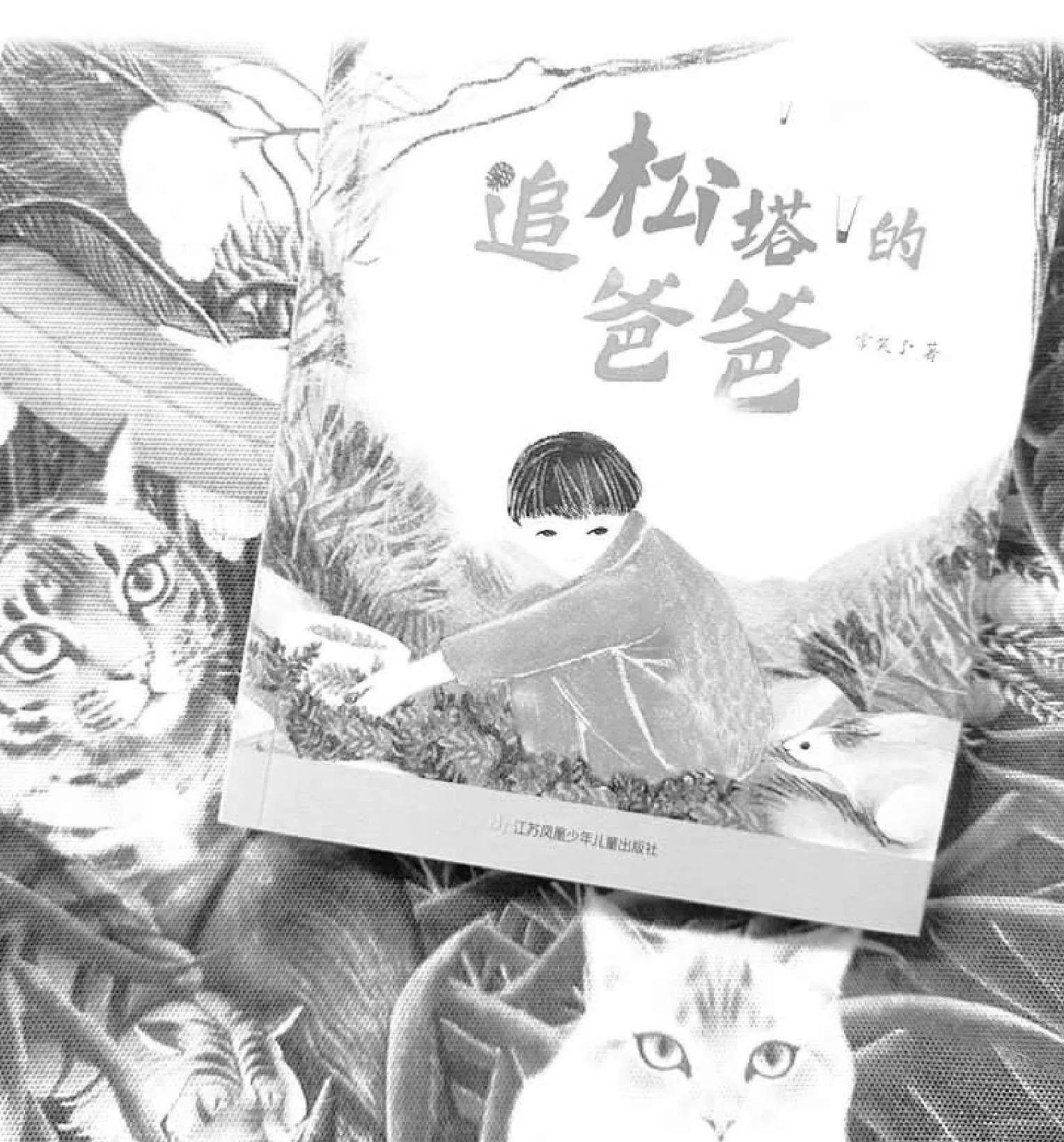

这是一部绿色环保题材的长篇儿童小说,取材新颖、紧跟时代,以东北红松林为背景,讲述了“打塔人”老侯和河悦乘坐的白气球意外飘走,侯小森和林场人经过三天两夜寻找他们下落的故事。小说双线并行,主线集中描写从白气球消失到白气球上的小森爸爸获救的三天内的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副线讲述在生活中,小森对爸爸从产生矛盾到理解、怀念的故事,生动而感人。
小说把紧张、充满悬念的寻人之旅和独特的东北民俗风情、自然岁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高耸的红松和尖锐的松针之上是梦幻的白气球,就像东北林场粗粝的生活之上,覆盖着互助的温情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寻找白气球之路是儿子走向父亲的路,也是城市儿童走近和理解山林、理解生态文明的路。
“文二代”常笑予
常新港、常笑予父女,均是儿童文学领域卓有成就的作家。常笑予说——
因为爸爸是作家,我小的时候有一点“逆反”,虽然偶尔会写一些小故事,但是从来不准爸爸妈妈看。直到十一岁那年,因《文学少年》的编辑通过爸爸向我约稿,希望我能写一个故事,后来我便发表了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当时杂志在作品下面留下作者的通信地址,于是有一些孩子给我写信,有的甚至比我大很多。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被看到”反馈给作者的力量。写作不仅仅是沉默的劳动,而是一种沟通,与自己,与读者。
小时候,我家的阅读氛围比较宽松,家里有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童话、儿童小说我喜欢看,成人文学也喜欢看。这种“博览群书”的阅读环境,给了我充分的读书自由,也让我有机会培养自己筛选和甄别的能力。
创作的时候,我把自己当作文中的一个角色,或者在多个角色中转换,我需要那种沉浸式的代入感让我和人物共情,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心境和周遭的环境。有点像是玩VR游戏,创作时全情跳进去,创作结束再跳出来,回顾全局做调整。
我觉得为儿童写作不能小瞧孩子。现在的孩子接触的信息量越来越大,时间也越来越早。他们聪明,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同时也渴求更广和更深的知识。
精彩文摘
第一章" "第一天十一点五十八分
白气球飘走了
梁库叔叔跑过来砸门的时候,小森正在把玩那块封了蜜蜂的琥珀。小森眯起眼,对着阳光看琥珀,里面的蜜蜂伸展翅膀,腹部的绒毛清晰可见。好像时间在琥珀里静止,蜜蜂还活着。
九月伊始,东北的天光白得耀眼,暑气却已经退了,秋风像个烦躁的清洁工,没好气地把城里山里天上地下扫个遍。
梁库叔叔拎着脚扎子,粗麻绑绳拖在地上,眼睛瞪得比嘴都大。
“气球飞走了!”
小森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只是木木地看着梁库叔叔。
“老侯!老侯飞走了!”
他手上的脚扎子叮叮当当碰在一起。
“轰”的一下,小森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给你妈打电话,你妈不接,估计干活呢。赶紧找她!”
老挂钟响了,里面的木头小鸟弹出来,干叫几声,回笼的时候卡了壳,仿佛关节生硬的木偶。小森看了一眼挂钟,时针分针“双手合十”,直指苍天。
梁库叔叔那辆老“金杯”载着侯小森,灰狼一样蹿了几条街,急停在大众浴池门口。
这家浴池的招牌已经褪色了,灰白的灯管弯出字的轮廓。等到天暗下来,霓虹灯亮起,人们才确信这家店不是歇业多年。不过亮着的是“大众浴也”,坏掉的三点水年久失修,老板也不挂心,反正附近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年轻的女前台横握着手机,眼睛粘在屏幕上,余光看到有人来,从抽屉里掏出两个绿色的手牌——男宾是绿色手牌,女宾是红色手牌。
“我们不洗澡,我找我妈。”
女前台抬头看了他一眼,说:“哦,小森啊。”眼睛又粘回屏幕上去了,只是另一只手慢悠悠地拔了手机上的充电线。
“阿姨,您快点儿!”
“咋的,有急事儿?”
“要出人命了!”梁库叔叔说。
女人这回认真看了看小森的脸——煞白。她什么都不说,趿着拖鞋噼里啪啦地往女浴池跑。
妈妈顾不上换衣服,穿着棕色“V”字领短袖工作服跑出来,身上散发着雾蒙蒙的热气和一种干净、好闻的味道。妈妈总在浴池待着,晒不到太阳,皮肤一天天地细腻起来,看不出是个在林区长大的女人。她的右手总在搓澡巾里包着,泡得又肿又皱,比左手大了一圈。
爸爸是个“打塔人”,从高高的红松树上把红松塔打下来。红松塔里的松子经过加工,运往国内国外的城市,再摆上超市的货架。
自打爸爸干这行起,小森就想过可能会有这么一天。他心里时不时冒出这个念头,但是他从来不敢往下想,好像多想一秒都会增加灾难发生的可能性。
小森家在松树镇,镇子不大,镇中央是林区的经营所。有人给小森看过松树镇的航拍图,应该是春天拍的,山绿得像块厚海绵,淡红色房顶连起来,蚯蚓一样细细小小地卧在里面。小森知道,镜头只要再拉远一点,这条红色的细线就会被茂盛的山林吞没。他想到自己看过的别的航拍图——连绵的群山和大片的田野,还有灯光勾勒出的北京城——松树镇太小了。
从松树镇出发,四面八方都是山。山上长满高高矮矮、曲曲直直的树,柞树、椴树、杨树、黄菠萝、暴马丁香,树下铺着沙参、桔梗、平贝、串地龙、五味子、苍术、川地血、赤芍、白芍……全是珍贵的药材。
林子里最多的还是红松树,近处长得鳞次栉比的是人工林。再往里走,剑一样的枝干插在地上,一蓬一蓬的绿往上挣,原始山林野蛮而乖张,争夺泥土、水分、阳光,拼命活。如果你闭上眼睛,静静地在森林里坐一下午,甚至能听到树的尖叫。
松树镇只有一所小学,没有中学,所以上初中以后,小森就去市里上学。妈妈在大众浴池找了给人搓澡的工作,便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方便上班,也方便小森上学。市里离松树镇有三十几千米的路程,爸爸想守着林子,就还住在林场小镇。所以小森放假的时候回镇上,上学的时候住在城里。
城里的家虽然是租来的,但被妈妈打理得井井有条,飘着淡淡的洗衣粉的味道,看上去和同学们的家并没有什么不同。松树镇的房子就没有这么清新了。爸爸出门之前和跑山回来,喜欢抽几根烟,辛辣的烟味钻到被褥和墙缝里,怎么洗都洗不掉,怎么盖都盖不住。妈妈说过他很多次。
可爸爸说:“那有什么办法,总不能在林子里抽烟吧?”
妈妈说:“你就不能不抽烟?”
两个人就不愉快起来,谁也不理谁。
通往松树镇的路连一百米的平路都没有,到处坑坑洼洼的,路中间时不时闪现一条蜿蜒的裂缝,那是泥土湿润后又干燥,开裂了。如果下雨,更是满地“蛤蟆沟”,一个不注意,车轮就会陷进去。
三个人坐在车里,一晃一颠的,车门上的矿泉水闹肚子似的咕咚咕咚响个不停。车开得快,过大坑的时候,人随车飞起又落下,会有一瞬间失重。小森的心也跟着一阵阵发紧。
妈妈坐在前面,鼓捣着手机。听筒声音大,提示音传出来:“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梁库叔叔说:“早打过了,没信号。”
林区的信号一阵有一阵无,一处有一处无,是常事。
妈妈不信邪,又打河悦叔叔的手机,是春春婶儿接的。春春婶儿的哭号声隔着电话,还是无比凄厉地灌到车厢里:“嫂子啊!我可怎么办啊——”
“先别着急,我们马上到。”妈妈安慰道。
每年九月,白露时节前后,红松塔的采摘季就开始了。一个红松塔有鞋那么大,长在二三十米高的树上。香油油的松子就藏在红松塔厚厚的鳞片里。
河悦叔叔是和爸爸乘同一个氢气球上去打松塔的。氢气球载着他们在天上飘,还有两个工人在下面扯着两根绳子,像放风筝似的。上面的人打松塔的工夫,“放风筝”的人会把两根绳子拴在树上,有时候赶时间,就用手扯着。一棵树上的松塔打完了,就换下一棵树,氢气球就这样在密林中走走停停。两只“细脚”在山里走,氢气球像云一样在树梢上飘,打松塔的人就立在云上。
梁库叔叔放在座椅中间的手机突然响了,手机屏幕上显示着“老侯”,三个人都伸手想接。梁库叔叔接起电话,手机里传来呼呼啦啦的风声。
“球往东飞了……这儿很高,什么都看不见。”爸爸的声音被风声扯得断断续续的。
“河悦呢?”梁库叔叔问。
“在。”
“球飞了多高?”
“五六十米有了。”
“稳住,把安全气阀打开,想办法让球降下来,抓住树尖下来。还有多少电量?”
“百分之二十。”
“关机保存电量,落地发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