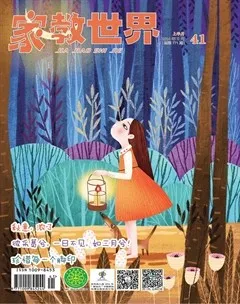儿童“全阅读”的时代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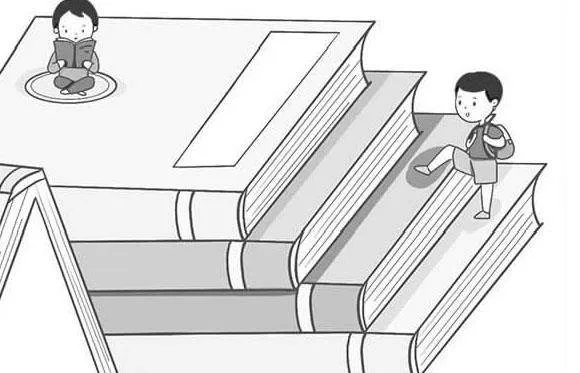

不论电子媒介还是人工智能,都不会终结阅读的时代,却将改写既有的阅读观念与形态。
在可以看得到的未来,儿童的阅读活动会以两种基本形态存在。一是传统的书籍阅读。相比于电子媒介,纸质书籍是技术上更为基础也更具稳定性的一种阅读媒介。当一本油墨印刷的图书摆在孩子面前,不需要经过电源、芯片、屏幕等任何中介,只凭借可从自然获取的光线以及最原始的人体肌肉动作,孩子就能翻看它。阅读者与其阅读的书籍之间建立起的这种未经太多技术中介稀释的归属感与稳定感,很可能带来纸质书阅读不可替代的一种愉悦,也是纸质阅读在电子媒介时代仍然充满魅力的原因之一。当然,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突破,儿童的书籍阅读也可能越来越多地延伸至电子媒介平台,即以高度还原纸质书形态的电子书取代传统的纸质书。这种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并无根本性的区别。
儿童阅读的第二种形态,我们称之为“全阅读”。“全阅读”主张面向一切文本的广泛阅读,是一种值得倡导的阅读观念与实践。除了图书,现实生活中还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本”:广告牌、宣传单、各种各样的介绍与说明,包括当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各类电子屏幕上的文字……一个真正的阅读者不是关在书斋里的书虫,而是能够将从书籍阅读中培育出来的独特敏锐施加到生活里的所有文本中,由此更全面、完整、成熟地理解它们,进而更好地掌控环境和自我。这种“全阅读”的观念与实践,一方面将促使儿童时代的阅读向着更广泛的阅读文本打开视野,另一方面也会促使人们更进一步关注儿童阅读素养的重要性。
应该看到,长期以来在儿童阅读的话题上,公众的注意力往往更多地放在阅读材料的质量水准之上。人们普遍认为,儿童图书的优劣决定了儿童阅读的福利,通过严控图书文本的质量,才能保障儿童阅读的权益。
但在儿童阅读活动的考量中,文本质量只是关键之一,阅读素养是另一关键所在。在当前的阅读环境中,即便是范围并不宽广、经过精心编辑的纸质书籍,从严格的教育价值来衡量,我们也远不能保证每一份儿童阅读材料的可靠性。基于这一考虑,我们曾经提出“对‘批判的儿童’的期待”,“引导孩子从批评的视角阅读一本书,学着发现这本书的优点,也能读出它的缺点,并对此做出恰当的回应”。这一“批判的读者”观可以进一步拓展到儿童面对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文化文本层面。教孩子如何以批判的阅读姿态面对一本书,也教他们如何以这一姿态面对其他广义的“文本”,这是未来儿童阅读素养的重要拓展,也是新的时代和生活向儿童阅读提出的要求。
今天,尼尔·波兹曼所说的传统童年的“符号环境”正在不断消解,依照当今电子媒介的发展速度,对儿童而言,传统的信息世界将来一定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失控”。与其任由孩子身陷这一失控的混乱中,不如在努力探索和建立新秩序的同时,把读懂一切信息文本的有效方法和路径交到孩子手中,给他们一种对文本的批判、反思能力,提升儿童的阅读素养,在关切到未来的视野中,这样的“阅读”将能使儿童获得新的生长力量。
这意味着,对电子媒介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儿童来说,阅读素养的培育可能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那么,一种可靠的儿童阅读素养从何而来?至少迄今为止,它最重要的基点仍然是书籍阅读。通过与书本的交往,感受阅读感性与理性的深切愉悦,学习阅读分辨与判断的重要技能,理解作为人类文化的独特价值与复杂表征的文字、图像以及其他一切符号,懂得领受审美世界的奥义,也有勇气和见识冲破伪审美话语的桎梏。经过这个过程,培养出来的阅读素养,将成为儿童在日益复杂的当代生活环境中实践“全阅读”的可靠起点,也将是他们在当代媒介和技术加速时代确认和建构自我的稳固基石。就此而言,纸质阅读在未来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