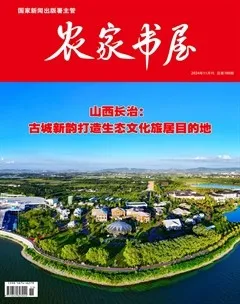神游华北联大

殷杰先生给我送来一部书稿,说我一定会有兴趣看的。
我一看书名《流动的大学:华北联大 1939—1948》,这“华北联大”几个字确实让我兴奋不已。七十六年前,我曾在华北联大上学,那时我才二十多岁,那段经历让人难忘。
抗战胜利后,我一直住在辛集(那时叫束鹿)。冀中十一分区的司政两部,就驻扎在胡合营的道北大院里。那时,我们正忙于反内战的文艺宣传活动。
一天,分区大院忽地喜气洋洋,操场上在搭戏台了。我们前线剧社从不敢在分区大院逞威风,“什么人敢来这里演戏呢?”于是,很快传来消息:要来的是联大文工团。他们刚从张家口撤来,为保密起见,联大不叫“联大”,对外叫作“平原宣教团”。
这不啻在院里放了一颗炸弹。联大文工团,在我们小小剧社的眼里,就是一座辉煌的艺术宫殿啊!
演出进行了两个晚上。第一晚净是歌舞小戏,《夫妻识字》《小姑贤》便在此时相识。记得突出的观感有两点:一是台上的人年纪都挺大,女同志穿一身毛蓝布棉袄裤,棉布帽子掩着两只耳朵,捂得一张脸只剩碗口大,留着鼻子、眼睛、嘴巴勉强能活动就算了。二是他们的歌声整齐洪亮,仿佛人人都有一副好嗓子,指挥的手势一点,声音“呼嗵”一下就像从炮筒子里打出来似的,然而听起来却又土又愣,怪味十足。后来,人们就把这股怪味叫作“山杠子味儿”。然而,说来也怪,第二日白天,整个分区大院便到处充满了这种“山杠子味儿”的歌声,年轻的、年老的,男的、女的,一张嘴就是“手榴弹呀么吼——嗨”或者“山药蛋呀么哪呀哈……”专意模仿那土愣腔调,一时竟成了时髦……
第二晚演的是全本《白毛女》。这一晚的《白毛女》确实把人“镇”了。歌唱家孟于扮演“喜儿”,她的唱腔优美高昂,激情迸发,一句“我不死,我要活!——”真如长虹喷空,全场震悚,至今还觉荡气回肠。饰“杨白劳”的是牧虹,这角色大约一开始就归他演,全是驾轻就熟,尤其是喝了卤水以后的大段“舞蹈”,把悲痛凄绝的情感发挥到了极致。陈强演的“黄世仁”不必说了,他把两个冷眼珠子一拧,立刻使你脊梁沟子发凉,如果不在最后“枪毙”他,人们怎能饶得过呢?饰“穆仁智”的那位,我把他名字忘记了,真可惜。他在《小姑贤》中也演了个角色,秧歌扭得极有风致。此人演戏讲究含蓄,动作表情幅度不大,却把“穆仁智”的奸险卑劣尽含在轻言巧笑之中,韵味深沉耐久。最风光的成功要数演“王大婶”的邸力(人都叫她阿邸),她出场一笑,便赢来满堂热烈的掌声。不知什么缘故,这一次,郭兰英和王昆都没有亮相。
但是,我们小小的前线剧社还是疯魔了。此后十多天,分区政治部作出决定: 把剧社全体拉到联大去,去受几个月训,以便在素质上有个显著提高。这个决定立即受到普遍一致的欢迎,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前线剧社拉进了联大文艺学院,与文工团驻一个村,就由他们具体辅导我们。每日一早,便有陈强、桑夫、吴坚几个人,带我们扭陕北秧歌。他们从察北来,早晨习惯穿厚棉袄、皮背心,两三圈扭过,就不免口喷白雾、汗流浃背了,于是就扒掉棉袄背心,顶着一头汗在排头位置上更扭个生龙活虎。他们被傅作义穷追千八百里,现在喘息甫定,居然还有这么大精气神儿,我们都觉得奇怪。
我在剧社创作组任副组长,其实是瞎混,除了能写两刷子,戏、音、美等一概不行。在人手不够的时候,我虽也跑跑“龙套”,但兴趣未曾在舞台上。
有一天闲遛,我碰到了文学系的学生——活跃人物陈淼。我问他,文学系是学什么的?他十分夸耀地把情况一介绍,立即就把我“抓住了 ”。
那时,我已有本自己作品的剪贴簿——贴着我发表在各小报上的战斗通讯、故事轶闻之类,篇幅多在三四千字之间。我就是凭着这本簿子,通过文学系主任陈企霞的“考试”,做了文学系的插班生。
1947 年 2 月的某一天,我背着小背包,穿着剧社发的带马裤插兜的军装,惴惴地走进了一家农户的大门 —— 到文学系第一学习小组报到。雅静大方的老大姐组长周延接待了我,小组成员还有白石、黄山、叶星、肖雷等人。那时候,我已享受营级干部待遇,却兴致勃勃地跑到这儿当起“兵”来了。
在联大,印象最深刻的仿佛并非读书上课,而是课外活动,是校园(如果存在校园的话)内外的大天地。我进文学系刚及一个月,便赶上全系分散,深入生活:大部分同学到各村采风去了,另有十多人因石家庄的国民党军不断向我区骚扰,藁城、正定、获鹿一带战斗频繁,便由教员蔡其矫(诗人)带领深入西部前线,分在各部队采访、体验、学习、锻炼。因我来自部队,理所当然地分在了这个组。
半月过去,同学们都尝了尝战争的滋味,有参与支援前线的,有和民兵一起埋地雷、割电线的,有访问战斗英雄的,也有直接参加战斗的。大家重聚在一起的时候,个个激情满怀,兴奋异常。蔡其矫那时也是个青年,听了各路人马的汇报,不禁眉飞色舞,激发了诗人气质,大放豪言说:“好!我们回去把事迹集中起来,写它一部《新水浒》吧。”可是,写《新水浒》,谈何容易啊!
下部队参战的事,以后还有多次,值得捎带一提的是贺敬之,他此后不久即参加了青沧战役,并与突击部队一起登上了城头。作战部队觉得,一位写过《白毛女》的作家,能与战士一起冒死爬城,精神可嘉,便写信来校替他请功。年底,全校搞“立功”运动总结,他果然因此立了一功。我那年曾发表短篇小说《周玉章》,因编辑萧殷加按语表扬了几句,也立了一功。但我这一功若与贺敬之的火线登城相比,实在是太便宜了。
至于下乡、劳动、土改、搞群众工作都是日常功课,联系群众的观念是极其明确的。平时与房东、与民众的交往,不只为搞好关系,也与业务血肉相连,向群众学民歌,录曲谱,听故事,收集语汇、剪纸、绣花样子……不论文、美、戏、音,各系皆成风气。文学系的墙报《文学新兵》(创刊时名《草叶》,第五期时更名)上发了李兴华的短篇《红线缘》,从形式、语言到内容都是地道民间风味,立即受到文学系师生的交口称赞。我曾把一段民间故事《县官和他的仆人们》拿到文学系的晚会上去说,不料大受欢迎,又被推荐到文艺学院晚会上去讲。当我再次讲完时,掌声还在其次,诗人艾青(文艺学院副院长)特别找到我说: “听了你的故事很感动,能不能把稿子抄给我一份?”可见,当时对民间艺术的追求,从上到下,充满了何等热情,绝不像而今的某些人一提民族的、民间的,则是嘴角一撇 —— 满脸不屑的样子。
我做了八个月插班生,便在文学系毕业了。论起收获来,也许正是这些耳濡目染的方方面面,给了我更为深刻的熏陶和影响。当然,课堂上(其实是农民的院子里)的教育,也是绝不能轻视的。战争年代,根据地环境虽然限制了联大的设备条件和教学手段,但也正由于此更显示了学校教学水平和作风的非同凡响。
陈企霞是文学系主任,他相貌瘦削,为人严肃,平时很难接近。可是,我日后的命运,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他“纠缠”在一起,“大倒其霉”。在当时,文学系同学却是普遍尊敬并喜欢他的。他虽严肃板正,却学识渊博,性情耿直,具有诗人气质:爱红脸,爱发脾气,也爱开怀大笑,在我们前线剧社演《抓俘虏》那个晚会上坐在前排,笑声冒得最高最响的就是他。他的课是“作品分析”,往往先选出一篇小说,油印后发下来,大家阅过后便在小组里展开讨论,然后课代表把情况向他汇报,他再在课堂上作结论性分析讲解。这么做的好处是:很实际,针对性强,讲师与学生间可以短距离“交锋”,解决问题直接、便当;而他的结论,常是服人而精当的。有一次,他发下一篇孔厥的《苦人儿》,小说用第一人称叙述一个女人的经历,结构顺畅而自然。可有的同学在讨论时说:“这算什么小说?一个人的诉苦记录罢了。”陈企霞在课堂上先把小说的长处和特点分析了,然后面孔板得铁冷地质问那位同学,弄得那位同学很不好意思。
就我个人来说,最觉得益的算来是萧殷的“创作方法论”。 我是插班生,许多课都赶在“半截腰”上,听得没头没脑。何洛的“文学概论”、欧阳凡海的“现代文学史”、诗人严辰(厂民)的“民间文学”,都是这样的。我文化基础差,读书也少,常常半天半天地坐着发蒙。萧殷不同,他比我来联大还要晚一点,是从《冀中导报》副刊岗位上调来文学系的。此人性情温和慈爱,天生一副奖掖后进的心肠,他生前的几部著作及主要功业都突出地表现着他对初学写作者的尽心培育和热情辅导。我从头听了他的“创作方法论”,后来还做了他的课代表,每堂课下来我都赶忙收集同学的各种反映,然后连同自己的笔记一同拿给他看。他总是专注地听意见,记下要点,再仔细改正我记录上的舛误。实在地说,我对文学创作能有个基本的概括的理解,确是从他开始的。日后,他主编《文艺报》的时候,任广东作协副主席的时候,这份奖掖后进的热衷是一直保持始终的。我奉他为文学园地上的“杰出园丁”,当不是过誉之词吧。
那时,我们也隔三差五地听听大课。所谓“大课”,就是全院各系学生聚在一块儿听。这类课,规格总是高些,通常以政治课或文化课居多,如张如心的“毛泽东思想”、俞林的“中国革命史”、于力(董鲁安)的“修辞学”,等等。俞林是河间人,本来是位作家,写过很著名的中篇《老赵下乡》。他还有很不错的外语修养,在专与国民党谈判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我方)工作过。可是,他讲起革命史来,也非常绮丽多彩。每当听他讲课,我都不期而然地有八个字升上脑际来形容他 —— “口若悬河 , 滔滔不绝”,一连四个小时,你是绝不会走神儿或打盹儿的……
最后,感谢《流动的大学:华北联大 1939—1948》的作者张在军先生,以翔实的史料、朴素的文字和真挚的情感,再现了华北联大九年的办学历程,也再次引发了我对华北联大的美好回忆。张先生书稿中的好多史料是我所不知道的,作为一个“联大人”尚且如此,可见这些年来人们对华北联大的研究是不够的。
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华北联大在党的关怀下诞生,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同时,讲好党办大学的故事,可以激励后辈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张在军先生与华北联大本无瓜葛,完全靠个人的自发行为进行研究写作,收集资料,辨析疑难,花费很大气力和时光,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工程,令人感佩。三十年前,我与朋友一同去辛集访旧,写过一篇《神游故校》。这次,我便把它略加删改,权充“序言”了。
遥想当年的华北联大生活,真有物换星移之感!今年我已经九十八岁了,最难忘的还是在华北联大的美好时光。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想把那段生活再重新过上一遍呢。
(来源:现代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