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啄木鸟》一起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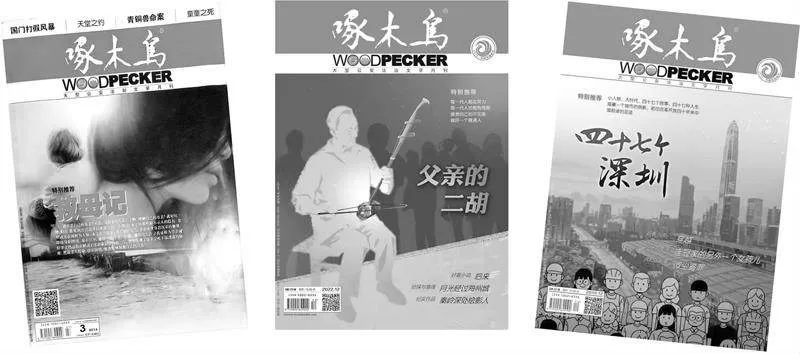
我最早接触《啄木鸟》是在高中,记得有一篇追捕“二王”的纪实文学作品,忘了谁带到班里的,反正几乎传遍了全班,既好看,又满足了我们对文学的追崇(我们是文科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回到小县城,图书馆依然是我常去的地方。最常看的杂志除了《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还有就是《啄木鸟》。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写作,阅读很纯粹,就是喜欢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无意中,也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我是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的。小县城的写作者,没有任何文学方面的人脉,发表只能靠盲投。前几年一直没敢投《啄木鸟》,主要是因为心理定势,《啄木鸟》太高大上,我是文学新兵,距离太远。几年之后,我写了《谁是第五个》,想着好歹也算与案件有关,照着杂志社的公共信箱投过去,没想到回复这么快。责编杨桂峰老师就细节、逻辑提了些意见,我修改后发在了2012年9月的《啄木鸟》上。
之后就顺畅多了,几乎每年都有一篇小说登上《啄木鸟》。河南文学界好几个文友都说,《啄木鸟》很看重我。的确。
有一次写作的间隙与杨桂峰老师聊天,她说那几天她一直在读长篇小说,头昏脑涨,也没遇到让人为之一振的好文本。其时,我的第一部长篇正在修改中,随口说了句,但愿自己的这部长篇不会让编辑“头昏脑涨”。我没敢奢望长篇能上《啄木鸟》,我知道文学刊物版面紧俏,甚至没敢想能拿出去发表。说实话,创作之前我志向远大,但实际创作中才体会到长篇的不易,结构、语言、故事,与中短篇大有不同。杨老师却充满了期待,嘱咐我慢慢写,不要急。
某日下班路上接到杨老师电话,说她也正在下班回去的路上,稿子刚看完,很激动,比预想的要好。创作者的激动也随之被激发。杨老师又说,对话再打磨打磨,争取能改编成影视剧。还有小说题目(最初叫《水殇》)不太理想,再想想,咱们一起想……
杨老师很快发来了她特地收集的一些经典影视剧对话供我参考。每当有了新的思路,比如不同性格之间的碰撞、结尾如何更加艺术化等,杨老师都会当即给我打电话。我们最长的一次通话接近一个小时,最晚的一次通话是在晚上十点以后——好像就是那个晚上,杨老师提出了《救母记》这一带有救赎意味的题目。某种程度上说,2014年3、4两期连载的《救母记》更像是我和杨主编共同的创作。2019年10月,时值《啄木鸟》创刊35周年,《啄木鸟》微信公众号发起“1984-2019年我最喜爱的精品佳作”投票活动,《救母记》从长篇组中胜出。
如果说《救母记》是靠实力挤上《啄木鸟》的话,长篇非虚构作品《四十七个深圳》则是《啄木鸟》在雕琢一个作家。《四十七个深圳》入选了中国作协2018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按我的理解,它应该与《啄木鸟》的办刊思路无关。看完稿子,杨桂峰主编说,《啄木鸟》立足公安题材,但好的叙事文本都属于刊物的范畴。杨主编还说,《啄木鸟》对你寄予厚望——作家充实刊物,刊物也应该有意识地扶助作家。
创作《嗷吼》时我没有规划,信马由缰地写,成稿七万多字,很尴尬,长篇太短,中篇又太长。创作时正是疫情初期,现实中和网络里,撕裂——国内的、国际的、亲情的、价值观的——随处可见,我也像大家一样焦虑不安。奇怪的是,真正投入创作后,我像是从疫情中完全脱离了出来,安定下来。小说中的代建平回望自己的过往时,我也跟着他停下来细细反思自己——对名利的追逐、虚荣的自大……疫情之下,当然也有忏悔,有对未来的规划。从这个意义上看,疫情与小说,形成了相互映照。很多人物像是从我的笔记本上被激活,他们渐渐丰满有血有肉之前都只是扁平的线条,但创作中,他们仿佛一直在我面前晃动。
小说发表在2021年11月的《啄木鸟》上,发表稿虽被删节了一万多字,但更为精炼,笔墨集中到了人物的内心上,小说的张力更大了。一位一直关注我创作的中文系教授也发现了这个改变,他说《嗷吼》跟我之前的世情百态小说比,明显更侧重于人物内心的挖掘。
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父亲的二胡》距第一部《救母记》已有八年。八年里,杨主编不断提醒我,应该准备好写更大的作品。也不是没有选题,小县城的作家其实比大城市的作家更有生活。但我变得患得患失,像备孕的妇女,要求情绪饱满的同时,调理饮食、补充叶酸、强健身体,生怕产下的宝宝有异常。好多小说的种子就这样在素材本里存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它有异质吗?有意义吗?是我真正想写的作品吗……
《父亲的二胡》是其中的幸存者。作为小县城中学教员,没有俯瞰世界的站位,信息也不对称,之前写大时代大家族大事件的心劲渐渐淡下去。我正知非之年,回望半生,感觉自己曾经那么无知、可笑。好在还未到而立之年的儿子已经有了自觉,当他说到计划购买婚姻方面的学习课程时,我真是又惊又喜。这是代际的进步,也是教育、文化素养的结果。三年疫情,焦虑与撕裂反而鼓励了我。于是,我分割成了无数人物,余大志、苏仁秀、刘雪瑞、丁富昌……责编在电话里说到杨主编的审读意见,也顺带分析了一下主人公余大志,他对父母不满意,对妻子不满意,对儿子不满意,其实他不满意的是他自己……我立时怔在那儿,责编的话让我醍醐灌顶:余大志的每一步成长其实都是建立在对自己不满意的基础上。换句话说,那是他前进的动力。
刊物的封面也做得别具匠心,推荐语是: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每一代人也都有局限,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做好一个普通人。不愧为编辑,几句话就提炼出小说的主题,余大志这个人物形象愈加清晰了。做好一个人,不是做一个好人。好人有外界的希冀,有明确的标准,但“人”更宽泛,抽去了外界的定义与约束,自己心仪的“人”,自己满意的“人”,普通人。做好一个人,学会爱,学会接受自己。
2024年是《啄木鸟》创利40周年,《啄木鸟》又赶在教师节前夕连载了我聚焦教育的长篇小说《号声响彻云霄》。责编肯定了小说力求从教育辐射县城各领域的雄心,刊首的导读语中写道:“半生执教的张运涛以一个教师的职业生涯为脉络,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体制、教育方式的变革,同时也以一个教师的视角旁观芸芸世间,呈现时代洪流中各色人等的悲欢离合。”责编微信里委婉表达出的缺憾,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警示着我未来的创作。
几十年来,《啄木鸟》不仅提高了我的阅读兴趣,也为我提供了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为我的创作储备了宝贵的文学经验。我们相互见证了各自的成长。希望未来的岁月里,我仍然能够与《啄木鸟》一起成长。
责任编辑/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