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在进步,艺术在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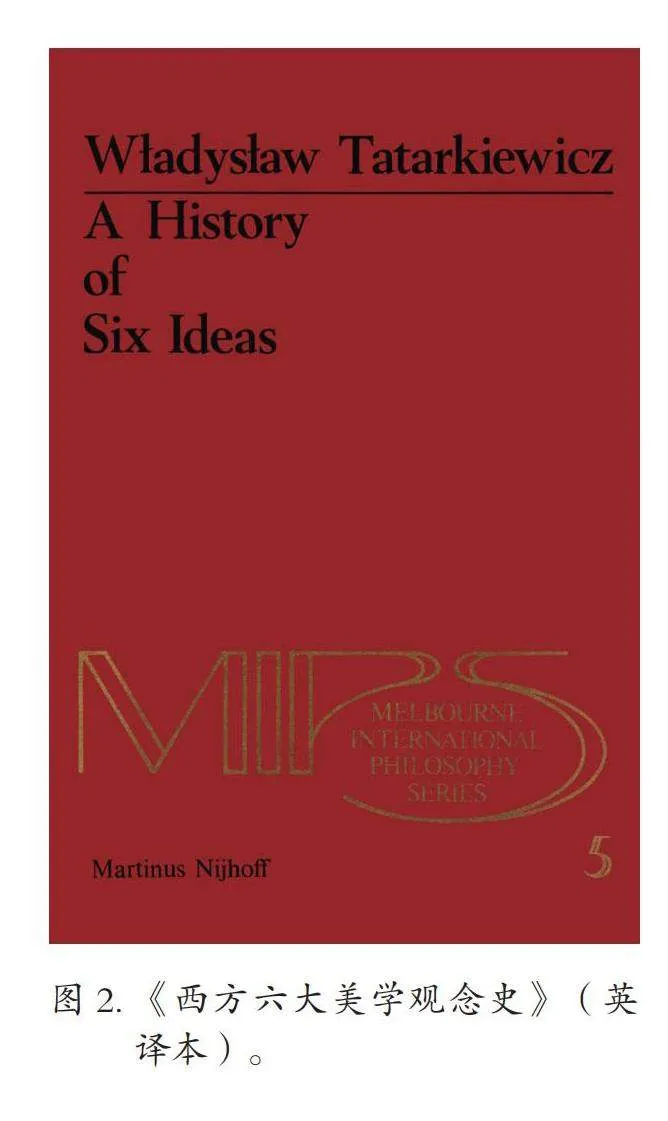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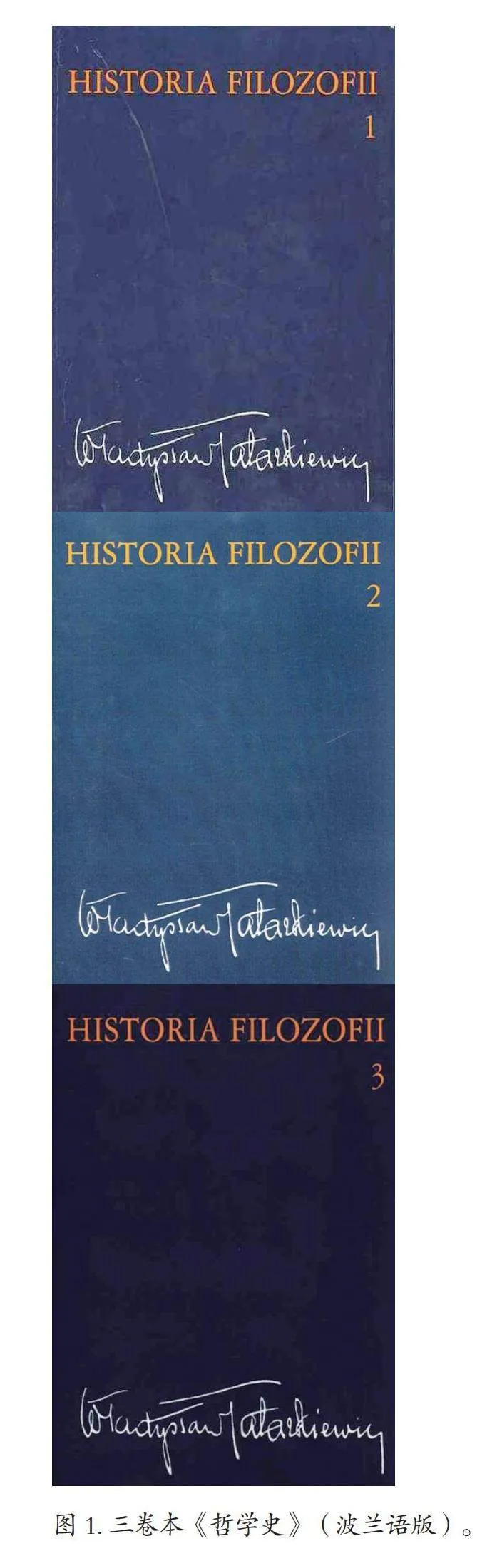
本文为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历史主义美学视域下太行精神文艺阐释研究”(项目编号:2023YJ115)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齐飞,文艺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比较文学、游戏研究。
摘 要 塔塔尔凯维奇的美学观与艺术观可以用“美学在进步,艺术在改变”来概括。“美学在进步”意味着在塔氏那里有着基础地位的“古典理论”的不断深化;“艺术在改变”是塔氏在面对多变的艺术样态时作出的一种具有相对性的总体概括。本文将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对塔氏的美学观与艺术观进行探讨,进一步分析塔氏美学思想中“美学本质主义与艺术自由主义”的折衷立场及其表现,并指出这种立场对于认识美学和艺术相关问题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塔塔尔凯维奇;美学观;艺术观;折衷立场
Abstract: Tatarkiewicz’s aesthetic view can be summarized as “aesthetics has progressed and arts change”. The view of “aesthetics has progressed” means the deepening of the “classical theory” which has a basic position for Tatarkiewicz. And the view of “arts change” is a relative generalization made by Tatarkiewicz in the face of changeable artistic forms. From these two angle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atarkiewicz’s aesthetic view and artistic view, further analyze his eclectic position of “aesthetic essentialism and artistic liberalism”, and point out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is position for understanding aesthetics and arts.
Keywords: Tatarkiewicz; aesthetic view; artistic view; eclectic position
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Władysław Tatarkiewicz)是波兰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艺术史家、美学家和伦理学家。1910年,塔塔尔凯维奇(后文称“塔氏”)从马堡大学博士毕业,并开始了自己的学术之路。他的著作,如三卷本《哲学史》(图1)、伦理学著作《幸福分析》以及三卷本《美学史》等在西方均产生一定影响。晚年写就的《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是塔氏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他对于美学当中诸多观念性问题的深刻思考,此书在中西方美学、艺术学界反响较大,并且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他的美学观与艺术观。通常认为,塔氏是一位中规中矩的传统学者,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在“古典理论”在塔氏那里的重要地位。笔者曾撰文指出,古典理论对于塔氏的美学思想而言是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的,具有“参照系”的作用。[1]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典理论就是铁板一块。恰恰相反,沿着古典理论这条脉络,可以发现塔氏美学思想中十分丰富的内涵。他对于美学、审美和艺术这些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都有过详细论述,在这些论述中,“美学在进步,艺术在改变”是塔氏在剖析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的总结,是塔氏美学、艺术观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同时成为他多元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新的艺术形态不断涌现,媒介和传播方式也在发生着深刻变革,这些变革不仅更新着艺术的定义,改变着艺术的边界,甚至影响了人们看待艺术的方式以及欣赏艺术时的体验。塔氏所秉持的折衷立场,其形成和发展同先锋派艺术密切相关,尽管距今已有时日,但这种立场在寻求艺术与美兼顾融合的同时亦有所侧重和突出,仍旧能够为当下美学与艺术学相关问题的研究、认识艺术中的现象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一、“美学在进步”——古典理论的稳固深化
在《美的伟大理论及其衰落》一文里,塔氏论述了美的发展历程。一开始,“希腊人对美的概念比我们更广泛,不仅延伸到美丽的事物、形状、颜色和声音,还延伸到美丽的思想和习俗”。[2]在柏拉图那里,美和善经常被混合起来使用。然而,在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派那里,有一种关于美的主观主义理论,认为美依赖于耳目的愉悦,美和善在他们那里产生了区别。不过,美的模糊性并未就此消失。在普罗提诺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诸如“美的科学”和“美的品德”这样的用词,美在他那里具有和在柏拉图那里相似的双重含义。此外,再考虑到古希腊人使用的和美相关的一些用词,如对称与和谐,以及中世纪、文艺复兴对于美的不同用法,塔氏把古典理论中关于美的概念归结为三点:1. 广义的美:道德伦理、美学意义上的美;2. 纯粹审美意义上的美,包括一切唤起人的美感的事物的美;3. 同样是审美意义上的,但仅限于视觉产生的美。[3]
在《美学进步了吗?》一文中,塔氏的观点也大致相同:
1.美的概念:作为古典理论的两个基础概念之一,美的概念是十分宽泛的。“美”这个词和“善”“有价值”几乎是同义的;一切善的东西,倘若它们可以吸引人、令人愉悦,则都可以被称作美的。
2.美在于各部分的比例。同义词还有“和谐”与对称。
3.美还有另外一个基础:它可以是某个事物达成目的的恰当性、充分性,以及合适。
4.美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不仅仅是人们对事物的主观反应。对称性和适用性就是这样的属性。
5.美是通过感觉和心灵来理解的。心灵的功能不仅在于理解精神上的美,还在于感官上的美。
6. 美不仅存在于艺术中,还存在于自然中,然而,它首先,而且在最高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的属性。[4]
在这些关于美的理论中,影响比较持久的是毕达哥拉斯开创的关于“数”的理论。这个理论直接衍生出的秩序、比例、和谐、对称等概念影响了西方理论界足够长的时间。中世纪,人们对于美的认知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奥古斯丁就曾说,“美是因形态悦目,形态因比例悦目,比例则因数而悦目”。[5]尽管后来的阿奎那、费奇诺等人对这个理论之外的情况有过说明,但总的来说只不过是为这种“美的伟大理论”添砖加瓦而已,其基础仍旧是对于古典理论的遵循。文艺复兴时期,古典观念仍旧根深蒂固,但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是一种伟大的善。
2.美是由适当的比例以及和谐的部分构成。伟大的雕塑家吉尔伯蒂说,“恰当的比例是构成美的唯一要素。”
3.美还可能来自适当的、恰当的形式和比例,而不仅仅来自绝对完美的形式和比例。
4.美是事物的客观属性;它来自自身。
5.美是由心灵获得的,而不仅仅是由感官获得。米开朗基罗说,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6.最高程度的美存在于自然之后,她的美胜过艺术之美。“艺术无法和自然匹敌。”[6]
如果从美的理论上来看,塔氏对于古典时代的观点仍然是比较纯粹的,即“美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非主观经验的投射”。[7]事实上,对于这个时代,人们更多的是对这种“纯粹”美学样态的概括。比如,鲍桑葵把古希腊美学原则归结为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和审美原则。从道德原则来看,“艺术上的再现在内容方面,必须按照和实际生活一样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形而上学的原则体现在“艺术乃是第二自然,只不过它是自然不完备的复制品”;审美原则中,“美纯粹是形式的”。[8]朱光潜先生也在《西方美学史》中认为,当时美学的主要问题“就是文艺的现实基础和文艺的社会功用”。[9]
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开始,美的问题逐渐摆脱了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探讨,变成了人的感性认识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塔氏的观点和主流观点大致无二。他认为,我们可以在艾迪生、哈奇生、休谟等人的美学著作中发现这种变化的端倪。同样是从18世纪开始,情况变得复杂了,美作为艺术评判标准的地位受到质疑,美的概念也受到冲击,“古典主义”这条美学的高速路逐渐消失。“古典艺术形成了伟大理论的基础,而伟大理论由于难以与当时的趋势相一致而变得无关紧要。”[10]这种趋势很明显就是浪漫主义,美学的进路正是在这个时候变得越来越多元。诚如塔氏所说:“古典主义的价值范畴,主要在于美,而浪漫主义的价值范畴,主要不是在于美,而是在于伟大、深刻、宏伟、高贵与丰富的灵感”,因而浪漫主义所代表的美可以视作“广义之美”。[11]伟大的美的理论也随着这股思潮的发展而逐渐式微,塔氏将这个过程称为“伟大的理论的危机”。美学中的大传统逐步加速让位于一个又一个的小传统,美学理论也从一条大路逐渐分解为各种小路。而要理解这一条条小路,不结合艺术的发展是无法完成的,接下来重点要谈的是塔氏对于艺术问题的看法。
二、“艺术在改变”——一种相对性的表达
对于艺术问题,塔氏的基本观点是“艺术在改变”。这一观点的形成是塔氏对艺术问题认识逐渐深化的结果。起初,塔氏是相信艺术和美都是有一种绝对的客观价值的。但随着美学研究的逐渐深入,他越来越感觉到,美学是一种具有很强主观倾向和个人意义的学科。艺术问题在原则上又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艺术理论,另一个是艺术实践,以及和艺术实践密切相关的艺术概念。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看法集中形成了塔氏具有相对性的艺术观点。
艺术理论的发展和美的理论的发展一样,它们都深深地扎根在古典理论之中。如塔氏所说,“艺术理论的确在进步,因为它们的概念更加清晰,命题变得更加丰富。艺术理论进步了,却没有改变,它的那些重要命题从西方文明的早期就已为人所知。它发生变化只不过是那些主要观点变成了例外,例外的观点变成了主要观点而已。”[12]在塔氏看来,艺术理论的变化是局部的。在《什么是艺术?当今的定义问题》一文中,塔氏指出,“艺术的概念在理论上是固定的”,这呼应了前面的观点。但紧接着他说:“艺术的概念在实践中却十分不稳定。决定什么是艺术品,什么不是艺术品的标准很多,而且都比较不稳定。”[13]在前半句话里,塔氏试图说明,艺术理论的发展是有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的。从艺术作为技术,到艺术内部种类的分化,再到由“美”统一在一起,这个时候艺术从概念上讲还是比较稳定的。但后半句话的意思是:随着新的艺术样态不断出现,艺术在概念上呈现出复杂的一面。塔氏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并没有比埃斯库罗斯和荷马优秀多少;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也并不比希腊雕塑完美;伦勃朗也并不比凡·艾克更伟大。艺术家是不同的,艺术也有不同的风格和形式。它们在改变,而且经常在改变。它们在改变,但没有进步。”[14]
这些矛盾形成了艺术十分复杂而多变的定义,它们本身充满了相对性:艺术时而是美的代名词,时而是对现实的再现,时而是形式的创造,时而是某种显著特征的表达,或者是产生一种审美体验,抑或对人的情绪的冲击。这种含义的不确定性让我们谈到艺术的时候不是过于宽泛,就是过于狭窄,难以为艺术找到一个固定的含义。因此,塔氏采取了一种对艺术的宽容立场。在他看来,我们面对这种多样性,最好的方法是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艺术概念,不排除功利主义以及物质与艺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我们面对现代艺术的商业化倾向的时候,这种立场尤为重要。塔氏总结道:“今天艺术概念的拓展比起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宽泛……我们对艺术的定义也必须涵盖这个广泛而多样化的领域。”[15]的确,对于现代艺术而言,由于自身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评价艺术作品的标准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将艺术局限在“美”的范畴,或者完全把艺术框定在审美的框架里似乎都不足以解释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了。
和许多哲学家一样,塔氏始终认为定义和概念是认识世界的最佳方式,对于艺术问题也是如此。他充分认识到了给艺术下定义的巨大难度,但他并没有停止尝试。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样巨大的难度,让塔氏采取了一种相对折衷的办法:一方面对艺术抱有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不放弃定义艺术的尝试。在这里,塔氏同时借鉴了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对艺术的看法。在20世纪以前,对于艺术的定义还倾向于本质主义。康德认为,“我们出于正当的理由只应当把通过自由而生产,也就是把通过以理性为其行动的基础的某种任意性而进行的生产称之为艺术。”[16]黑格尔的艺术思想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艺术是理想的体现,艺术自身的发展过程就是向其本质不断靠近的过程。车尔尼雪夫斯基立足“美是生活”的观念,认为“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艺术作品常常还有另一个作用——说明生活;它们还有一个作用:对生活现象下判断”。[17]
上述这些本质主义的立场延续了古希腊传统,主张以一种或几种固定的标准对艺术进行分类和评判。后来有很多理论家,如海德格尔、阿瑟·丹托等人对于艺术的分析都或多或少体现出这种立场,即艺术的定义以及艺术品的界定与用一套标准对艺术进行解释密不可分。进入20世纪,反本质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波及到了对于艺术定义的问题上。同时,这也和以追求惊奇效果为目的的当代艺术的大量出现和快速发展脱不开干系。在这些反本质主义者看来,艺术实际上是对社会既有规则的革新与挑战,所有被固定概念所框定的艺术表现形式都应该被打破,不存在固定的规律与章法。在这股潮流中,影响比较大的是美国分析哲学家威茨和美学家肯尼克提出的主张,这种主张也成为他们“取消主义美学”理论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艺术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因此是无法被定义的。威茨就认为,概念应该是开放的,除了在数理逻辑中,或者出于特定目的的考虑之外,概念是不应该被限定的。艺术就属于这种开放的概念,“艺术具有可扩展、大胆创新的特性,它始终存在不断的变化和新奇的创造,这让艺术从逻辑上讲并不具有获得界定属性的可能”。[18]塔氏部分承认这种观点,但仅仅继承了这种开放的态度。艺术的概念对于塔氏来说是相对的,但绝不是虚无的。如果这种相对性的艺术概念的诠释最后被彻底的开放性吞噬,那么就会演化为难以有实际意义的“虚无主义”,这也是“取消主义美学”发展到最后容易遇到的问题。塔氏则克服了这一点,他对艺术抱有开放的态度:他承认艺术概念的开放性和相对性,但明确反对不给艺术下定义的虚无主义态度。尽管他对于定义和概念问题的执着追求在面对艺术的时候似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他并没有和威茨一样,索性不给艺术下定义,而是认为“缺少定义会成为我们更加深入研究艺术的严重障碍”。[19]
“艺术在改变”这一观点后来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后文称“《观念史》”,图2)一书中,塔氏认为艺术是由不同概念集合而成的,当我们给艺术下定义时,“应该考虑到概念的全体”。这里的“全体”是从宽泛意义上讲的。按照塔氏的观点,艺术具有多重性格,这种性格会让艺术的定义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国家和文化之间发生不同的变化。[20]在概念问题上,他认同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维特根斯坦在著作《哲学研究》中探讨了这种“家族相似”的情况,他说:“没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能够使我把一个词用于全体——但这些现象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彼此关联。而正是由于这种或这些关系,我们才把它们全称之为‘语言’。”[21]他随即用游戏举例,认为这种考察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他说:“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型、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22]塔氏从中汲取了经验,认为艺术也应该是一种相似但多样的概念的融合。他认为艺术的概念具有开放性不等于放弃对艺术进行定义的努力和尝试,这是两回事。接下来他便开始了对艺术进行定义的尝试——使用辩证法,这也是塔氏惯用的方式。
塔氏先抛出一个基本的观点:艺术是一种有意识的人类活动(a conscious human activity)。这是塔氏分析的出发点——从一个简单的定义开始。接着他便对这个命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结合艺术的生产、表现、审美体验、价值角度,以及艺术品唤起的效果来对艺术问题进行系统的综合性考察。塔氏发现,无论人们如何定义艺术,最后都会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通常只关注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如果要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就必须采取选言命题的方式,即“或者”的方式,这样才能兼顾艺术的不同维度。最后,塔氏给出了自己尝试作出的艺术和艺术品的定义:
艺术是一种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它或者再现事物,或者构成形式,或者表现经验,这种再现、构成和表现的产物可以激发人的快感、情绪或者令人感到震惊。
艺术品或者是事物的再现,或者是形式的构成,或者是经验的表现——它们都可以激发人们的快感、情绪,或者让人震惊。[23]
塔氏对于艺术的定义和高特提出的“艺术的群体概念”有相似之处。后者认为,艺术的概念是群体概念的集合,这个概念的应用应该有多重的标准,其中并没有一个标准是让“某物成为艺术”的必须具备的条件。他认为,如果一个概念的含义是由群体给出的,那么我们就无法在单独必要条件和联合充分条件的意义上来定义这个概念。[24]这显然是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但塔氏并没有因定义的复杂而回避为艺术作出定义的尝试,无论这种定义如何多样,塔氏仍旧希望把定义限定在能够解释的范围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塔氏在定义艺术和艺术品时使用的是逻辑学中选言命题的方式,在选言命题的方式中,他又采取了相容选言命题的办法,认定反映事物的情况和性质是能够并存的。对于定义艺术来说,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尽可能地呈现出艺术的多元化特征,另一方面也能将艺术同其他“不是艺术”的事物相区分,本身就是一种相对性的方法。孙冰冰、周计武撰文指出,塔氏的析取性定义方式“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又不乏空间去解释和面向新艺术对象的框架”。[25]
《什么是艺术?当今的定义问题》是塔氏先前撰写的一篇论文,发表在1971年的《英国美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上,后来被塔氏几乎原封不动地放入到《观念史》的内容之中。这篇论文构成了《观念史》第一章——《艺术:概念史》的前七个小节。后面的两个小节是对前面理论的深化,第八节论述了定义和理论背后的三种动机以及四种理论前提。这里没有必要再复述书中的内容,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九小节的后半段,塔氏反思了自己对于艺术定义和概念的看法。毕竟,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西方艺术已经发生了许多令人始料未及的变化。这里塔氏论述了先锋派从崛起时被人诟病,到和传统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再到最后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过程。他分析了先锋派差异、极端和反叛的特点,阐述了先锋派的基本立场和主张,但他最为发人深省的论述,还是对当今艺术领域,乃至整个时代的概括:“这个时代大多倾向于反对,它反对博物馆,反对美学,反对艺术的变化中出现特别显要的花样,反对形式,反对以社会性的方式对待艺术,反对艺术家,反对作者的概念,反对艺术品本身,甚至反对‘艺术’这个名称。”[26]
可以看出,塔氏的艺术观体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来源于“艺术”本身作为观念的复杂性。然而,归根结底,如果没有历史的发展,就没有对艺术的阐释,人们只要阐释艺术,就必然要去解决相对性的问题。虽然很多艺术家对艺术的看法是绝对而极端的,但是作为艺术史家,单一的立场无益于解决艺术观念的问题。因而,塔氏的这种相对性的艺术观可以让我们抱有一种全面和发展的态度去看待艺术。这种艺术观也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艺术,并使得我们了解到,在历史上给艺术赋予的那些定义都是在相对性的范围内作出的,这种相对性实际上是历史的常态。正是出于这种相对性,历史学家们把历史划分成一个个不同的时期,对存在于其中的对象给出一个个概念,并试图加以诠释——这种划分是史学家的本能,也是认知事件的必然方式。但塔氏很清楚这样做的局限,正如他在《现代美学》序言里所说的那样:
历史学家进行了这种操作,但他们必须意识到,他们正在对历史进行拆分,柏格森认为,时间之流无法被划分成片段,他的观点当然也适用于历史。一些人希望可以把一个“时段”看作具有统一的、不变的特点的时间片段,历史就驻足其中,他们的愿望注定会落空。因为在时间之中,并不存在这样统一的时间段。即便被划分为片段,时间仍然是流动的,其他学科是这样,美学亦如是。我们的思想很自然地倾向于在事件的流动之中停驻,但科学的反思让我们有义务认识到这一错误,并通过恢复事件的流动性来纠正它。[27]
总的来说,塔氏的艺术观是全面而开放的。作为史学家,他倾向于用历史主义的原则将他所研究的对象置入到历史的动态发展中,艺术及其概念同样如此。他认为,艺术处在历史的河流当中,无论发生什么变化,总会最终融入历史这条永不止息的河流之中。“一条河流遭遇不平的岩层和转动的石头,于是形成漩涡,改变了河床,但是曾几何时,河流又恢复它先前的流向,又直又平地继续向前流去。”[28]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赫拉克利特“万物皆流”的观点——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如塔氏所言,“历史告诉我们每件事都会变化,因为我们有理由假定,对于变化的需求,尽管在今天是如此之鲜活,但是迟早也会成为过去……然而揆诸实际,迄至目前,它(急进型实验)还并没有穷尽”。[29]虽然塔氏对于艺术的变化持有乐观的态度,但我们在他反思的字里行间,同样体会到了他的震惊。我们很难想象,像塔氏这样的传统学者在面对先锋派绘画时受到的震撼:作为有着十分深厚的哲学、美学和艺术修养的人来说,很多艺术作品在他看来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种对传统的反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并非无法说通,毕竟,艺术的发展过程从来不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模式来进行的。
而让塔氏更加迷惑的是,现代的绘画让自古以来建立起来的艺术概念和定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松动,它充满了自由、不羁以及对传统的背离,它摆脱了两千多年来施加于其身的枷锁的束缚,突破了既定的精英边界,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塔氏先前对于艺术和艺术品的定义已经考虑得比较全面,该定义也已超出以往艺术和美之间一度牢固的关联,考虑到了现代艺术中令人震撼的那种类似于“崇高”的审美体验。但如果我们审视后现代的艺术,会发现上述艺术定义的有效性仍然令人怀疑:后现代的艺术不会引起人的任何感觉,在后现代艺术中,我们似乎什么都找不到,那些转向观念的艺术最终走向了彻底的反美学,“它”没有美、没有丑、没有感觉、没有任何美学品质。[30]对此,塔氏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新奇的时代里,难道说这种追求永远没有尽头吗?”[31]这是塔氏的疑问、我们的疑问,或许也是这个时代的艺术的疑问。
三、美学本质主义与艺术自由主义的折衷立场
通过对“美学在进步,艺术在改变”及其内涵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塔氏美学观中的折衷立场。如前文提到的,绝对的客观价值让塔氏在进行美学和艺术研究初期,把自己的价值论加于艺术之上,认为有一些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他一度坚定地认为这种绝对的价值存在于艺术作品之中,甚至批判美学中存在的主观倾向。对于美学而言,这种对于绝对价值的坚持表现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即相信古典主义本身的永恒价值。但随着他对于美学和艺术问题理解的不断深入以及分析哲学对他影响的逐渐加深,他越来越发现这种“激进的审美客观主义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解决方案”,从而“倾向于将关系主义作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中间立场”。[32]尽管哲学中许多形而上学的因素在美学中依旧存在,但在塔氏看来,美学和艺术的问题有许多是和个人以及现实层面密切相关的。他认为,美学是一种具有很强主观倾向和个人意义的学科,这种“主观倾向”和“个人意义”就是让塔氏“激进的审美客观主义”松动的原因。而在美学艺术观上,他的折衷立场则具体表现为一种美学本质主义与艺术自由主义的交融态度。
塔氏美学本质主义立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来源。首先,塔氏美学本质主义的立场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他一直坚持甚至偏重的“古典理论”。从《回忆录》中可知,塔氏的祖父是艺术家,酷爱绘画和雕塑,家人们喜欢收藏各种古典主义艺术品,塔氏几乎是在这些艺术作品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这段经历让他形成了对艺术敏锐的感知力,也让塔氏相信应该存在着一种古典的、永恒的美,这种观念让塔氏将古典理论称为“伟大的理论”。古典理论不仅成为塔氏从历史主义角度进行美学和艺术分析的基础和起点,也成为塔氏美学思想中本质主义立场的重要理论来源。古典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塔氏对于价值问题本身的看法。对于塔氏而言,美的价值本身就具有绝对、客观的一面,他甚至曾明确表明自己反对完全主观主义的认知,客观价值才是他的基本主张。
然而,随着塔氏对于艺术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在艺术作品的开放性和自由阐释等问题上,塔氏又有了新的理解,他的本质主义观点逐渐发生了松动,他对于艺术的看法亦生发出一定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建立在古典理论之上的。与此同时,塔氏史学家的身份在艺术问题上也起到了建构性的作用:他越来越强调艺术的历史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传统和艺术实践的转变甚至突变的问题,这就形成了塔氏美学上的本质主义与艺术上的自由主义相融合的立场。它集中表现在塔氏对艺术和艺术品定义时所抱有的开放态度上:一方面,他吸收了取消美学开放性和相对性的主张,主张要用开放、包容的态度来看待艺术;另一方面,对艺术和艺术品进行定义的尝试本身就说明了他仍旧需要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来对艺术体现出来的自由加以平衡和限制。对塔氏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把塔氏遵循的这种相对性原则称作“关系主义”,即“将关系主义作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中间立场”,它是存在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一种具有相对性倾向的折衷立场。对于这种具有“关系主义”的折衷立场,晚年的塔氏进行了如下总结:
1.在承认人类判断具有普遍性的情况下,我们指出,有些普遍的,并且循环往复发生的事实并不是暂时的,它们是可以被历史证实的。比如说,历史就证明了古希腊的雕塑和庙宇具有成就的价值,这可以间接地说明,古典本身就是一种永恒的价值。
2.不可否认,人类的一些判断仅在满足某些需求的情况之下,才能赋予一些事物以价值,但是我们要指出,很多需求本身就是必要的,作为人类并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思考它们。
3.这其中还包括和自然现象有关的价值论的特殊性,这些现象是一些人经验的对象,所以它们之中有一种“人文因素”。即便这些“人文因素”是主观的,但它们并不是完全主观的。价值可以是客观的,即便它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用,甚至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33]
这一论述一方面可以很好地证明前文的观点:首先是强调古典的永恒价值的本质主义立场,其次是强调“人文因素”的自由主义立场。塔氏在承认古典本身永恒的客观价值的立场上,用人文因素中蕴含的相对性对这种客观价值加以调和。如果对塔氏的其他思想,比如哲学和伦理学思想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这段论述的目的并非仅针对美学和艺术,还包括伦理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学科,塔氏在《论幸福》中的观点同样可以用这段论述加以观照。因此,回到艺术问题,本质上讲,塔氏希望用哲学的概念与定义来归纳艺术问题,并努力去探求艺术中存有的永恒价值,但艺术的主观性和特殊性让塔氏不得不采取一种较为宽容的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美学本质主义与艺术自由主义的折衷立场就这样形成了。这一立场同时认识到哲学美学这一面向的本质维度,以及存在于艺术实践中的灵活、自由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如孙晓霞所说,塔氏的美学研究方式“在哲学美学与艺术科学两条分离的道路之间形成了一条中间道路”,他的研究进路和多元美学观“对今日的艺术学、美学学科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理论价值”。[34]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同时,还应当认识到折衷立场同塔氏历史主义美学思想的联系。笔者曾撰文指出塔氏美学思想中呈现出的历史主义美学特点以及其中包含的“个体性”“相对性”及“历史性阐释”三个维度。“个体性”是对事物发展特点和发展语境的强调;“相对性”侧重于价值的历史发展以及价值在变化过程中体现出的反本质主义的态度;“历史性阐释”是随着历史主义的发展逐渐形成的一个特征,强调对事件及艺术作品研究时所贯彻的历史的、开放的阐释原则。[35]折衷立场与塔氏的历史主义美学思想是高度契合的。其一,这种立场充分兼顾美学与艺术各自的特点以及两者可能产生的关系;其二,折衷立场将美学与艺术问题纳入历史语境当中,对其进行具体的、相对性的考量;其三,折衷立场考虑到了艺术实践中蕴含的自由度和特殊性,因而为艺术,特别是艺术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打开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结 语
前文论述塔氏美学观和艺术观时,主要是为了阐述塔氏在面对美学理论问题和艺术实践问题时的态度和标准。可以看出,塔氏的美学理论以“古典理论”为基点,且这种理论是有规律可循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转化,主流与支流的转变。而艺术问题由于涉及诸多实践方面的问题,往往呈现出多样化和相对性的色彩。特别是在先锋艺术样态层出不穷的今天,给艺术下定义似乎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塔氏并没有放弃这种尝试。
本文分别陈述了塔氏的美学观和艺术观,但这并不是说,在塔氏的美学思想里,美学问题和艺术问题就是截然对立、毫无联系的。恰恰相反,美学理论问题和艺术实践问题在塔氏那里非常恰切地融合在了一起,塔氏的美学本质主义立场和艺术自由主义立场出现了互相渗透、相互补充的情况,我们称之为“美学本质主义与艺术自由主义”的折衷立场。当下,艺术品越来越“泛化”,艺术似乎失去了自身的边界。塔氏对于美学和艺术的看法应该可以为我们认识艺术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他的美学观中“美学本质主义”的立场能够让观者以一种历史的视角,将美的大小传统的变化置放于美学理论史的河流中加以审视;他对于艺术所秉持的“艺术自由主义”,连同他定义艺术的尝试则让我们以一种更加开放、多元的态度看待艺术。艺术的美也在绝对与相对之间、在本质与自由之间展现出来。
[1]王齐飞:《塔塔尔凯维奇:古典理论的意义》,《中外文化与文论》2021年第2期,第349—358页。
[2]Władysław Tatarkiewicz, "The Great Theory of Beauty and Its Decline,"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31(Winter, 1972): 165-180.
[3]Ibid..
[4]Władysław Tatarkiewicz, “Did Aesthetics Progres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 31(Sep,1970):47-59.
[5]陆扬:《西方美学通史: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30页。
[6]Władysław Tatarkiewicz, “Did Aesthetics Progres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 31(Sep,1970):47-59.
[7][波]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34页。
[8][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6—17页。
[9]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38页。
[10]Władysław Tatarkiewicz, "The Great Theory of Beauty and Its Decline,"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31 (1972): 165-180.
[11][波]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第201页。
[12]Władysław Tatarkiewicz,"Did Aesthetics Progres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31(Sep,1970): 47-59.
[13]Władysław Tatarkiewicz,"What is art? The problem of definition today,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 11, (Feb,1971): 134-153.
[14]Władysław Tatarkiewicz,"Did Aesthetics Progres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31(Sep, 1970): 47-59.
[15]Władysław Tatarkiewicz,"What is art? The problem of definition today,"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 11(Feb, 1971): 134-153.
[16][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三大批判合集(下)》),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17,第343页。
[17][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109页。
[18] Morris Weitz, "The Role of Theory in Aesthetics ,"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15(Sep.,1956): 25-35.
[19]Władysław Tatarkiewicz, "What is art? The problem of definition today,"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11 (1971):134-153.
[20][波]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译文出版社,2013,第45页。
[21][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46页。
[22]同上书,第48页。
[23]Władysław Tatarkiewicz,"What is art? The problem of definition today,"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11, (1971): 134-153.
[24]Berys Gaut, "The Cluster Account of Art Defended,"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45(2005) : 273-288.
[25]孙冰冰、周计武:《如何应对艺术概念的开放性?——论塔塔尔凯维奇的析取性定义》,《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110—118页。
[26][波]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译文出版社,2013,第55—56页。
[27]Władysław Tatarkiewicz, History of Aesthetics,Vol.III, Modern Aesthetics, trans. Chester A. Kisiel and John F. Besemeres, ed. D. Petsch(PWN-polish Scientific Publishers, 1974), p.20.
[28][波]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译文出版社,2013,第57页。
[29]同上。
[30]彭锋:《美学与艺术的当代博弈》,《文艺研究》2014年第11期,第13—20页。
[31][波]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译文出版社,2013,第57页。
[32]Dziemidok, Bohdan. "Aksjologia Władysława Tatarkiewicza," Filo-Sofija Nr.13-14 (2011/2-3): 459-472.
[33]Władysław Tatarkiewicz, Parerga(Warszawa:PWN, 1978), S. 62.
[34]孙晓霞:《美学与艺术学的中间道路——塔塔尔凯维奇的美学史体系再分析》,《外国美学》2018年第1期,第37—52页。
[35]王齐飞:《塔塔尔凯维奇历史主义美学思想探析》,《艺术理论与艺术史学刊》2022年第2期,第141—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