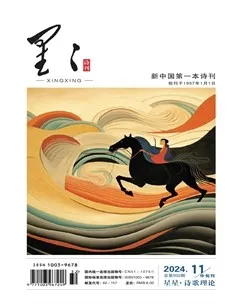寂静而深邃的心灵之旅
我与阿卓务林并不熟悉,近日收到他寄来的2023年2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群山之上》,初读便被其文字深深吸引。在诗集《群山之上》中,诗歌的意象异彩纷呈,彝族母语的力量如“幻觉之音,来自天堂”,充满了沃尔夫冈·伊塞尔所说的“召唤”的力量,不断激发我的阅读兴致。时光静静流淌,一张木犁、一个石磨,还有舞动的皮鼓,如“天外咒语”和“万能的隐喻”,让人“眼里泪水汪汪,仿佛奔腾着一万只麂子”。在这样的诗境里,民族生活的灵韵和诗人的创造力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整部诗集耐人寻味的意象世界。
诗集《群山之上》分为“指路经”“草木青”“山歌王”“西南谣”“光阴咒”“匿名信”六辑。在我看来,看似随意的辑名编排中呈现出一种井然有序的内在理性,直观地将诗人对诗歌意义的认识展现出来,让读者看到诗人将民族生活内化为心灵图景并形成诗性表达的完整过程,其逻辑递进带着自洽与上升的清晰走向。这个层层推进的过程有点类似于T.S.艾略特和威廉·布莱克的诗意升华方式,但与他们不同的是,阿卓务林用来当作言说载体的始终是彝族的民族文化与生活细节,带着云南少数民族的本土气息。读完整部诗集,我认为阿卓务林是一个具有诗性自觉的诗人,而作为一位彝族诗人,他的创作主体意识又具有明显的直观形态。
诗集的第一辑“指路经”展示了诗人的彝族文化之根和诗歌创作的价值起点,是诗人的本色亮相。彝族文化中蕴含的母语的呼唤、文字带来的季节、凉山的来信、祖先的火镰、山歌中升起的炊烟、迁徙路上的大梦、咒语中柔软的心愿等,都是阿卓务林构成诗意的“指路经”。朴素、坚韧和善良本性与知恩必报的性格让阿卓务林成为一名当之无愧的彝族诗人,而诗性始终流淌在那片深厚的彝族文化厚土之中。在第二辑“草木青”中,阿卓务林从彝族文化指向自然之物。热爱一种文化就会热爱滋育这种文化的大自然,而大自然永远都是各民族文化的摇篮。在这一辑中,我反复读到那些平凡的植物、动物和大自然的奇观,但这并不是普通的咏物之作。在阿卓务林笔下,大自然是被赋予了特定意味的属于彝族人心灵的“凉山奇观”,它们长着“飞越群山的翅膀”,“三千年死去,三万年活来”。大自然的大爱启迪了诗人,也可以说是诗人的创作显现了这种无声的大爱。第三辑“山歌王”的诗意由自然转向人文,展现的是作为个体的人无法离开的亲情。从远嫁他乡的可爱的二姐开始,回忆的闸门打开,诗人自如地呈现身边人的世俗生活。亲情、爱情以及人间的普遍之爱,构成了忧郁而又柔软的诗歌群像,也构成了一个质朴而低调的彝族人的生活世界。如《对爱只字不提的女人》中,“风把她们的脸吹红,她们便以/一朵花的名义开在我心底/雨把她们的心淋湿,她们便以/一滴泪的忧伤泊在我眼里”,诗中“对爱只字不提的女人”即使心中挚爱无限也隐忍着,她们的爱是深沉无声的,而那些“悲伤,宛如烟云”。我认为只有深谙本民族欢乐和痛苦的诗人才会有这种独特而深刻的体会。
阿卓务林将具体的爱化作对故乡厚重的情感,在第四辑“西南谣”中诗意再次演进,升华到社会现实。他在《故乡》中写道,“故乡就在脚下/再怎么用力踩/她也不会喊疼”。故乡成为诗人赞美、思念、信赖的底蕴,却埋藏着一个巨大的情结——故乡的大山、河流、湖泊、古城会一扫低沉与喑哑,闪现出雪峰一样的亮色与圣洁。如《群山之上》中,“山冈上去年积的雪,丝绢般/装饰着天际/……/水灵灵的牧羊女/遁入冬眠的草甸,唯有头上被晨曦/染红的丝巾,风中桦叶般招摇”。令人神往的玉龙雪山、泸沽湖、宁蒗城、丽江城、永北城等在诗中一一出现,构成平凡又神奇的意象,让我如入梦境,如沐清风。作为一个清醒的诗人,阿卓务林并没有一味沉浸在这种美好的境界之中,而是注意到人间存在的苦难。在诗歌创作中反思历来便是可贵的品质,或者说是诗人成熟的标志,就如第五辑“光阴咒”中,阿卓务林反思心灵的异化对生活的惊悸与否定,对现代化的进程充满深层次的忧郁和疑惑。如《在低处》中,“在低处,甚至更低处/挖掘机的尖角直刺大地的心脏/丝质的渔网撒向空阔的天空”。诗中拉煤的马车穿过小镇,有“叫作汽车的怪兽”,诗人“耳朵里的天堂”交织着人世与神界的声音,人的“内心是空的”,有的只是孤独和无助。针对世俗,诗人质疑远离心灵的行为;针对精神,诗人叩问时光与生命的真相。因此,“光阴咒”可以说是诗人诗性自觉的重要体现,带有超越族群局限的意义。而第六辑“匿名信”的重心则是反思之后的领悟与告白,是对真谛的探寻与收获。如《高原红》中,“心无杂念的牧羊人摆放好皮靴之后/回到树下,绵羊群顺从地躺在他身旁/春意盎然的神山历经一个早晨的争吵之后/平息往事,杜鹃花蕾在一声鸟鸣中/等待着绽放。风停了下来,云也不动了/……/而千里之外的荒野/一位远道而来的信徒,因一场突如其来的/高原反应,她的脸被染上殷红的色彩”。高原的秘境没有标志,但带着秘境的安宁,一切都像被清水洗过之后的样子——邂逅与错过、挚爱与无果、顾眷与舍弃等皆为天意。因此,诗人将诗意羽化为“群山之上”的一片空灵,“我带不走,带不走西山的云霞”。
在云南,阿卓务林始终是一个亲历者,对彝族生活的沉浸式体验让他对诗歌有着自己的理解,并形成独特的言说表达方式——旁若无人地低语,静静说出一个又一个让人心灵颤动的独特场景,构建属于“凉山的意象”。如《在凉山》中,“只有未曾尝过洋芋的绵羊/没有从未采撷苦荞花的蜜蜂/在凉山,苦荞花是盛开的梦想”。艰苦环境中盛开的苦荞花,由于有绵羊、蜜蜂的铺垫而传达了内在的情感,呈现出意象的鲜亮,这并不是走马观花就可以看到的景致,而是与生活融为一体之后的领悟。又如《天菩萨》中,“行走在彝人的高山上/我们成了飞翔的雄鹰/身后是响声如雷的翅膀/……/只要是灵魂栖息处/风雨慈善,菩萨不惊”。如果诗人不曾与高山融为一体,又怎能想象出这神奇的幻境,只有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故乡的人,才会生发这样的感受。
诺瓦里斯曾说,哲学是带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精神的家园。虽然这是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哲学的理解,但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彝族诗人阿卓务林来说,诗歌何尝不是这样。对故乡彝族生活的沉浸式体验,使那些生活中十分普遍的事物在阿卓务林心中也产生了特别的意味。在《弯月》中,“父辈们遗忘在山上的火镰/醒了//看,它跑到了天上/敲出闪闪光”;在《火种》中,“若是哪家女儿出嫁,火焰还会更炽烈/……/但不论哪一个季节,火塘里的炭火//需像种子一样拢盖好,生活无非酸甜/眼前一亮的光,亘古未变的冷暖”;在《牧羊人》中,“你张开双臂,幻想自己长有风神的翅膀/路上有山,当然也会有水/多么幸运啊,你用火镰燃起一簇火/来自午夜深处的人,远远看得见”。阿卓务林的感悟与哲思有着耐人寻味、激荡人心的张力,用充满想象的言说完成诗意构建的同时,用形象的方式诠释了诗歌所追寻的哲学意味。
在当下的时代,诗歌的外部因素常常影响着诗歌应有的质地,没有诗性的事物纷至沓来,使诗人难以静守心灵的安宁。对于阿卓务林来说,喃喃的低语来自故乡的情感深处,想象的翅膀因深入民族文化而更为有力地张开。他用个性化的言说保持与时代的联系,极少使用大词,语调也十分平静。如《万格山》中,“我的出生地,梦里常回的故乡/它像一尊佛,端坐在白云之上/脚下无论发生什么,一声不吭”。诗中的金沙江和高原上神一样的大山是一种无言的存在,但它们的内力却无比强大,令人崇敬,而这正是阿卓务林独特的个性化写作方式。在任何诗人笔下,那些“一声不吭”的有内力的表达其实都有力地保持了与时代的关联,只有摒弃功利的杂念才能看到真相。正如巴勃罗·聂鲁达曾经写过,“你就像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所以当写作越来越多地走向个人的时候,写作的魅力也逐渐呈现。最后借用人们对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特的评价来表达我对彝族诗人阿卓务林的肯定,“令个体的存在获得了普遍性”,同时也将其作为一种期望,愿他在写作中进一步呈现出云南省多民族文化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