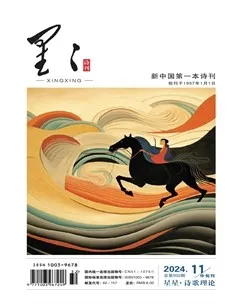来自边塞的诗性
“边塞诗”主要是指描写边塞生活、战争、风情的诗歌。中华文化中以西北地区作为描写对象的“边塞诗”自唐朝盛极一时后,于文学史中渐渐失去了所谓的话语权。“万物皆流变”,进入新时代后,“失语”多年的“边塞诗”迎来了“新边塞诗”的时代,为“边塞诗”注入了新的活力。2024年8月,一支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采风队伍到喀什采风,重新挖掘这座边塞城市的文化内涵,将喀什沉重的过往、独特的人文以及壮阔的风景与自己的灵魂深度交融,创作出一批具有新时代特色的“边塞诗”。在我阅读完“丝路上的诗路”喀什诗人疏附县采风作品选后,看到诗人们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激发出的“新边塞诗性”。
喀什地区古称“疏勒”“任汝”“疏附”,作为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是中外商人云集的国际商埠。现在的喀什是新疆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集中体现了维吾尔族民俗风情、文化艺术、建筑风格及传统经济的特色和精华。这次采风作品选中呈现的“新边塞诗性”就流露出强烈的历史关怀。如诗人赵香城在《探访明尧勒》中写道,“拾起一只陶罐的把手,似有汗渍斑斑/这陶,盛过戍卒的青春、期盼和呼唤//拾起一块带花的瓷片,似有泪光溢出/这碗,盛过苦涩的烟缕和泪滴//我沿着内墙走过一圈,丈量着死寂的城池/计量着属于此处死去的时间”。为满足古丝绸之路出口贸易的庞大需求,古代明尧勒人民夜以继日地赶制着各种精美的器物,作为意象,诗中的陶器、瓷器有着双重隐喻。首先,无论是陶罐还是瓷器,皆出自劳动人民勤劳的双手,在精心烧制的过程中凝聚着匠人们的心血与智慧。诗人从散落一地的碎片中,不仅窥见了器具往昔的华美风貌,更深刻感受到了匠人们倾注其中的悲欢。这些器具的故事也是这些无名匠人们的故事,蕴藏着诗人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其次,无论是陶罐的把手还是带花的瓷片,都作为文明曾经丰饶于此的证据而存在。经过时光的冲刷,虽然这些器具变得残破不堪,徒留些许残骸令人凭吊,即便“汗渍”早已风干,被时间遗弃在这“死寂的城池”,却超越其本身的物质形态,成了那段遥远却令人神往的时光的象征。在面对历史的同时,喀什诗人也将目光投入现在的疏附城。如边智在《小巷》中写道,“小巷弯弯曲曲/悠长、厚重、苍老、古朴/延伸着喀什噶尔的历史/展示着喀什噶尔的美”。面对此情此景,诗人自然而然地表达出对一座城的深情赞美。此外,许廷平的《克孜勒河畔》、唐兴义的《兰干辞》、王九洋的《乌帕尔日记》、李平原的《致疏附》、黄敏的《馕》也是写给新时代疏附的,是诗人对家乡发展的赞美之诗。
古老的器物、建筑或许会随着时光风化而流逝,但人们的精神信念却始终不灭。诗人稻子在《枯木断想》中写道,“执念。执着/一定有这样的隐形的力量”。恶劣的外在环境造就了疏附这座古城内在的执着与坚韧。正如马可·奥勒流所说:“阻碍了行动的阻碍,反而促进了行动。”疏附古城的人们从来没有因为古城在历史中的“失语”失去生活的信心,而是自扎根于这片土地便热爱着这里的一切,在袅袅乐音中演奏着他们的欢乐与哀愁。如甘灵辉在《在疏附乐器村》中写道,“他瘦削黢黑的脸上/目光如炬 闪着快乐的光芒/点亮困顿的世界”。无论日子过得如何艰辛,音乐始终是不能缺失的调味剂,在乐者弹奏的片刻,悠扬的乐声便构成了他的世界,不仅他自己深深地沉醉其中,也让听者陶醉,忘掉尘世的一切烦忧。
赵香城在《琴匠》中写道,“他神情专注地凿着一件锯坯成型的木件/在木件上凿出一个碗的模样/小砍刀,一下,一下,深浅有度/我认出这是一把艾介克琴的雏形/他点头笑了,引我观赏墙上悬挂的/一件件神品”。琴匠近乎虔诚地完成着每一个雕刻步骤,形象是如此真挚动人。因为在琴匠心中,乐器不单是一种表演工具,更是一件“神品”,是能够与神沟通的凭借物。这质朴的工匠精神以一种“非物质化”的姿态“夺回”曾失去的文化传承,其间蕴含的一个民族的“执着”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之一,也将汇聚成为一股温暖而强大的情感力量,催生的诗意也就显得更加珍贵。
历史的深邃与精神的坚韧在疏附相互交融,碰撞出绚烂夺目的诗意火花,引领诗人们走向更为深邃广阔的诗性思考领域。魏明德在《四十眼泉》中写道,“四十眼泉/叮咚了几个世纪/像是弹奏一首悠扬的乐章/从黄昏到黎明/穿过疏勒国/穿过沙漠/穿过河西走廊/穿过街巷/汇入护城河/这一刻/四十眼泉与长安对话/与商旅对饮/古老与现代交织/是自然的馈赠/是历史的见证”。诗人将过往与现实并呈,用四个“穿过”巧妙地构建了时空交汇的壮丽画卷。从时间维度看,四十眼泉历经不同世纪的更迭始终流淌不息,跨越了时间的长河;从空间视角看,四十眼泉流经了众多地域并连接起不同的风景与文化,实现了空间的跨越。作为时空的穿越者,四十眼泉不仅是历史的象征,更是历史的亲历者,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味。甘灵辉在《一千条路》中写道,“去明尧勒古战场遗址没有路/热娜说,我们走的这条道/洪水来的时候是河流/洪水消退了,就是路/明尧勒,汉译意为一千条路/一千条路,一千条消失的河流/一千条消失的河流,就是一千条路”。这是诗人造访明尧勒遗址时写下的诗句,体现出她对存在问题的思考。河流常被视作文明的摇篮,河流并非永恒不变,它们会随着自然的力量而变化。明尧勒的河流似乎也在诉说着这片土地曾经的繁荣与辉煌,无论是作为滋养生命的河流,还是洪水退去后留下的道路,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都以各自的方式展现着存在的意义与力量。此外,赵青阳的《蝉鸣》一诗则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喀什所在的西北地区的诗性曾沉寂了漫长的数个世纪,但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学的枷锁被打破,朦胧诗如同一股清新的风,对中国诗人的艺术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从那时起,西部的诗人们也纷纷挣脱空洞浮华的创作窠臼,摒弃单纯咏物赞颂的陈旧模式,携手开创了属于新时期的“新边塞诗”,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了崭新的生命力。在“新边塞诗”的影响下,喀什的诗人们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如唐晓冰的《冶铁》、空白的《遇见·杏》、梅朵的《观舞》、包训华的《雄鹰歌唱大地》,是诗人们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将笔触探向灵魂的深处,以真挚的情感回应喀什深情的呼唤。在他们笔下,诗歌的地域个性得到了充分、生动的展现,每行诗句都洋溢着来自边塞的诗性魅力。彭金山在评价“新边塞诗”的这种“双向深入”的感受时认为,这种方式使“‘风景’‘风情’由习惯认识上的客体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生命主体和表述主体,新边塞诗真正成为诗人‘心灵的声音’‘情绪的方程式’”。
喀什这座历史悠久的边塞城市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的光彩,正以开放的姿态向世人发出诚挚邀请。透过这些饱含深情与哲思的诗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新边塞诗”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向着更加高远的方向翱翔,书写着新时代边塞文学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