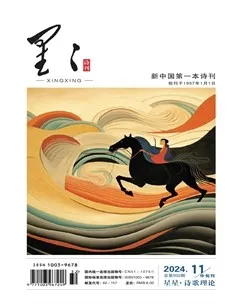巨草内部的存在之思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戈 麦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草生长的时候,我在林中沉睡
我最后梦见的是秤盘上的一根针
突然竖起,撑起一颗巨大的星球
我感到草在我心中生长
是在我看到一幅六世纪的作品的时候
一个男人旗杆一样的椎骨
狠狠地扎在一棵无比尖利的针上
可是没有人看见草生长,这就和
没有人站在草坪的塔影里观察一小队蚂蚁
它们从一根稗草的旁边经过时
草尖要高出蚂蚁微微隆起的背部多少,一样
但草不是在我的心中生长
像几世不见的恐慌,它长过了我心灵的高度
总有一天,当我又一次从睡梦中惊醒
我已经永远生活在一根巨草的心脏
——选自戈麦著,西渡编《蓝星诗库·戈麦的诗·典藏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
诗人西渡曾在怀念戈麦的文章中描述其为“一个在刀刃上行走的人,一个奇迹的创造者”。如他所言,阅读戈麦的诗篇绝非一场轻松愉悦的漫步,因其行文间涌动着的那股难以言喻的紧张感,与善于从简单事项中发掘时代症候的敏感力,让每一个试图接近的人都不得不与他一同行走在刀刃上,面对那些被日常琐碎掩盖的深刻与复杂。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便是这样一首诗,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它诞生于时代更迭下诗人与世界、自我的心理博弈。在诗歌的开篇,诗人通过一句简短有力的陈述,将诗歌的主题引向一个哲学议题:存在与被感知之间的关系。草在生长,但没有人看见,诗人描绘了自然界中一个司空见惯却往往被忽略的现象,我们不禁发问:“草”的象征意义何在?它是否代表了对生命本质的探索,以及对个体存在价值的觉察?还是反映了时代中悄然滋生的不稳定因素?无论如何,诗人视之为如“草的生长”一般普遍的现象,却往往被忽略,甚至遗忘。存在本身与被感知之间的隔膜是“在林中沉睡”的结果,这种“沉睡”并不是真正的睡眠,而是生命的静默、孤独的观察,也暗含着苏醒的可能性,暗示了一种潜在的、未被发掘的生命力。当存在物缺席时,其存在的功能属性反而变得愈发活跃,成为一种等待被发现和填补的空白。接着,诗人沿着诗意的轨迹踏入梦境,借用梦中的超现实图景展现人类内心的潜在资源。“一颗巨大的星球”,其重量不可估算,它象征着那些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难以捉摸、无法衡量的力量和情感。而在诗人的梦中,巨大的星球却被秤盘的指针——通常用于衡量有形之物的测量工具所托举,物的不可测量性与真实存在的物理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张力与视觉冲击,挑战了我们对物理法则的认知,使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现实与梦境、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界限。通过超现实的描绘,诗人将诗意引向了一个充满紧张与神秘的领域。
在第二节中,诗人以“草在我心中生长”为开头,将“草的生长”从被忽视的境地拉回,成为诗人心中可被感知的存在。“六世纪”的时间指代,让人不禁联想到欧洲历史上那段黑暗压抑,却孕育着文艺复兴火种的中世纪,联想起在艰难时刻,人类的精神与创造力仍具有复苏的可能性。此时“针”这一具有线索意义的意象再次出现,我们可以注意到与之相关联的意象产生了变化:从“巨大的星球”转化为“男人的椎骨”,标志着诗人从宏大的宇宙转向了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而这根扎在男人椎骨上的利刺,象征着诗人面对现实的不安和内心的挣扎,深深地贯穿诗人的血肉,使得诗人无法再回避言说的冲动与诗意的躁动。
到了第三节,诗人再次将不被感知的草置于叙述的中心,形成了一种结构上的复现。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复现超越了简单的重复,而带来了诗意的叠加与跃进,它巩固了“看见”与“忽视”,以及“没有人”所指向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张力,强化了诗歌中两极对立的紧张关系。诗人进一步揭示了人们对于草生长细节的忽略,例如蚂蚁经过草尖时,草尖高出蚂蚁背部的微小高度,引导读者更加敏锐地感受到这种被遗忘的现实。无论是在“人群之外”还是在“诗人体内”,草始终保持着其存在的双重向度,面对前者被遗忘与忽视,却萌生于后者心中躁动不安的土壤。
然而在诗歌的结尾部分,当诗人再次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却对“草的生长”这一曾发生过的心理历程提出了否认,诗意的天平向悲观倾斜。此前,他或许曾误以为草在内心蓬勃生长,然而最终意识到,这不过是一种情感的错觉。诗人态度的转变,源于他意识到这“几世不见的恐慌”仍然存在——如同被刺穿在针尖上的六世纪的男人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以“超越心灵高度”的压倒性力量悬浮于现代人的心灵上空,等待下一次“惊醒”时被察觉。在对大多数人已将“草的生长”(自身主体性的觉察)抛掷脑后的现实有了深刻体认之后,诗人选择以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姿态来面对,即“从睡梦中”醒来。此时,一种诗性逻辑的自我实现在诗人心中得以完成。诗人深知自我的更新无法超脱时代的匮乏,对内心之“草”的清醒感知无法改变“没有人看见草生长”的现实,他选择将自身寄托于一根“巨草”,一处困境当中的心灵平衡木,使得诗人得以站在另一个维度,审视着这个时代的病症与希望。
巴什拉在《论内在性形象》中提出,人们对事物的想象能够改变物的存在维度:“一旦我们想在微型世界中梦想或思考,一切就都变大了。无限小的现象,有了无限大的宇宙外表。”戈麦的这首诗同理,当诗人开始对“草的生长”这一细微变化的现象进行想象性觉察,便摆脱了“微小”带来的视觉与心理上的局限性,而看到细物的无垠内部。草随着诗意的延展而生长、扩大,最终以一种几何学悖论的方式成为诗人永远寄寓其中的“巨草”。当诗人进入“巨草的心脏”,那么草与诗人的大小关系便发生了颠倒,二者的内外秩序也被翻转,诗人得以借助“巨草”之内的隐秘观察,以物的视角窥见自己的内在。
这首《没有人看见草生长》的创作时间为1990年4月,两日之后,戈麦创作出了被后人广为知晓的《厌世者》,标志着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厌世者时期”。在《厌世者》中,戈麦用“在世界的镜子后发现奇迹的人”形容“厌世者”这一群体,既赋予了这一群体崇高的象征意义,又透露出一种自我陈述的意味,诗人本身作为“厌世者”中的一员,在拒绝空洞呆板的世界的同时寻找着奇迹与解脱。当我们将《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与《厌世者》进行比较时,不难发现两者在诗意上的连贯性,以及诗句深处潜藏着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一方面,“巨草的心脏”象征着那些“厌世者”内心深处对生命奇迹的诉求,这种超越自身有限性的愿望正是他们得以在世界的镜子后发现奇迹、超越现实束缚的力量所在;另一方面,它也是一颗孤独与暗含自我解脱意味的心脏,象征着诗人在外部世界寻求自我解脱的尝试无果后,将精神自留地与外界彻底割裂的选择。诗人没有在自我与世界的冲突中留有和解的余地,因为深知一切和解只是暂时性的妥协,在“永远”所代表的纯粹性的诱惑面前,诗人几乎以一种自我献祭式的姿态倒向永恒的孪生子——死亡。同年9月,戈麦选择以自杀的方式彻底与现实的深渊断绝关系。或许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他于死亡的怀抱中“再次醒来”,他已“永远”栖息于那颗“巨草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