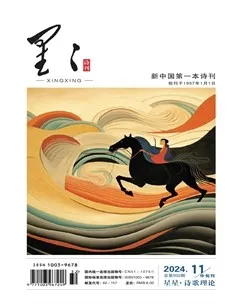诗歌文化的探究与力行
吴宜平:老师您好!目前我们的诗歌批评家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专门从事诗歌批评,很少关注其他文类;还有不多的几位批评家,既做诗歌批评,也很关注小说等其他文类。从我对您的了解中,您既从事小说批评,也从事诗歌批评,我还发现您其实对文学批评本身(包括对批评家)发表过很多文章,可以说是对批评的批评,很想知道您为什么会关切到如此多的领域,特别是这些年来为什么比较多地关注诗歌?
何言宏:宜平好!这个问题也有朋友问过,而且还是以非常善意的关切和提醒的方式来问我的。因为集中精力于某一更具体的领域、某一种文体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特别是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中,对于所谓的出“成果”、拿“项目”“集中精力办大事”,无疑是一种聪明的选择。对我来说,之所以横跨这几个领域,原因其实很多,有的甚至是无意间的结果——比如在对文学批评的批评上,回头一看,居然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字,前不久在编一本新的论文集,甚至想专门就此编选上一本。这些年来,之所以相对较多地关注诗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新诗的成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评价,甚至到今天新诗的合法性还会被质疑,实际上,这无疑是一个十足的伪问题,居然还会经常被拿出来煞有介事、吵吵嚷嚷地讨论。我认为在总体上,中国新诗的成就并不亚于小说,某些方面,其实要高于小说等其他文类,特别是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要远远高于。关于新诗的成就,废名先生多年前就说过:“我们的新诗简直可以与唐人的诗比,也可以有初唐、盛唐、晚唐的杰作,也可以有五代词、北宋词、南宋词的杰作,或者更不如说可以与整个的旧诗比,新诗也可以有古风有近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盛事。我劝大家不要菲薄今人,中国的新诗成绩很好了。”八九十年后的今天,废名先生当年所说的“中国的新诗成绩”,无疑更好!所以,我较多关注诗歌便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同时,无疑也出于对诗歌的热爱,也有人在江湖上了“贼船”身不由己等方面的原因,因此还耽误了很多“正事”,影响了对小说的关注,最近我还在读一些小说,算是某种补救。
吴宜平:那在您的小说批评、诗歌批评和批评的批评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或某种整体性、某种统一的考虑?
何言宏:首先得承认差异,即诗歌批评、小说批评与批评的批评之间在感悟、想象、知识、方法和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就我自己的体会,诗歌批评的难度与要求都要更高,小说批评相对要容易些。但也不可一概而论,要写出好的批评文字,其实都很不容易。我是好文章——而不只是所谓好论文——的鼓吹者。每读到一篇好文章,我都会像过节一样开心,甚至会奔走相告,或者相反,秘藏于内心。至于你问到的不同批评间的内在联系,我想那是很自然的。实际上我一直认为,不管是小说批评还是诗歌批评、散文批评、批评的批评等,都是我们作为“文学人”所表达的文学的自我意识,是一种文学的自觉,也是我们基于每一个批评主体的价值观念和批评对象之间的深入对话。所以,就我而言,每一次批评工作都是自己价值观的阐述、讨论或自我辩难与反思,也许这就是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整体性或统一的考虑。但在很多时候,这些又都是自然而然的,只要我们在写作时真诚思考和表达即可。实际上,这些年来我自己的思想也有变化,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过于信奉某种激进、简单、表面性的启蒙主义,而是一方面向基本的古典人文主义、现代人文主义退守,另一方面,也试图向新的人文主义——比如全球人文——进行某些拓展,但这都是另外的话题了,以后再说。
吴宜平:您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
何言宏:这个问题我曾在多处做过讨论,也曾有专门的文章。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涌现出很多相当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可以说以其诗歌成就开辟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也实现了诗歌史意义上的历史转型。这一转型的深刻性和广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诗歌体制方面。我们应该都记得,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诗歌体制与主流体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民间诗歌刊物、民间诗歌奖与主流性的诗歌刊物、诗歌奖之间的明确分野。而在二十一世纪以来,民间和主流之间却在很多方面走向了合流,合力形成了我称之为“混合体制”的诗歌体制;二是诗歌“活动文化”的兴盛与繁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运动此起彼伏,特别是“朦胧诗”运动、“第三代诗歌”运动等,不仅产生了许多重要的诗人诗作,取得了重要的诗学成果,还毫无疑问地融入正史。而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已经看不到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代之而起和遍地可见的是形形色色的诗歌活动,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线上与线下结合互动的诗歌活动更是越来越多;三是诗歌创作本身、中国诗歌的精神和美学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的现实精神、历史意识、日常书写、生命体验、女性意识、本土情怀、世界眼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需要我们的深入寻绎与辩证,在诗歌史等维度进行恰当的评估与定位。所以,综合来看,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的历史转型应该是全方位和整体性的,不仅是诗歌创作和诗学上的转型,更是更加广阔和深刻的诗歌文化的转型。
吴宜平:您对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历史转型的概括,很多方面我都感兴趣,比如女性写作问题、地方性问题、日常性问题、情感文化问题等。女性诗歌方面,记得我在做关于女性诗歌的博士论文时,曾与您多次讨论,很想再请您多谈谈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
何言宏:是啊,我们曾多次讨论过女性诗歌问题。但是说实话,关于女性诗歌或女性文学的讨论很有难度。许多年来,我们对女性诗歌、女性文学的讨论基本上沿袭着欧美学院的激进女性主义立场,实际上已经陈陈相因和固步自封地走向了固化,这一立场可以一言以蔽之为“身份政治”,本来丰富复杂和相当开阔的女性主义,被过于褊狭地简单化为对所谓“政治正确”的偏执追求。要知道,认识到这点很重要,因为目前在欧美甚嚣尘上的LGBT便以此为基础。所以,突破这一固化了的认知不仅很有难度,也非常重要,并且也可能会冒犯那些只是简单化地克隆西方所谓政治正确的女性主义话语的人士。不过在此方面我并不想仅仅停留和局限于女性主义话语的理论空转,而是想注目于具体的女性诗歌创作。如果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诗歌某些方面应和了西方女性诗歌甚至女性主义理论较为激进的方面,那在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些应和已经不再新鲜,很多女性诗人已经不再热衷于这些应和,而是变得更加开阔、更加温厚,对于亲人、对于生活、对于自然、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爱,越来越在她们的诗中有所体现。我曾将此称为“女性人文主义”,算是为超越既往“政治正确”的女性主义找到了一种新的途径、新的话语。归根到底,女性主义必须超越“政治正确”,走向更加广阔和深厚的“女性人文”。
吴宜平:近几年地方性问题已成为热点话题,诸如“新南方”“新东北”,还有“新浙派”“新北京”等,讨论得热火朝天,已经成了显学。但我注意到,早在2007年您就明确提出过“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问题”,后来您又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不断对此深化和拓展。就在今年《扬子江评论》的“文学现场”栏目“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中,您的《地方性问题中的个体核心》一文又重点讨论了“地方性”与“个体性”问题,您可以再谈一下诗人与地方之间的写作关系吗?
何言宏:地方性问题确实是个热点,而且热了好些年,现在仍然是一门显学。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早在2007年我就明确提出过“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问题”。当时我还在南京工作,和黄梵、马铃薯兄弟、傅元锋、何同彬、育邦等朋友一起搞了个“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我们以此为名义与平台,张罗过好多诗歌活动,2007年的“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论坛”便以“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问题”作为主题,很多诗人和朋友(如那一届的“柔刚诗歌奖”得主柏桦、宋琳等)都做了很好的发言。之后得到《扬子江评论》的大力支持,并从2008年第4期开始,专门开设“中国当代诗歌的南方精神”专栏,试图进行系列性的专题讨论。记得开始的这一期是在第一个栏目,并以“焦点话题”来予以突出,发表了我本人《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柏桦《江南诗人的隐逸与漫游》、李振声《南方精神的核心价值》、黄梵《作为一种分类方法的“南方精神”》和马永波《从比较文学的视野观照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五篇文章,很有规模。像柏桦的《江南诗人的隐逸与漫游》还成了讨论地方性特别是江南问题的名篇。一直感到非常可惜,由于自己的忙乱与懒散,这个栏目未能继续下去。不过在南方或江南问题上,后来总是心心念念,断断续续地以不同的方式来讨论,包括继续撰写一些文章,以及和朋友们一起捣鼓出的“江南七子”等,都说明“南方精神”问题还有充分的讨论空间。地方性问题能热到今天,并且能不断地展开与深入,我感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至于你所问到的诗人与地方之间的写作关系,首先,我最想强调的便是,地方性并不应该成为诗人或作家的创作目的,他们不需要刻意追求地方性,这在博尔赫斯的名文《阿根廷作家与传统》中已有很好的阐述;其次,在文学作品自然具有的地方性中,我们想看到的仍然是诗人或作家的个体性、个体主体性、个体多样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地方多样性。
吴宜平:您的批评文章,有些发表在专业性的文学批评刊物上,采用了论文体,但有很多发表在文学刊物上。您还在《星星》《诗歌月刊》等刊物开设过专栏,所采用的往往是随笔性的批评文体,我们在大学里工作和学习,很想知道个中原因。
何言宏:“我们在大学里工作和学习”——我知道你想说的是,我的不少发表在文学报刊上的文章,包括在《文艺报》《文学报》《星星》《诗歌月刊》等报纸和刊物上开设、主持的专栏,按照目前大学的考核标准,是不被承认的,所以很多明智的人从来不屑于在这些方面“浪费”时间,一心按照大学的指挥棒来指挥自己。我并不一味地排斥论文体,论文或论著体同样有很多杰作。像朱光潜、李泽厚等先生的论文和著作,很多都是经典。我自己当然也写过不少论著体,但论著体之外的对话体、随笔体,另外还有如“主持人的话”“授奖辞”等,可以表达论文体根本无法表达的内容。好像是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我认为文体甚至还可能是思想的囚笼。比如论文体,一方面,它会呈现出你的所思所想,将你的思路与论述逻辑很清晰地体现出来,形成所谓的“浮雕”;另一方面,它还会规范甚至窒息你的所思所想,将你丰富的感受以格式化的方式排除掉,尽说一些正确的废话,因此造成论文的空洞、平庸。所以说实话,要写一篇好的论文其实很难,要求很高。而另外一些文体,比如随笔体,因为其文体上的自由,不仅可以像蒙田所说的那样“更完整、更生动”和“整个儿赤裸裸地”表达自我,而且还可长可短,非常便捷。像我曾经在《星星》诗刊开设的“台湾诗人十二家”专栏,只花一年的时间便为大家介绍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十二位代表性的台湾诗人,如陈黎、夏宇、焦桐、许悔之、方群、颜艾林等;而为《诗歌月刊》开设的“诗歌当季”,一年时间内发表了四十多位诗人新作的阅读笔记,如果用论文体,其中很多想法恐怕要写好多篇、好多年。实际上,我所尊敬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比如谢冕先生、洪子诚先生、陈超先生和耿占春先生等,都是随笔大家,也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吴宜平:作为一位批评家,您是如何看待您的批评工作的?
何言宏:很多人不太理解批评家的工作,甚至在文学界也会有人怀疑和贬低批评家的意义,认为批评家是靠作家与诗人吃饭,寄生于后者。每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说,批评家与诗人、作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古希腊诗人及悲剧作家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之间的关系,也是孔子与《诗经》作者们的关系。当然,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认识到,正如诗人和作家们不是荷马、不是埃斯库罗斯,我们也不是苏格拉底,对于真理(包括一些小真理)的追求也许才是我们的共同任务与乐趣。
吴宜平:诗歌方面,除了从事诗歌批评,您还做了大量的其他工作,可否请您介绍一下?
何言宏:这些“其他工作”前些年做得比较多,我只能简要地谈谈。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大概是在2007年,我与南京的朋友一起搞了个“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除了发布当时影响很大甚至也有争议的“中国诗歌排行榜”,还在一些朋友和机构的支持下,先后举办了“中国南京·香泉湖国际诗歌节”“中国南京·凤凰台国际诗歌节”“中国南京·随园诗歌节”等,这些诗歌节内容很丰富,还包括“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论坛”和中国历时最久的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的颁奖仪式等。我来上海工作后,觉得中国诗歌与世界对接、交流的最佳区位就是上海,而我也一直认为,中国诗歌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性对话,在世界诗歌和全球诗学格局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在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下,2016年和朋友们一起张罗起了“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也花费了很多时间与精力,且不细说。当然,除过这些规模比较大的活动之外,还张罗过不少其他诗歌活动,比如至今还在张罗的“柔刚诗歌奖”等。其实,批评之外的“其他工作”也许还应该包括先后在《文艺报》《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等报刊主持的一些栏目,包括主编诗歌方面的一些图书,比如字数多达八九百万字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以及你也参加并担任副主编的两卷本《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对我来说,这些林林总总的工作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设计、内在的整体性,这就是我这几年来经常倡导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文学文化”或“诗歌文化”的理论方法。如果我们以更加综合的“文学文化”或“诗歌文化”的视野与方法来进行诗歌批评或者诗歌史研究,我在具体的诗歌批评之外所做的这些“其他工作”便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非常难得的实践经验。投身和介入到真正的诗歌现场,对我的诗歌研究和批评来说非常重要。
吴宜平:老师接下来有哪些计划,特别是诗歌批评与诗歌研究方面?
何言宏:说到计划,首要的就是得抓紧把手中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视野中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历史转型研究”完成,也希望自己在诗歌批评外,在我们将要出版的诗歌史料的基础上,尽早完成诗歌史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