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典型华人家庭”
读费孝通先生的著作《生育制度》时,读到他的“社会成员再生产”理论,我不禁暗笑,现在想要研究这些理论,显然在中国是缺乏较具普遍性和典型性的案例的,毕竟很多家庭是以三口之家为主。这就让我想起一个说法,海外华人倒是较典型的华人家庭。比如说,我在马六甲的一家。
马来西亚华人的家族往往庞大得多。我在马六甲的家里有七口人:爸爸、妈妈、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加上我。放在这个时代,即使是在马来西亚的“小”家庭中也算人口众多了。我听说2016年中国放开二孩政策后,出现了好多兄弟姐妹相差十几岁以上的家庭,常能目睹这样的场景——已经长出胡髭的哥哥抱着襁褓中的弟弟去散步。我和哥哥、姐姐的年龄差得不是很大,大家算是没什么代沟。兄弟姐妹的关系时而兄友弟恭、姐让妹谦,时而互不相让、硝烟弥漫,每过段时间甚至上演一番全武行。我的爸爸妈妈恰好各自都有8个兄弟姐妹,我家还算是“落后”了。曾经,我问妈妈为什么要这么等差数列似的一个个生,妈妈一本正经地说:咱们华人喜欢一个家庭枝繁叶茂,小时候是陪伴,长大后可以互相照应。这话目前我还是有点不懂,因为陪伴有时确实很好,就是大多时候太吵闹了,叫人想安心做点事时都找不到个地方待。爸爸妈妈都特别喜欢热闹,尤其注重雨露均沾地对待每个孩子。话又说回来,典型的华人父母总会有一些奇怪的习惯,比如爸爸很爱在你开心时偶尔泼冷水,妈妈则把孩子抓得很紧。反而是我的中国同学,有的一家三口相处得很平等,爸妈遇事会和孩子坐下来倾心交谈。我和同学们诉苦,他们就会说“哎呀,我们还有点羡慕呢”。我真有点哭笑不得。
爸爸经常会在我们与他分享期待时说几句不阴不阳的话(他称之为“给你们降降温,以免头脑过载”)。譬如,我要是说我考试考得挺好的,这一次估计可以拿到奖学金了,爸爸就会边看报纸边听我说,然后告诉我:“奖学金这么好拿?哩想得太美了吧?哩就慢慢等吧,看拿不拿得到。”小学的时候我听不明白,以为他叫我耐心等待呢,念了中学我就明白了,他老人家的确很热衷于给子女“降温”。我多少有点不理解,虽然孩子不奢望努力能有什么回报,但是有个小盼头总可以吧,偏偏他最擅长扫兴。我努力去理解爸爸,也许是他小时候也经常被长辈这样对待,潜移默化自己也变成了这样的大人,真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不,我才不要成为这样的大人!我安慰自己,爸爸这么讲也有两个好处——在事情不如预期,期待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不会那么失望。同时我也告诫自己,不要变成这样的父母。
妈妈把我们抓得很紧,18岁以前,孩子们晚上10点前必须到家;18岁以后,12点之前必须回来,不然就会被教训几句。妈妈会仔细盘问我们去哪儿了,我们的行踪都在她老人家的掌握中。我们家孩子这么多,不可能人人都考上马来西亚本地顶尖的大学,所以兄弟姐妹们有的选择去中国的好学校深造(比如我)。即便我们到了国外,妈妈也想知道我们的下落,不时发消息让孩子们打开定位,她说看到定位,知道大家都安好,自己就会很安心。我们在这样的典型家庭里长大,其实都可以接受,但其他人可就不一定了。大哥的对象曾问他,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为什么还要经常为母亲开定位。她嘲笑大哥是所谓的“妈宝男”。这让大哥非常烦恼,开始试图切断妈妈的关注。反过来,这让妈妈非常难受,于是我又成了妈妈的倾诉对象。她经常说“长子照书养,幼子照猪养”(好吧,我不得不做那只听话的小猪)。其实,哥哥姐姐比我更辛苦一点,总是要做弟弟妹妹的榜样。大哥是个温柔寡言的男孩子,特别体贴,妈妈最喜欢他。二哥则乖巧灵动,也善于哄妈妈开心,妈妈也很疼他。姐姐和三哥就显得叛逆些了,妈妈也最头疼他们。而我特别能聆听烦恼,妈妈最喜欢把我当成树洞。
当然,爸爸妈妈也有优点。大男子主义的爸爸的爱是深沉隐晦的。在马来西亚,如果想在小学毕业后进入以中文为媒介语的华文独立中学学习,就得先通过入学考,“独中”被认为“成材率较高”。一旦没有通过考试,就要到以英语和马来语为媒介语的国民型中学读书。我还记得,我参加入学考试的那天,天气阴阴的,太阳的温暖被云层阻拦在高空,地面呼呼地吹着凉风。那天我忘了带外套,只穿着小学校服,我感觉冷飕飕的。爸爸和大哥早早把我送到考点,我告诉他们考完试出来会用公共电话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再过来接我。当我考完试,恍恍惚惚走到楼下,便看见爸爸站在视野最好的走廊尾端,向我挥着手。我有点感动,快步奔向他,爸爸亲热地一把搂住我说:“看哩这试考得‘脸青青’的,免惊啦,没考上的话爸爸再帮你想办法啦,走吧,带哩去呷饭。”后来,大哥告诉我,那天他们把我送到考场座位后并没有离开,一直在楼下的阵阵凉风中等我,而爸爸在考试结束前一个小时就一直站在那个走廊尾端等我。爸爸心里可能也和我一样忐忑:“囡囡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大考试,她应该能做到的吧?”那天爸爸和大哥带我去吃了鱼丸米粉汤,清淡又暖和。
虽然妈妈把我们的行踪抓得很紧,但是在其他方面又放得非常松。妈妈不是那种亚洲“虎妈”,那种要求孩子一定要科科优秀,同时还得多才多艺的严厉母亲,她完全不会插手我们的学习。若是孩子们有想尝试的新事物,只要不违背道德和社会规范,她都不会说什么。想去露营、爬山、划船、参加生活营、在森林里过一夜,以及在国外冬季的海边玩,都行,没问题。想学钢琴、书法、绘画、舞蹈、游泳,能坚持下来她都全力支持。而不想学了,那就不学,绝不会因此责备你,因此我们很早就尝到了三分钟热度的“甜头”。有时,反而是老师比妈妈更担心我们的学习成绩。妈妈在学习上唯一抓得比较紧的是英语。马来西亚虽然是个多语言环境,倘若没有系统地用心学习,说出来的英语会是掺杂各种语言,语法杂乱无章的所谓“啰吔语”。妈妈自己就是英语老师,她认为要是亲自教我们这5个“土豆”英语,反而不利于把语言学好。因此,妈妈把我们送到了我家附近一位印裔老太太家里学英语。所幸我们对语言学习都比较感兴趣,学得还不算痛苦,不时还有一种取得进步的快乐,这也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小时候我们喜欢让妈妈开车带我们到附近海边淘沙玩,每次妈妈都会在车上放一首20世纪70年代的英文流行歌My Love,大家会跟着妈妈一起唱“My love is warmer than the warmest sunshine, softer than the sky”。车轮发动之前已经在太阳底下停留许久,车被晒得热烘烘的,空调暂时也降不下温度,车里像个桑拿房。六个人挤在五人座的四轮小轿车里一起唱歌,我会唱着唱着换成中文“我的爱比最热烈的阳光还要温暖,比天空还要松软”……我的脑袋被热气蒸得晕乎乎的,感觉妈妈好像真的开车带我们飞上了天空,车窗外飘着朵朵白云,和歌词里唱的一样,看起来又松又软,摇下车窗伸出手就可以抓上一把,手感一定很好。空调渐渐把温度降下来,孩子们又回到地面,而我们的心依旧比太阳还要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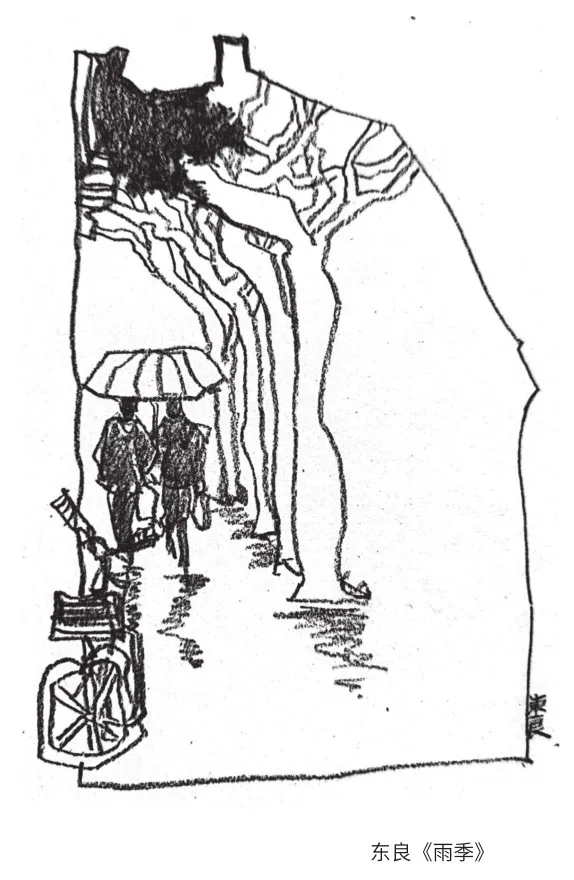
年纪渐渐变大,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像妈妈的免费心理咨询师,虽然没有执业资格,也没法给予任何专业建议,只能为她省下到外面找正牌咨询师的费用。爸爸和妈妈吵架了,妈妈会来跟我说;妈妈和姐姐闹了不愉快,妈妈还是来找我说;三哥和妈妈冷战,妈妈依旧来和我说。我这只“听话的小猪”就像妈妈的潜水气瓶,帮她在充满压力的海底还能继续呼吸。妈妈也知道,气瓶里的空气总有一天会耗尽,因此自从我离开家中,她便开始慢慢“上浮海面”,也就是说,她尝试着自己去调整情绪。我几次回家都能察觉妈妈越来越“接近海面”,最近一次回国发现她已经开始在“自由潜”了。当然,我还是会观察整个“海面情况”,如果有风浪预兆,如果妈妈需要,我会自动成为妈妈的气瓶,一起下潜。
爸爸鲜少参与我们的成长之路,幼儿园毕业,没有到场;小学毕业,也没有到场;中学毕业,同样没有到场。他每一天不是在外头工作,就是在家专注地看报纸。他参与最多的家庭活动就是一起吃午饭和晚饭,而我印象最深的共同回忆也只有那次入学考,所以我与他不算太亲密。直到前几年,我才再次意识到他那华人式的“深沉隐晦”的爱,只是不知道要怎么表达,仅能用他最擅长的那个方法。那次我们家一下子病倒3个人,有两个在国外,唯独他和二哥身体健康。看他手忙脚乱、如坐针毡地给我们每个人送柠檬蜂蜜水、白开水、药物等等,每隔5分钟就到每个房间看看躺在床上病恹恹的家人,问一嘴:“你感觉还好吗?”样子笨拙又好笑。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想对他说:“别再问了,让我睡觉啦。”他的爱太“深沉隐晦”了,导致孩子们也容易忘记他心里藏着对每个人的牵挂。
在我的印象里,爸爸就像12年前入学考那天的米粉汤,在我被风吹得手脚冰凉、瑟瑟发抖的时候,他会给我温暖。妈妈就像太阳,有时候比太阳还要温暖,热得让人头晕,我们都逐渐理解了,这就是她表达亲子之爱的方式。
想来爸爸妈妈也只是生养了五个孩子,如何对待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他们也在慢慢累积经验。等经验累积得差不多了,我们也都要渐次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再怎么不舍,米粉汤也会因为换了老板而变味,再怎么不舍,五人座四轮小轿车也会退休,换成七人座的四轮驱动车,再怎么不舍,爸爸妈妈总有一天也会开启新的旅程。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希望在和煦的朝阳和晨曦中,我们的“典型华人家庭”能相互陪伴着走得更远更久。
责任编辑 苏牧
作者简介
黄榆轩,马来西亚,南京艺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和美术与书法学院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