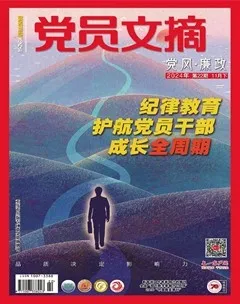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需要“体检”了吗?
2005年,原国家人事部、卫生部颁布《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体检标准》),对此前各地公务员录用中良莠不齐的体检标准进行了统一,修订了其中不科学的规定,特别是对乙肝病原携带者的录用作了重新表述。
此后近20年,《体检标准》作为国家颁布的标准性文件,被我国多数企事业单位广泛参照,已然成为入职体检录用的示范性文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该标准逐渐遇到新情况,全国各地出现多起因“入职体检标准争议”而引发的考生诉讼案件。
多位学者认为,相较于社会发展进程,《体检标准》部分条款已存在滞后性。过去几年,有关修订公务员《体检标准》的提议在全国两会中被反复提出,有关部门对此给予了正面回应,并表示已开展相关调研。
不同省份标准不同
2023年,经过两年备考,32岁的李玉终于“上岸”考取了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小学教师编制。但没高兴太久,一则体检不合格的通知摆在了她面前。
“地中海贫血,我万万没想到是因为这个问题。”李玉说。
过去多年,李玉一直在教培行业做代课老师,没感到身体有任何异常。2017年,李玉在婚检时得知自己是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婚后备孕时,她专门前往医院询问,医生告诉她:“这是出生便在基因里携带的,没有问题,也不需要干预治疗。”
后来,李玉和丈夫生下3个健康的孩子。入职体检前,她特地查看《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其中第三条写着:“血液系统疾病,不合格。”她又向医生询问是否会有影响,医生回复:“不会影响,没事,教育局不会看这个。”
因此,李玉放心如实地写下病史,没想到却因此被挡在入职门槛之外。她找到思明区教育局,对方回应是参照《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依规办事”。但在此前,她通过了同样是依据此标准考核的福建省教师资格考试,并且由思明区教育局颁发了教师资格证书。“所以,怎么会一个标准出现两种结果?”李玉不解。
李玉继续向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问询,对方给出的回复是:“参照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而在《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以下简称《操作手册》)中,有关“贫血”的条文解释中写道:“除某些原因造成的缺铁性贫血外,往往难以彻底治愈,属体检不合格。”
可李玉了解到,广东和广西两省(区),曾分别于2010年和2024年4月针对其省(区)内事业单位发布专项体检标准,在血液系统疾病中对地中海贫血作出放宽录用规定。
比如,在最新发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中第三条明确规定:“地中海贫血(地贫基因携带者、静止型、轻型)且血红蛋白高于90g/L,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可给予合格。”
医疗在进步,《体检标准》是否应跟进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曾于2021年、2022年连续两年建议重新修订《体检标准》,呼吁对一些能够正常履职的慢性病患者放宽录用限制。
张宝艳起初是因多囊肾患者的留言开始关注此议题,“然后我发现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涉及很大一个群体”。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肾脏病科主任毛志国表示:多囊肾病是目前发病率最高的单基因遗传肾脏病,发病率约为千分之一,“按这个比例算,我国至少有145万名患者”。
“这个病的主要特点是病程很长,在不做任何干预的自然病症情况下,部分病人可能会在五六十岁时肾功能衰竭。”毛志国猜测,这或许是2005版《体检标准》将之定为“不合格”的原因之一。

但毛志国表示:“近些年,医学界对于多囊肾的认知和治疗都有很大的进步。20年前防治这个疾病可能手段有限,但在现在的医疗手段下,我们对多囊肾的早期基因筛查已相当成熟,病人可以很早发现这个病,并且完全‘可防、可治、可显著延缓进展’。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医学水平来看,对于多囊肾患者有点‘量刑过重’。”
这也是目前主张修订《体检标准》的呼吁者的主要观点之一。公务员《体检标准》制定于2005年,上一次修订是2016年,一些医学专家认为,相较于不断提升的医疗水平,这份标准已明显存有滞后性。
除多囊肾病外,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健康医学科主任徐国纲表示,目前被《体检标准》认定为“不合格”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部分精神类疾病,或许也应依据现有医学水平作适当调整。
张宝艳在调研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一些非常优秀的患者,无法进入科研院所或是高校任职,转去海外就业,“我感觉,这也是一种对人才的浪费”。
如何改变
过去5年,每年全国两会都有相关代表呼吁对公务员《体检标准》进行修订。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金力曾在回复某多囊肾病患者代表的邮件来信中表示,有关部门对他提出的相关建议给予正面回应,认为确有修订必要,但仍需研究论证,并表示已向相关方面转达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不宜扩展用于其他行业的建议。
事实上,虽然如今的《体检标准》存有争议,但在2005年《体检标准》颁布之初,是为了更好保障公民平等就业的权利。
在2005版的《体检标准》中,修正了许多规定不科学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特别是对乙肝病原携带者的录用作了科学表述,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一个重要进步。
而此后《体检标准》的几次修正,也都是对当时社会呼吁的一种回应,在多项条款中都显现放宽的趋向,体现出《体检标准》在目的上对公平性的推动。
但是,由于法规的调整通常具有滞后性,很难跟上快速发展的社会变化。也因此,多位法学及医学界专家认为,除了要对《体检标准》进行定期修订之外,也要审视《体检标准》在设定上的合理性。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说:“体检标准应是一个最低标准,而非选拔性标准。”按照公务员法第13条规定,公务员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那么《体检标准》就应该以此为基准,不可过高。
一些法学研究者认为,目前的《体检标准》实际上是“个性的而非共性的集合”,即它是对公务员职位所有身体条件简单相加所得到的总和,而非一个“最大公约数”,这就要求应聘者的身体条件必须达到“全能”状态。
南开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刘俊振说,公职人员作为以国家为“雇主”的特定群体,本身存有某种特殊性,因而拥有特定的体检标准可以理解。
事实上,对患者而言,更大的就业阻碍来自公务员《体检标准》的滥用。通过检索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招聘信息,能够发现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都在体检标准中参照公务员《体检标准》。
这一方面是由于非公务员体检存在标准上的空白;另一方面,刘俊振认为,这或许反映出用人单位在招聘管理角度并没有对岗位本身作足够系统和严谨的分析。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成本性”始终是主要考虑因素,“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企业公平”。比如,某事业单位人事工作人员表示,虽然他也认为放宽体检标准在社会公义上是合理的,但作为用人方,他曾多次面临因员工身体问题而导致的工作问题,单位每年对员工的健康支出也比较大,这使得他在招聘时难免谨慎。并且,在面对多名候选者时,用人方“优中选优”也在情理之中。
多种原因都导致用人单位对调整入职体检要求缺乏动力,协调好“企业公平”与“社会公平”,这既需要某种外部限制,比如设置专门的反歧视法律以及反歧视机构。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从内部提升企业进行调整的动力。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