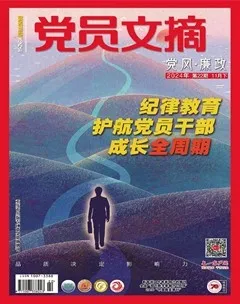谨防“非升即走”走偏
近年来,“双一流”等重点高校借鉴国外经验改革教师人事制度,推行以“非升即走”为主的“准聘—长聘制”。
但部分高校把“非升即走”异化为竞逐“科研GDP”的工具,存在淘汰率较高、以论文和项目为主的考评体系相对单一等情况,引发较大争议。
一些高校“非升即走”出现异化
今年,部分高校“非升即走”让一些青年教师承压等话题受到社会关注。“非升即走”简单说就是学校保障“准聘”学者的生活和科研待遇,学者需限期拿出代表性成果以获得“长聘”。
随着越来越多“双一流”乃至部分地方院校推行“非升即走”,这一旨在激发教师创新活力的改革举措,在一些高校变形走样。
一方面,“走”的比例过高。
此前有媒体报道,南方某高校曾以“特聘研究员”“师资博士后”等名义,6年引进8000余人,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能留下。
东部一所水利高校商学院的留美海归刚刚经历“走”的全过程,“7月初学校人力资源处通知我不再续聘,8月就停了工资和五险一金”。
另一方面,“升”的标准较为单一。
“‘非升即走’说起来简单,只要6年内评上副高就行,但难点是‘国字号’基金项目中标率很低。我的课题经费、论文数量都够,就缺‘国自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所以一直评不上副高。”一所“211”高校的90后讲师说。
实际上,高校青年教师不仅要忙科研,还需承担教学和日常管理事务,但一些学校的考评指标对这些方面体现较少。
“作为一名教师,我肯定想把课上好,备课至少要花掉全年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但在考评指标里,一学期上两门专业课的评分,不如发表一篇C刊论文。这种‘重科研轻教学’的考评导向,我感觉不太合理,用心教学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一所“双一流”高校90后讲师说。
“非升即走”变味侵蚀高校生态
大学应当是全心全意做学问、面对诱惑不盲从的地方,一些高校目前的考评导向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侵蚀创新精神、学术“近亲繁殖”、轻视教学育人等消极现象。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杨希对1099名高校理工科教师的问卷调查发现,“准聘—长聘制”改革后,教师群体的职业不安全感增强,对失败的容忍度下降,为了保证准聘期内有成果产出,或多或少“不敢”尝试新方向或新方法。
东南大学数学学院副研究员孙烨通过挖掘论文数据库,分析了近900万篇论文署名和引用信息中包含的24.5万组师生关系。结果显示,学术成就呈现出一定的继承模式。
此外,一些高校“非升即走”的考评“指挥棒”轻视教学育人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教学和科研“两张皮”现象。有的教师不愿花太多精力备课,有的教师日常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关心不够。
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蕴哲观察到,这一矛盾在思政领域更为突出。“上好思政课关键是沟通心灵,需要教师以身作则,走到学生中间。”陈蕴哲说,一些青年思政教师不得不将重心放在申报项目、发论文、拿奖项上,课堂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多措并举规范“非升即走”
平衡好激励和淘汰的关系,合理确定淘汰比例。
“大学治理现代化不能狭隘理解为企业化,‘准聘—长聘制’也不等于‘非升即走’。”陈蕴哲建议,聘任制改革宜分类施策,明确哪些高校、学科宜于试点,科学设定淘汰率;针对部分高校“非升即走”引发的法律争议,教育、人社等部门组织专项整治,全面审视聘用合同、考评体系是否合理、合规。
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弹性设置准聘期。
苏州大学东吴智库副理事长陈一建议各学科根据自身实际,在6年准聘期的基础上弹性安排,学校、院系也应为新进教师提供完善的科研配套条件,特别是以“老带新”等方式帮助他们尽快融入。
在教师考评方面立体多维,培育“教研相长”的高校生态。
“教书、科研和管理,都是高校教师的工作内容。大学既需要科学家也需要教育家,科学家当然可以同时成为教育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事处处长、高级人才办公室主任崔海涛建议,“破立结合”推进教师评价改革,一方面突出教书育人导向,另一方面实行多维综合评价,完善包含教学、管理等事务在内的立体评价体系。
陈蕴哲还表示,有不少学科存在知名学者同时牵头多个省部级以上课题、青年学者多年未中一题的情况。因而,需为青年学者存留发展空间,如在立项环节为他们开辟专门赛道。
此外,针对我国高校师资供求失衡存在地域差异的情况,中西部不少高校仍面临人才缺口,需重点增强其人才吸引力。
(摘自《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