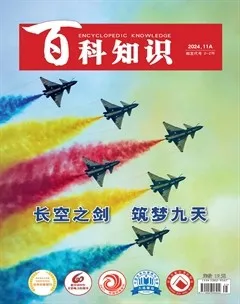古代宵禁那些事儿
在近期热播的剧集《唐朝诡事录之西行》中,我们看到长安城的宵禁十分严格,夜晚时分,守卫宫中及京城安全的金吾卫便会严格巡查警戒。宵禁,通常也称夜禁,是一种出于维护公共安全、社会秩序或救灾需要,而采取的以限制民众活动范围的方式来管控夜间人员流动的措施。由于现代社会仅在特殊情况下,于特定的时间、区域临时采取此措施,所以当代人对宵禁已较为陌生。但在中国古代,无论皇宫、都市,还是关禁、县城,都将宵禁作为一项制度性的常规措施。宵禁深刻影响着百姓的日常生活,近代以后才被逐步取消。
宵禁缘起
由于古代夜间照明设备有限且效果不佳,加之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习惯,所以古时入夜后,人们一般都居家休息,遇有紧急之事往往也是“日行百里,不以夜行”,以避免走夜路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在此情况下,为了防范有人趁夜深人静外出行“奸邪之事”,古代的城市管理中很早便设置了专员来司夜。
至迟成书于西汉的儒家经典《周礼》中记载,周代有“司寤氏”根据星辰起落来确定禁止人们夜晚出行的起讫时间,并率部属进行巡察。东汉永宁元年(120年)颁布的《禁夜行诏》要求“钟鸣漏尽”后,京师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唐代将宵禁列入律令,每天时间一到,负责人员便开始击鼓,届时城门、街口都要下锁,街区间无法通行。之后的朝代一般都有宵禁。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在离京赴任前到欧阳修家辞行,就是因被留饮酒而未能在宵禁前离开,只得与欧阳修痛饮了一夜。边城、县城也要严格执行宵禁。明人胡安描述宵禁后边城固原(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刁斗风清初禁夜,毡帷月冷尽防秋”,一片肃杀之气。清代诗人钟淳崖喜好饮酒,一次喝醉后违规夜行,被当地县尉施以杖刑,他每挨打一下,“辄呼爽快”,被时人传为笑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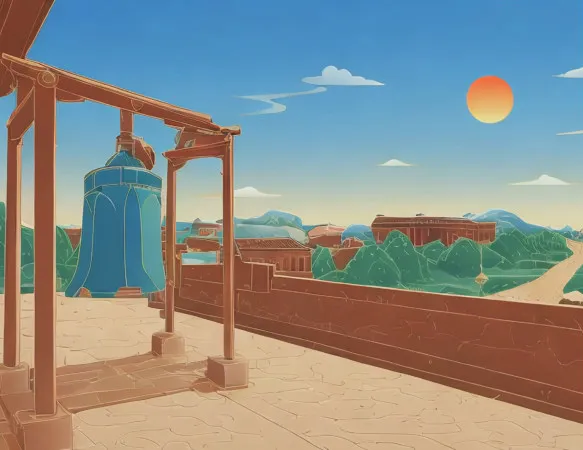
钟鼓传音
宵禁通常是以鼓或钟为号,故又有鼓禁、钟禁之称。唐初,“京城诸街,每至晨暮,遣人传呼以警众”。贞观十年(636年)“始置街鼓”,宵禁前擂响600下,结束时擂响400下,“时人便之”。元代的宵禁以钟为号,并规定宵禁期间寺庙不能敲钟。但由于元朝统治者尊崇佛教,故对寺庙的宵禁要求并不十分严格,甚至有的地方还借寺院之钟来进行宵禁报时:“凡寺之甲郡县者有钟焉,而有司因之。甲夜扣之一百有八,人皆闭户休息,行于路者为犯夜,有禁。昧爽(黎明)以前复扣之一百有八,先行者为犯早,亦有禁。”
古时也有钟鼓并用的情况。东汉蔡邕在《独断》中言:“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鼓鸣即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明清时期的宵禁是晚上先击鼓后敲钟,早晨先敲钟后击鼓,即所谓“暮鼓晨钟”。
宵禁的时间,一般是“一更三点禁人行,五更三点放人行”。古时一夜分为五更,每更相当于现在的2小时;一更又分为五点,每点相当于24分钟。19点入更,一更三点即20点12分,五更三点即4点12分。有的朝代还会根据冬夏时令来微调宵禁时间。
宵禁时,会有专门人员负责巡逻、执法。如元大都(今北京)在夜晚“有三四十人一队的巡逻队在街头不停地巡逻”,如果遇到犯夜之人,便会“立刻将其拘留”,待天明后交有司处罚。在元杂剧《玉清庵送错鸳鸯被》中,巡夜者在宵禁期间发现了外出约会的刘员外,便道:“这早晚更深夜静,见一个人走将去,那厮必定是贼!”于是将刘员外捉到自己办公的巡铺,吊了整整一夜。这些巡夜人员在巡逻时还须携带夜巡牌,牌上一般写有“关伪防奸,不许借带,违者治罪”“持此夜巡”等内容。
令行禁止
宵禁期间,城门关闭,民众不能随意外出,违者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汉末,曹操任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部分区域的治安)时,有权势的大宦官蹇硕的叔父便因违反宵禁而被曹操依法棒杀。金代章宗时,右丞相完颜襄等一众高官因给御史大夫唐括贡祝寿而违反了宵禁规定,第二天便遭到了降官或免职的处罚。元代的宵禁规定更为细致,宵禁期间不但禁止百姓随意走动,聚众做祈祷、祭祀等事尤为不可,违者将受到笞刑(用荆条等抽打背部或臀部);如犯禁后反抗拘捕以致伤害执法者,则要被处以杖刑107下。只有执行紧急公务、急病、死丧、产育等特殊情况,获准后才可通行。
当然,也有人利用此类规定从事不正当的活动。如在清代小说《歧路灯》中,一名夜间外出聚赌之徒就曾利用急病不在宵禁之限的法律规定,以为母抓药为由多次应付过了巡夜人员的盘查。这虽是文学作品中的描写,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宵禁制度中存在的漏洞。
历史上,在宵禁期间,甚至一度不允许百姓在家点灯。如元初来华的马可·波罗就曾描述,宵禁期间,杭州城内有“一部分守卫沿街巡逻,查看是否有人在宵禁熄灯的时间里还点着灯火。如果发现有人违反禁令,他们就在这户人家的门上作一个记号,第二天清晨,把这家的主人带到衙门里审讯。如果事主不能为他的违禁行为给出正当的理由,就要受到处罚”。
上元弛禁
宵禁也并非日日皆禁。
唐代,从武则天时期开始,为了庆祝上元节(后世多称为元宵节),允许正月十五、十六两天不再施行宵禁,以便百姓张灯纵乐、彻夜欢娱。此后,历代皆延续了上元节期间暂停宵禁的传统。北宋自仁宗以后,更规定每年冬至到上元节期间,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华门以北的城区都不再宵禁。时人有诗描写上元节期间的夜晚景象:“前时官家不禁夜,九衢艳艳烧明缸。彩山插天众乐振,游人肩摩车毂撞。”明永乐七年(1409年)颁令:“自正月十一日为始,其赐元宵节假十日,百官朝参不奏事,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弛夜禁,著为令。”这10天成为那时一年中最热闹的光景。
夜深灯火
宋代是古代宵禁史上的特例。北宋晚期宵禁已经松弛。当时传统的坊市格局已被打破,商业活动不再被限制于固定的市场之中,商铺可以对街开门,人们的夜生活随之逐渐丰富。为了方便民众在夜间聚饮,还出现了代办宴会的“四司六局”,其中“油烛局”负责灯火照明。诗人刘子翚在《汴京纪事》中“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的名句,读来使人眼前仿佛出现了当年汴京城里的火树银花。南宋时,宵禁之法已成具文。杭州笙歌鼎沸,勾栏瓦肆灯火通明,“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偏远之地也是如此。陆游有诗云:“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
在传统社会,军事行动和犯罪活动常靠夜色掩护而得以进行,宵禁无疑是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有效机制,但同时也压抑了人们对夜生活的渴望,夜市、夜宴等商业、休闲娱乐活动无法开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夜间照明设备和治安状况今非昔比,宵禁制度早已不合时宜,最终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