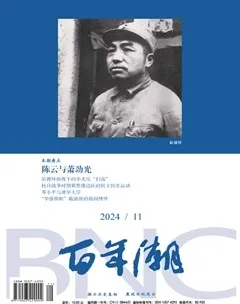在空军地勤工作的回忆
明玉清,1932年生于辽宁鞍山。1948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选入空降兵,同年转入第六航空学校学习。1951年,在空军第十四师第四十二团担任机械师。1952年至1953年,两次参加抗美援朝空军作战,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奖章。1951年、1952年、1954年,因参加国庆检阅,荣获三等功3次。1977年8月,转业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保障处,后为正处级干部。1992年离休,享受副局级待遇。
少年参军
记得父母曾对我讲,因为贫穷,我的父辈举家从山东逃难至遥远的东北边陲—漠河县。北大荒一年之中只有三个月无霜,农作物难以成活,我们只得迁徙至沈阳以南谋生。1932年,我出生于辽宁鞍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并在伪满洲国推行奴化教育。饥饿如影随形,每一餐都可能是最后一餐,汤水、野菜、杂草乃至树皮,都成了果腹之物。我生下来就营养不良,3岁时还不会坐。父母说,要不咱就把这个孩子送给人家得了。结果送出去,不到7天又被送回来,怕死在人家那。
到14岁那年,我已能陪伴父亲赴鞍山谋生,负责饲养两匹马,只为换取一日三餐。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4月,解放军征兵的消息传来,我毅然报名参军。家里生活发生了转机,土改分得田地,父亲成为农会干部。1948年5月5日,我正式入伍,年仅16岁。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我作为重机枪手随部队北上,参加黑山阻击战,阻止国民党军队经由营口撤退。我与战友们徒步穿越漫长的路途,从鞍山到辽西。那年月,道路未经硬化,泥泞不堪,偶尔可见两条车辙印在泥中,沿途食物与清水皆成奢望,路边的积水混杂着各种杂质,渴得没办法,也只能喝这个解渴。
直到我们抵达辽宁省台安县,司务长费尽周折,总算寻得一处驻地。可是,当地刚刚解放,家家户户的条件都十分有限,有的家炕未干,有的则因有新生儿不宜打扰,我们便选在一片雪地安营。司务长买到稻草,每人分得一捆,当作褥垫与被盖。半梦半醒间,淳朴的村民们被我们触动,其中一家五口主动邀请我们进屋避寒。我们婉拒不成,最终接受了群众的好意。军队的严明纪律赢得了群众的尊重与信任,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信念。
黑山阻击战后,沈阳宣告解放。随后,我们随部队编入警卫师。后来,我与战友们一同调到北京,加入刚成立的空军司令部。1949年6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末,我们在南苑机场学习空军地勤。随后,部队让我们这些文化基础薄弱的陆军转空军人员先进行了三个月的文化补习,再深入学习飞机发动机理论等专业知识。
赴朝作战
1952年初,我们部队赴朝轮战。飞行员paLAp2zc8/rGeFJZdd6PsXPzj96h7Ed0JsM/YyswEzk=在尚未完全掌握平稳起飞与降落的技巧时,便投身战场,在实战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初春时节,我们的部队抵达丹东(时称安东)大虎山,那里的临时机场十分简陋,跑道由稻草铺设底层,上面覆盖钢板,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团第一次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主要执行空战任务。值得一提的是,我所负责的飞机的飞行员是新中国第一位拥有大学学历的飞行员。飞行队伍的其他成员,则大多来自陆军部队,我们的飞行副团长,就是陆军炮兵营长转行的。
地勤主要负责保障每一架飞机的完好状态,确保随时能投入战斗。作为地勤团队唯一的党员,面对任何技术难题,我都冲锋在前,力求解决。我们住在当地村民家中,一个仅有三间房的小院却挤着七口人,他们慷慨地让出一间房给我们。我们十几个人挤在地铺和炕上,共同抵御寒冷。每天凌晨三点,无论风雨,我们都准时起身,徒步五公里训练,途中不乏艰难,特别是在途经的高粱地中,锋利的高粱茬时常划破脚掌。那种环境里,正是老百姓的默默支持,坚定了我们斗争到底的决心。
记得我有一次发了高烧,房东大娘得知后,用省下的两个鸡蛋和一碗面条为我送来温暖。当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这无疑是宝贵的食物。我得知鸡蛋是特意从邻家借来的,内心更是久久难以平静。
1953年初,东北局势依然不稳,美国飞机频繁穿越鸭绿江进入中国领空,在中朝边境上空进行轰炸和扫射。我们团再次入朝作战,驻地是丹东凤城机场。我们在凤城南边,苏联部队在凤城北边,苏联那边有高射炮,我们没有,所以美国飞机专门到我们这边来扫射。他们俯冲下来扫射一阵,然后迅速逃跑。有一次,敌机低空扫射,当时我正站在飞机旁边,根本无处可逃,也没有什么障碍物遮挡,只能在机场跑道上躲避。

之后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副大队长在空中发现敌情。按照常规,发现敌机应先报告,然后分配任务:谁负责攻击,谁负责掩护。但这次副大队长看情况紧急,指挥僚机直接冲了过去。这一仗,他击落一架敌机,击伤另一架,还在抗美援朝群英会上获得了表彰。回国后,他在某机场担任基地主任。不幸的是,他在一次飞行事故中牺牲了。我常常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
第二次作战一直打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虽然驻地条件相对之前有很大改善,但因缺乏高射炮,我们也吃了不少亏,敌机总是在我们头顶扫射。1953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了疯狂的轰炸。那时,我们的空军没有太多实战经验,主要靠勇气和毅力,边打边总结经验。由于飞行起降时不稳定,我们地面的指挥员需要不断调整,为飞机引导降落。停战后,为确保安全,部队仍继续保持警戒。
1953年8月,部队撤回河北通县。地勤人员先行乘坐运输机回国,有敌情时就赶快降落。当时刚飞到辽阳,就因敌情紧急而迫降。等敌机走后,再次起飞,不久又在唐山机场迫降,最终到达通县。
金门上空执行作战任务
1958年10月10日,我部奉命前往福建,参与对金门的战斗。部队接到起飞迎敌的命令后,我们机械师迅速行动,先行将降落伞放入座舱,飞行员们及时赶到。随着起飞信号弹的升空,部分飞行员甚至来不及完全装备完毕便紧急升空。国民党军方面出动6架飞机,而我们则以8架迎战。我的一位挚友担任8号僚机,在激烈的交锋中,他英勇作战,成功击落敌机一架,击伤一架。但是,他的飞机也受损严重,在万米高空被迫跳伞,却不幸遭到国民党军防空部队的射击,英勇牺牲。那时他新婚仅仅20天,让人痛心。
此次空战,我们取得击落敌机两架、击伤一架,活捉一名飞行员的战果。基于人道主义,我们最终决定将俘获飞行员放回台湾。
后来,我们先后两次秘密执行特殊使命,乘飞机前往西北核试验区域进行核爆取样。起初,任务的具体内容对外严格保密,只告知起飞时间和飞行路径。我们跟随指示,完成了取样任务。记得回到兰州时,军区政委亲自邀请我乘坐他的软卧车厢。政委坚持让我同行,并叮嘱保密。直至后来解密,我才知道那两次任务非同一般。

后来,我随部队移防到了天津。
驻地紧邻一所监狱,为防止潜在的风险,我们每人配备枪械,夜间枪不离身,时刻警惕。随后,我又被派往包钢工作。
1992年离休后,我负责老干部支部工作。这个支部里主要是学校后勤人员,共18个人,其中12位是抗日老战士,如今只剩下3位。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带领这几位老战士来到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加了一场特殊的仪式。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我们4位老战士佩戴勋章和纪念章出场之际,围观的群众纷纷致意,场面十分感人。
我相信,只要我们保持着这种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着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不可战胜的。(责任编辑 崔立仁)
整理者:刘昊,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郭永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