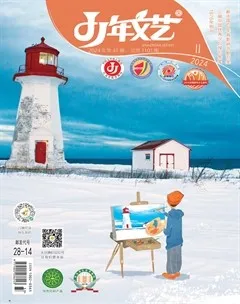食在山城

从地铁站出来之后,迎接我和好友的便是一阵湿润的桂花香气。
路两旁的行道树高而密,上面藏了星星点点的桂花,耐心地熏遍了穿行这座城的所有风。
这便是山城的秋吗?天色仍有些暗暗的,灰白的天上有大片的阴云,灰白的楼又是格外地高,一幢幢地矗立着,上面是一层层密布的窄小灰色调窗格。
行走在重庆的路上,在高高的钢筋水泥建筑面前,我渺小得好像只是一粒细沙。
在旅店安顿好,黑已侵占了天幕,我肚中馋虫也叫嚣个不停。
夜点上了街角的灯,我们没有选择住在景区附近,可没想到这居民楼下的火锅店,生意也是红红火火。隔壁是一家烧烤店,外面也坐满了人。街边摆满了相似的折叠桌,塑料凳倒是五颜六色,像是成心要冲淡重庆那一抹浓郁的灰底色。相邻几家的凳子定是不一样的颜色,你家用蓝色,我家就用红色,避免食客坐错了店,这是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
“两位,坐里头吧。”跑堂的大叔飞速地递过来一张菜单,黑白的,上面只打印了菜品和价格,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
这应该是我做得最快的一张“考卷”:炸酥肉、滑肉、麻辣牛肉……我迫不及待地勾选上了我最喜欢的那些答案。
锅底上得很快,一大锅红汤带几块白腻的牛油,铺满了花椒和大红色的辣椒。老板见我们盯着锅里那几块小小的饭粒团,连忙介绍说:“这是醪糟,放在锅里增香的。”重庆话虽说也归属于官话的一支,还是带了些西南风味。
汤面有轻微的波动,没过一会儿,红汤就在大火的作用下开始“咕嘟咕嘟”冒泡。重庆火锅就像一列快节奏的轻轨,带你呼啸着穿过黑漆漆的大楼,让你在猝不及防的瞬间瞪大了眼睛,还来不及细看,红汤就咋咋呼呼地开了锅,各色香料的气味夹杂着辣椒的呛,直钻鼻孔,咳嗽声不断催促你赶紧开吃。轻轨在片刻之间穿了楼,当你又惊诧地望着车窗外灰蒙蒙的嘉陵江时,它再来个拐弯,你还没反应过来,第一块滚烫的鸭血就顺着你的嘴,也拐了个弯,丝滑地流进了远道而来的胃里,就像第一滴雨融入江中一样自然。
外面噼里啪啦下起了雨,火锅也作势不断哗哗翻滚,孃孃们不慌不忙地支起了棚子,这顿饭才刚刚拉开序幕。
鸭血这种熟知的搭档,通常只负责唱一出短暂的开场红,惊鸿一瞥后便老老实实地沉了底,等到熟了便乖乖地浮起。你若暂时不想吃,它便在你涮其他食物的时候,在锅里浮浮沉沉地秀上一点存在感,让你时不时也来上两筷子。我随机选择了离我最近的一碟肉,长竹筷一夹一放,就能淹死一撮新鲜的毛肚,滚滚热浪中,它没几秒就蜷起了边,曲缩成卑微的模样,这是蛋白质投了降,再放任它在红汤里荡两下,便可以送入嘴里。嫩肉片则是一整块儿的梅花肉,七瘦三肥的黄金比例,十分厚实,属于荤菜中犒劳胃口的头号选手,保证爽口的同时也不会太过油腻。
腹中填了些食物,就像小孩子口袋里坠了心爱的石头,沉甸甸的,有种摸得着的稳妥。这时候,人的注意力未免就会涣散些。
店里人声鼎沸,锅里红浪翻滚。左手边一桌的娃娃费劲地扒拉着锅底,苦苦地和一片肉鏖战,麻辣牛肉明显是潜水的一把好手,还善于伪装,自己化了一身红,融进锅底。可惜娃娃的筷子用得还不太娴熟,让那食物狡猾地逃脱了好几回,怪不得川渝出去的火锅牌子要叫“海底捞”呢。右桌的几位伯伯则忙着摆龙门阵,聊得热火朝天,旁边喝剩的啤酒瓶摆了一摞,火锅只是话头的配菜,这桌聚会到了下半夜,还得转移阵地,不知道会辗转到谁家的机麻桌上,他们便在推弄麻将中,默默反刍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独家情报。
“老板,加菜!”其中一个伯伯招了招手。
“好嘛!这就来!”做事麻利的老板一呼即应。他朝后厨高声喊着:“加菜!两份牛肉!再来五瓶啤酒!”他又顺手给我们上了一碗蛋炒饭,“这是免费自助的,后面还有冰汤圆,你们可以自己去拿。”
桌上的菜其实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蛋炒饭加上火锅,碳水叠加油脂的双倍快乐,恐怕只有重庆才会有,只是我的肚子毕竟不是长江,实在是装不下这么多。我们俩商量着一人一半,勉强吃完了掌心大小的一碗饭,最后又盛了半碗凉虾解腻。
饭毕,出了店,雨还是淅淅沥沥,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巴山夜雨的名头,大概缘由于此。
不知道是不是吃撑了的缘故,我走在路上总觉得被什么东西绊着,走也走不快。好友听了我的疑虑,不禁失笑提醒:“这是上坡。”
我这才回头看去,后面稀疏的车流都比我要矮些。原来,不知不觉中我在爬坡。
回到旅店,就着雨声,一夜好睡。
我们想尝尝当地的早餐,于是选择出去碰碰运气。跟着地图导航,靠着热心群众的指路,一路七拐八弯来到小区里。成片的树荫绿意葱葱,店就藏在这团静谧之中,幸好,还开着。门口吊着一盏昏黄的老灯,老板正在滚一碗汤面。
路边简简单单地搭了个棚子,食客坐在临时摆设的塑料板凳上,优哉游哉地品味这清凉无事的早晨。风带了几分湿意,我深吸一口气,仔细嗅闻,总感觉是下了一夜雨的缘故,今早的桂花香气只是微弱地残存在空气中,变得若有若无了,又或许是我熟悉了这气味,久在桂花之中不闻其香了。
我抬起衣袖确认,吃了这重庆的火锅,虽是睡过一觉了,身上也还沾有隐约的火锅味,可算得上入乡随俗了。隔壁的女孩在闲聊,好像是想邀朋友去家里做客,旁边一人便要推脱,几人说得有些快了,便像上了“区域锁”,外地人分辨不出具体的内容。重庆话都是火锅味的,重庆人说话就像油炸得噼里啪啦的花椒一样热辣焦香。
正闲思中,孃孃殷勤地端上了一碗油茶,上面撒满了炸得金黄的碎馓子,底下是绵烂的米糊,米糊并不是雪白的,而是带了重庆天色一样的灰调,中间混着小葱还有香菜,边缘带了一圈圈的粉末。细细一看,稍微深一些的是胡椒粉,浅一些带了红的则是花椒粉,其余的调料也隐匿在这小小一碗糨糊状的混沌之中,拌上酥脆的馓子,在口腔奏上一段奇妙的圆舞曲。
酸菜鲜肉米线上了台,满满当当的一大碗摆在桌上,就着细雨飘出一缕缕热气。米线顶上堆叠着好几片嫩滑的瘦肉,汤面上漂着作为点缀的葱花,瓷碗的碗沿缺了一个小口。自家腌制的酸菜入了口,错落在米线上的豆芽还有木耳,自然也逃不过饕餮的筷子。
“妹儿,你们两个够吃吗?”孃孃走过来,坐在一旁问。
我嘴里正吸溜着米线,只能一个劲儿地点头。等咽下那口堵人的东西,我本想和她攀谈几句,没想到刚好又来了几个客人,孃孃便起身去招呼了。
三下五除二,我们两个人把油茶吃了个精光,又把汤喝得一滴都不剩,正好慰藉一下昨晚接待热辣火锅的肠胃,也和店主做最郑重的无声告别。
之后,我们在半山崖线走走停停,上坡下坡,难免走得饥肠辘辘。晌午时分,我们又踏进一家豆花店,开始新一轮的觅食。店里摆着长长的板凳,坐满了翘首等饭的客人。
七块钱一碗豆花,我俩一个红碟,一个青碟。我们再叫上一道烧白,一份水煮肉片。出门几天,都没有吃青菜,按我们的饮食习惯,必须得加一个炝炒通心菜作为点缀。
对于食物,我格外宽容,即使我一向吃惯加糖的豆腐花,也没有咸甜之争的偏见。豆花嫩滑,没有一丝豆腥味,就着有酥黄豆的自家调配的秘制蘸水,再来上一口肉,实在是巴适得很。烧白看似肥腻,但油脂不多,还带有芽菜的香气,我们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尝,通心菜就上了桌。作为广东人,我原先多少有几分在炒制时蔬技艺上的自恃,但这道小小的通心菜便叫我认了瘪,翠绿爽口,若把烧白比作一位浓妆艳抹的佳人,那通心菜便是万顷碧荷的清幽之景,多一分太俗气,少一分太寡淡,两者相辅相成,一起迷醉了味蕾,让我们差点忘了最后一道水煮肉片还没有上。
一位大叔见我们不停翻看火车票,便开口问道:“你们几点的车?要不要打包?”
我们说了时间,一旁的厨师头也不抬,手上动作依旧稳当:“赶得上!”
饭店就在火车站附近,厨师翻炒的速度明显要比普通居民区的饭店厨师快上几倍。只见他面不改色,手腕轻轻巧巧地一翻,最后一勺热油浇在大红辣椒上,嗞嗞作响。香气化了形,随着冒出来的热气飘进鼻子,那热气又转眼化作火车的那一缕,我们便带着圆溜溜的肚子,依依不舍地辞别了山城。
发稿/朱云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