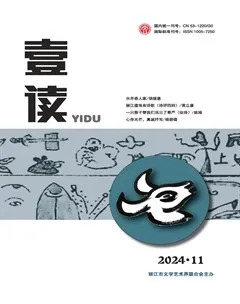心存光芒,真诚抒写
杨映红是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七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的学员,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生活中,杨映红给人的印象是温暖、开朗、活泼的,就像丽江的阳光,时刻在照耀别人。这种感觉,分毫不差地移植到她的诗歌里,给她的文字增添了温度、光芒和风采。不过,与生活中的她相比,诗歌里的她明显有更加丰富纵深的主体形象,还不仅仅是一道“阳光”可以形容。我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写作者,哪怕与他(她)朝夕相伴也是不够的,必须深入到他(她)的文字中,才有可能窥见其灵魂的褶皱,洞悉其心灵的森林。
抒情,是杨映红诗歌的发声方式。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有情要抒,不吐不快,是她最基本的写作动机。杨映红的诗总有一名“抒情主人公”,在替她“说出”之时也在构建着她的诗歌面貌。从句式上来看,这些诗多由短句构成,我们几乎找不出一个曲折牵绊、复杂蜿蜒的长句。短句是作者性情的生动写照:明朗、健康、清爽、利落。其背后则包含着某种肯定的意志:杨映红的诗歌书写是一种“再次确认”的行为,通过写作,她再次框定、确证书写对象的意义、价值。例如,《母土》一诗写故乡丽江,“古城与雪山一起,就是一曲清笛/对母土的眷恋/在体内奏响,生长”,这一抒情要达到的目的是对故乡的礼赞,以及对自身故乡情结的二次强化,“愿将余生的爱都交付于你/一点点浸入你/丽江,我的母土!你听到了吗”。同样是云南地域题材的《洱海》是一首运思巧妙的情诗,诗人写洱海,是因为“此刻多想喊出声来/对天空和浪花/大声说出我们的爱情”。诗中,“我们的爱情”是既定的事实,是现在进行时,不需要论证,只需要“喊出声来”,而“喊出声来”正是对既定事实(爱情)的再次确认。通过确认式的抒情,杨映红让情感价值与诗歌书写彼此叠加,不断强化肯定式的诗歌伦理。她的诗不负责疑问、探讨、反对,只负责守护既有的价值,升华既有的情感。
搞清楚这一点,再反观杨映红诗歌风貌的明朗与健康,清爽与利落,会发现她的诗是表里如一、诚实可信的,从而亦可理解她诗里难得的松弛感。也许有人会说,杨映红生活在丽江,丽江不是世外桃源吗?在这个地方写出的诗,不松弛才怪。实则不然,生活并非桃源,哪有从天而降的轻松。将丽江与轻松划等号,要么是善意的想象,要么就是有意的营销。杨映红在《松茸》一诗里透露过自己劳累忙碌的丽江生活:于他人而言,对丽江的美好回忆里,少不了盛夏的松茸,“去年丽江一夏,只爱上/这点青绿”;对她来说,盛夏则是辛勤采集松茸的季节,哪有什么“远方的诗情”,“松茸约等于丽江/我却沦陷于山野//远方的诗情,与我/从未遇见”。综上所述,杨映红诗里的松弛感,并非因为生活在丽江,而是因为她的诗写行为与价值理想是同频的、互证的。在这样的逻辑洽和下,才会有自如的节奏呼吸,有朗朗的精神。
母亲、爱情、自然,是杨映红书写的三大主题。《年味》《母亲的样子》等诗,都在表达对母亲的深爱和牵挂。严格说来,她写母亲的诗数量并不多,但“母亲”在杨映红的诗里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身份镜像,构成了她诗歌的伦理基础。在《诗人》里,她如此表述母亲与自己、自己与下一代的关系:“母亲把我写成一首诗……当我做了母亲/生活,是另一首诗。”通过对“母亲”的凝视,诗人完成了自身某一个侧面的身份指认。在这一伦理基础上,她的诗歌抒情才得以徐徐展开,持续锻造着宽容、良善、富有深情的品质。
爱情,是杨映红常写的另一个题材。《赠你洱海蓝,慰我苍山白》《爱上夜》《暗藏》《人入琴》等,都是完成度不错的抒情短诗,处理得节制又不失心性。在情诗里,杨映红的状态是自然打开的,她不羞于表露自己娇羞的、小女人的一面,“小猫”就是其形象的自画像:“一只小猫/怀抱着甜蜜的爱情/期待,白昼的到来”(《期待·白昼》);“我是一只调皮的小猫/在阳光下追逐笑闹”(《就在这一刻静止》);更不耻于表现自己野性的一面,“你慢慢扩展了夜色/我被抽离,掠取/融入游离的暗物质”(《蛊》);“把带有蜜的诗句/揉进你的魂魄/从此,你就是我的了”(《哪怕支离破碎,也要引发一场雪崩》)。要辨析的是,杨映红诗里的野性并不是无根的、孤立的,而是与柔情相伴相生的,是身体、欲望与爱的天然协奏曲;与现代人孤独的、病态的、不彻底的爱相比,她笔下的爱是一种积极的力量,给人源源不断的滋养,使人走向完整,而不是更加破碎。我认为,情诗是最能展现杨映红诗歌特色的文类,在情诗书写中,她能做到收放自如,浑然天成,且展现出一个不可多得的女性视角——这个视角交织着她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真挚,勇敢,淋漓;同时又包含着能被普遍感知的共属经验与世界经验。这些情诗,是真正富于活力的、生机勃勃的女性创造。
杨映红笔下还常常出现大自然。对大自然发自内心的颂赞,是这些诗的共同母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诗都是“同一首诗”,只不过变奏出了各不相同的面貌。无论是写西南边陲,还是写内蒙风光,杨映红都饱蘸热情,用自己的语调大方地说出,喊出。她有几首关于丽江中洲的诗,写得很用心。《油茶罐》开篇即言“穿过风,穿过雨露/让这个带有乡愁的油茶罐/从一堆粘土里生长”,此处将油茶罐人格化,与乡愁相连,赋予器物以人的情感;另一首《幽深的巷弄》,用的则是比喻,“中洲的巷弄,是古老的志书”,将巷弄与历史相连,赋予建筑以时间感。这些诗的修辞技巧并不难,难的是大方地说出时,还能保持大地感、生活感和融入感,还能存留一抹拙朴的风致。这些诗让我看到,杨映红在写作中不追求讨巧,她是实打实地面对书写对象,尊重它们,以真心相待。正因如此,她才能写出“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从远古而来的河流逆流而上/用干净的额头/抵达神的天堂”(《科尔沁》)这样打动人的句子,才能用平等亲切的眼光去看待大草原上的另一个民族。
一个诚实的写作者是幸福的,当她以诚实面对写作时,写作会回赠她更珍贵的东西。更何况,这位写作者还是“心存星光的女人”(《明亮的忧伤》),更是被阳光普照着的。我衷心祝福杨映红在未来的写作路途上,能采撷到更多的芳华与果实。
责任编辑:和丽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