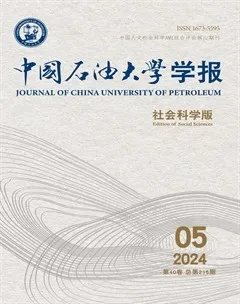霍菲尔德法律关系理论下的环境权解构

摘要:作为分析法学的重要应用工具,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理论以严谨的思辨性契合了环境权在属性、主体、权能范围、落实与前景方面的模糊与争议困境。综合既有的环境权探索成果,可以理想环境的生活权益、理想环境的享受权益、排除环境侵害的权益、排除环境破坏的权益、可持续利用的资源权益、获取环境信息的权益、参与环境维护与管理的权益、保护环境质量与承担损害责任的义务、维护代际利益的义务、主张与保障集体环境与资源利益的职责的解析为基本,并以生物权利、环境空间利益、环境权救济等落实问题为辅助,尝试形成既有环境权内容的完整逻辑体系,且在环境权的整体存在、整体实现等问题中得出分析结论。
关键词:环境权;霍菲尔德;法律关系;落实;前景;救济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4)05-0027-12
一、引言
环境权的法律结构及实现是环境法领域的典型命题。环境权具有元素要件复杂、权益类别丰富、权能范围广泛等特征,加上环境法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这项权利的分析难以取得足够透彻与严格的解构成果。而霍菲尔德在私法领域萌生的分析理论,以穷尽式的逻辑论证推演出法律关系的最小公分母[1],为环境权内容的环境法解读提供了理想逻辑元素与方法论。综合既有成果,将环境权内容分而化之,以霍菲尔德法律关系理论(以下简称霍菲尔德理论)重新阐释,并适时归纳该权利发展与实现的前瞻性结论,属于环境法学研究的有益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霍菲尔德理论并非环境权取得独立权利地位的终极依据,而只作为论证方法,尝试发掘该领域的若干学理要点。
二、霍菲尔德理论的简述
20世纪初,霍菲尔德发表了《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系列论文,提出了法律关系的元形式主张,以“right”“no-right”“duty”“privilege”“power”“disability”“liability”“immunity”8个概念组构起法律关系的概念原件[2]71-77,进而借助关联(correlate)与相反(opposite)两种主要关系[3],构建起自洽的逻辑架构(见图1)。从原理上突破了传统法学“权利—义务”的对向关系与基于经验归纳的列举性阐述风格,并以前所未有的穷尽式逻辑分析态度形成法律关系解构的全新方法论。尽管霍菲尔德主要将这种理论应用于以商法为代表的私法关系范畴[2]72-75,[4],但霍菲尔德理论属于法学乃至哲学意义上具备普适性、原则性的操作方法[5],其影响甚至超出社会科学的范畴,同人工智能技术[2]120、数学二进制[6-7]等领域相关联,拥有极强的拓展潜力,为环境权等新型权利的解析创设出无限可能。
霍菲尔德之后,诸多分析法学家开展了霍菲尔德理论的研讨与深化。在中国,夏勇、张志铭、沈宗灵、王涌等分析法学家结合本国的法学实践,吸收汉语的表述精华,深度转化了霍菲尔德概念矩阵的内涵表述,实现了良好的本土化变革。[2]150,[8]结合环境权的理念特征与解读的完整性,本文采取“right——‘权利’(也称claim,后文同)、no-right——‘无权利’(狭义,也可用no-claim替代,后文同)、duty——‘义务’(此处不包括责任,仅指狭义概念)①、privilege——‘自由’(指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的自由,不同于哲学意义或传统法学意义上的广义概念)、power——‘权力’(属于改变他人法律关系的广义解读)、disability——‘无权力’(参照power解读)、liability——‘责任’(受power行使影响)、immunity——‘豁免’(不受power行使影响)”[2]127的观点,以便开展环IWO8NBodVwcuydJNPN38oQ==境权的专门建构。值得一提的是,霍菲尔德理论除了关联与相反关系外,还存在矛盾关系[9],这将在环境权解构中涉及。
三、环境权的争议与霍菲尔德理论的解构
(一)环境权的争议简述
环境权理论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自《寂静的春天》一书发表后,有关公民生活在良好环境中的权利争议逐渐引起各国的广泛重视[10],引发了环境权的学术辩论与决策变革。随着相应观点的内涵丰富与体系成熟,各国逐渐衍生出环境要素的权利组建乃至救济独立化取向,并发展出公共财产[11]、公共信托[12]、生态利益中心主义[13]、环境要素主体化[14]12,138等关联成果。然而,在环境权益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因其区别于传统法律制度的预期内容与实施机理,引发了诸多纠葛与模糊。结合中国的法治实际,存在如下待明晰之处。
第一,环境权的权能属性尚待明确。针对环境权的特性,学界存在人类权[15]52、自得权[16-17]、社会权[15]122、私权[18]乃至反射利益[19]等主张,形成个体权能与集体权能、天然权能与衍生权能、完整权能与单纯利益乃至预期利益之争,进而产生权利认定与法律解析的学理障碍。
第二,环境权的关系主体存在争议。这类争议同环境权的属性之辩息息相关。一是坚持环境权作为传统私权的学者,倾向主张环境权的行权主体应为个人。二是坚持环境权作为人类权等集体性权利的学者,倾向主张环境权的行权主体应为国家或特定区域的群体(甚至全人类,如代际利益说)。三是坚持环境权指理想环境维系的学者,倾向主张将非人类生物甚至自然生态纳入主体考量范畴,从而与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等观点对接。[20]202-214
第三,环境权的权能范围较为模糊。对于环境权的权能内容,有学者认为具有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双重属性。[21]有学者认为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等。[19]有学者认为环境权是主体享有清洁、健康等良好环境的权利[22-24],因其客体不确定,故不宜直接划分内容范围。总而言之,环境权的内容争议不仅对权利本身的明晰造成影响,也直接反映到对环境权设立与保护的必要性证成上。
第四,环境权的落实存在障碍。一方面,环境权的权属不明使法律难以就此权利设计相对完整的行为规范与保障限度。另一方面,即使学界或公权机关借助既有法律规范的针对性阐释拓展出环境权的保障空间,也难以在救济程序中确定清晰的维权主体与行为资格,加上涉及其他利益冲突、举证工作艰难、审理级别与周期难以规范等因素干扰,环境权的实现面临重重困难。
第五,环境权的发展前景尚无定论。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环境权的壮大势必涉及利益中心的明确。就学界主张与维权实际而言,环境权仍重点关注人类利益。但随着法哲学思维的嬗变、人与环境“隔离争端”空间的客观缩减,以生态利益或人与生态共同利益为核心的主张日渐兴起,逐渐挑战既有的法理乃至哲学价值基础。此外,代际利益的兴盛也在未来利益的维护与预估方面塑造论证需求。
环境权的理念症结与既有法律关系理念的体系特征关联密切。其主体、客体、内容、属性等基本权利元素均不同于传统法律理念的权利结构,固有的权利—义务二元化取向与基于传统法治现实归纳的经验规则,已难以应对环境权的融入与环境法律体系的发展。即使不认可环境权的正当化与独立化,关联问题(如代际公平、野生动植物保护[25]、“景观”利益[26])的处理仍离不开新型法律关系理论的解读尝试。对应的,霍菲尔德理论以严格的逻辑推演,克服了传统法律理论依赖于静态经验汇总、缺乏应对新现象的方法的弊病。此外,霍菲尔德理论真正实现了对行为、利益、权能、损害等评价对象的全面覆盖,引入了“自由”“责任”“无权利”等诸多传统理论忽视的因素,有助于处理环境权关联的环境损害风险、主体确权评估、利益衡量等难以法治化的问题,具备显著的严谨性与全面性。
(二)环境权的内容解构
诸多国家在学术研究与法律规范中开展了概念范畴的探索。在学术方面,仁藤一、池尾隆良指出,“为了保护环境不受破坏,我们有支配环境和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基于此项权利,对于那些污染环境、妨害或将要妨害我们舒适生活的行为,我们享有请求排除妨害以及请求预防此种妨害的权利……”[27]随后,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拓展了环境权的基本概念。在法律方面,智利、菲律宾、阿根廷、保加利亚、美国、匈牙利、俄罗斯等数十个国家均以不同的形式规定了环境权内容。其中,对环境权做出相对完整阐释的当为《韩国环境政策基本法》、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环境权利法案》等法规。可总结出如下环境权概念的要点:(1)理想环境的生活权益;(2)理想环境的享受权益;(3)排除环境侵害的权益;(4)排除环境破坏的权益;(5)可持续利用的资源权益;(6)获取环境信息的权益;(7)参与环境维护与管理的权益;(8)保护环境质量与承担损害责任的义务;(9)维护代际利益的义务;(10)主张与保障集体环境与资源利益的职责。以此为基本,可形成霍菲尔德理论的分析内容。
1.理想环境的生活权益
这种权益关乎公民在健康、舒适的环境中正常生活,属于基本生存权范畴,也属于“权利”(+)与“权利”(-)的关系②。权利主体为自然人,义务主体为实施环境开发、利用、占有等行为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团体乃至国家。对于代际关系,存在当代人与后代人关于环境生活权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后代人属于想象中的“权利”主体,权利义务内容难以具体确定,且强行正当化也违背法不溯及既往(属于不利追溯)[28]、公正、可预期等基础理念,故不宜认定存在代际范畴的生存权关系。
2.理想环境的享受权益
这种权益属于公民享有目标环境状态的利益表现。在行为上,分为外在的观光与内心的感受。在对象上,指向优美、静谧、安宁、愉悦等环境特征。落实至霍菲尔德理论,同其是否关联其他类别的要素息息相关。
首先,若权利主体行使享受权益影响他人合法权益,则不应获得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一方面,主体双方应存在“自由”—“无权利”的关联,即权利主体享有享受理想环境的“自由”,义务主体不享有要求权利主体停止此种享受的“权利”。然而,另一方面,权利主体并不享有要求义务主体不干涉权利主体行权的“权利”,义务主体可基于自身合法权益,改变环境状态,形成互不干涉的特殊关联。在此,日本山口百惠案可作分析参照。山口百惠(演员)夫妇在山头修建了别墅,后因多人围观而建造了遮挡别墅的围墙,产生周围人士眺望权与夫妇个人隐私权益的潜在冲突,案件一度引发争议与疑难。[20]116以霍菲尔德理论分析,可认定围观群众拥有眺望权的“自由”,但不享有要求山口百惠夫妇不阻碍其权利实现的“权利”,以维护夫妇的个人隐私权益。
其次,当权利主体行使享受权益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损害超越权利的预期利益时,则不享有此类“自由”,而是负有不得干涉公共利益维护的“义务”(-),某种程度上甚至负有促成公共利益维护的“义务”(+)。例如,在三峡水库修建时,居民不得以自己享有对三峡的环境享受权而干涉该项目实施,负有“义务”(-);在堰塞湖爆破的过程中,周边居民应负有及时搬迁、支持爆破以维护公共安全的“义务”(+)。综上所述,可以之为模型,解构环境权在公共开发等活动中的取舍与维权现象。
最后,在权利主体行使享受权益不影响任何合法权益或影响的权益极其微小的情形下,权利主体享有要求义务主体不得干预自身权益实现的“权利”(-)。在部分特殊情形下,权利主体甚至拥有要求义务主体积极作为以实现享受的“权利”(+)。现实而言,针对其他公民,这项权能一般是“权利”(-),针对政府等公权力代表或特定社会组织,这项权能原则上应是“权利”(+),以充分维权。
3.排除环境侵害的权益
在自力排除方面,公民对实施侵害行为者拥有实施排除行为的“自由”,行为人则对应“无权利”要求受害者停止自力救济。值得注意的是,有必要研究受害者是否拥有改变他人法律关系的“权力”。例如,若行为人与他人签订砍伐某处山林的协议(在民事规范、行政程序等方面合法),当该砍伐行为将造成风景破坏、水土流失而损害当地人权益时,尚不清楚受害者是否拥有经法律授权、确认该协议无效或可撤销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存在理论空间,但应由法律严格限定,即只有在相应协议对环境的损害或预期损害达到严重(如影响到公民健康或造成显著财产损害)程度的前提下,才可认定该损害具备引发“权力”的条件。单纯的环境享受权难以满足这项“权力”的要件。
在公力排除方面,涉及环境侵害的救济权实现问题。本文重点分析司法救济的落实情形。首先,需讨论救济权的主体问题。对于生存权范畴的环境权能,公民自然拥有请求行为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恢复应然环境状态等“权利”。然而,相应“权利”的实现应以司法机关支持诉讼主张、并得到顺畅执行为条件。③在此,权利主张者、行为者、法院形成了三角关联,即法院就环境权侵害对主张者负有公正裁断、执行裁决的“义务”(+),而这种“义务”(+)的实现又构成行为者与主张者间“权利”落实的现实条件。当然,行为者提起诉讼本身也行使了法律赋予的“权力”(诉权行使),进而引发法院“义务”(+)的产生,形成了环境权诉讼救济的完整关系流程。其次,还有必要论证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等集体诉讼的关系变更,进而明确环境权的拥有主体。实质拥有环境权的主体应限于自然人,而不包括国家、团体等集体力量。类似于法律拟制的法人人格[29],代为行使权能的实质应是权益实现的条件之一,与法院履职的“义务”(+)无实质差异。若认定组织拥有环境权,不但将形成集体性环境权的界定与权能结构重建的需求,更将产生集体与个人权能的冲突、环境权沦为公共决策的博弈工具等风险。在逻辑层面,这种权能的实现效果最终仍归于具体个体,如恢复环境的利益享受者仍为特定地区民众,并未产生霍菲尔德理论意义上的法律关系“翻新”,仅形成集体组织代表公民正当行权的“义务”(+)(基于该类组织的社会义务与职责,不宜认为其享有“自由”),民众则拥有要求正当行权、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权利”(+)。
4.排除环境破坏的权益
这里的环境破坏排除不同于前述环境侵害的排除,代表了一种社会责任感或道义自觉。例如,针对名胜古迹的开发行为,未必损害个人法律上的实质环境权益,但作为环境共享者及社会共同体的参与者,公民理应享有排除这种妨碍的“自由”。当然,基于法律关系的相对性与社会交易的稳定需求,公民不享有排除与变更相应行为关系的“权力”。而针对公民是否享有请求行为人排除损害、恢复原状及请求公力救济的“权利”,可分为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基于社会秩序与利益权衡考量,尚不宜开放排除环境破坏的自力救济窗口。公力救济可再分为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在行政救济上,应认可公民拥有这种“权利”,以借助举报、举证等方式,辅助行政机关惩处违法行为。在司法救济上,根据既有法律规定,只有直接受到损害者与特定的社会组织及国家机关才可分别以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环境权益,而不直接涉及其合法权益的普通公民尚不具备提起诉讼、消除环境破坏的“权利”。然而,公民拥有请求救济环境破坏的“权利”(此为针对司法机关的),理论上既有利于保护环境,也可增强民众的环保与责任意识,唯一顾虑的便是泛滥的环境诉讼阻碍正常的经济开发与行为者生活。因而,未来可在完善环境诉讼受案条件与程序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在均衡中协调公民、行为者与公权机关的利益关系。此外,日本、美国等国家曾出现公民与动植物联合起诉或代理动植物起诉[14]12,198等全新的诉讼形式,也可归入这类权益范畴。在承认生物主体论的前提下,认可公民的司法救济请求“权利”有助于阐述全新诉讼的法理基础。
5.可持续利用的资源权益
与环境污染防治对应,针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公民同样可在合理的权益范围内拥有“自由”与相应“权利”。
普通资源可分为生存型、发展型与享受型。生存型资源主要包括水、大气、土壤等基本要素,公民对此不仅拥有享受相应资源的“权利”与“自由”,甚至也拥有不当处分的“豁免”与单方解除相应协议的“权力”。例如,企业与当地居民签订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协议,后因生态恶化、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存,居民应拥有解除该协议、要求企业停止利用与开发的“权力”,也需得到法律明确。发展型资源主要包括特定矿产资源、可再生能源、特殊元素、具有经济价值的林木等。在中国,部分资源属于全民所有,针对全民所有的资源,作为个体的公民负有不得随意使用的“义务”,作为集体的人民则拥有使用该资源的“自由”,通常由特定管理机关代表与行使。当然,若国家行使“权力”,即将相应资源赋予个人利用,则该个体拥有使用该资源的“权利”,也应负有妥善使用该资源的“义务”,而不可拥有随意使用甚至废弃该资源的“自由”,义务相对方应是集体意义上的人民。当然,若该主体违反法律规定或出现特殊情况,则国家可行使“权力”收回相应权益,并自然拥有请求不当行为者赔偿损失的“权利”。享受型资源主要包括名胜古迹资源、特殊风景资源等,公民所拥有的权益关系与理想环境的享受权益类似。当然,公民理应负有不破坏当地环境、保障相应资源价值存续甚至增长(如历史遗迹的价值随时间流逝而可能增长)机会的“义务”,对应的“权利”主体应是全体人民,由国家来代表。
特定的资源种类存在特殊的关系形式,有必要对土地资源与公物资源做出分析。对于土地资源而言,中国实行土地公有、房地一体主义[2]219等政策,对应的环境权益也存在与物权关系的微妙联系。其一,针对承包土地,公民拥有使用并排除相应侵害的“权利”,却不享有处分完整的“权利”与“自由”,甚至负有不得随意处分或浪费的“义务”。在此,似乎可补充公民维护土地生态价值与存续能力的“义务”,以形成完整的维护链条。而土地使用人与出让人也应通过协议或政府指导等途径,实现科学的权责分配。其二,针对土地与房屋的使用,当房屋所有者出让相应房屋时,自然转移了该土地本身的环保义务及基于相邻关系而产生的环保义务,进而形成“权力”的存续必要。在此,应考虑在法律中明确相应赋权,将这种“权力”融入物权转移或房屋买卖的合同等文本中,并尝试纳入成本考量范畴,借助市场指导价等形式,使不同环境负担的房屋、土地对象拥有不同的出让价格,以支持后继者的环境权益维护。其三,对于国家对相应土地的征收与征用,存在环保义务的转移与损耗价值的考量。例如,国家临时征用相应土地后,使用人便暂时除去了征用期间维护环境的“义务”,并产生在此期间存在的环境损害的补偿“权利”。若为征收,这种损耗应计量至对应的补偿价格体系中,予以合理的数值筹算。公共资源是指大气、阳光、海滩等事实上不属于国家垄断、个人天然享有的存在。就公共资源而言,公民之间的权益关联应是“自由”—“无权利”,不可随意设定特定公共资源的垄断利益或特别的公权支持。例如,《黑龙江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将大气作为国家资源予以垄断性管控的做法,违反了宪法本意,也不符合霍菲尔德理论的形式规律,需加以改正。当然,在公民对公共资源的正当使用或享受遭到如“黑龙江事件”或破坏性开发等活动的侵害时,自然拥有自力救济与诉诸公权的“自由”与“权利”,“权力”的本质来源离不开宪法对公民人身权益的保护与人民主权理念的渗透,也产生了相应法律细化规定、完善救济程序的需求。
6.获取环境信息的权益
对于自然类信息而言,主要包括当地的自然环境状况、自然灾害发生概率及预期损害内容、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总量、非公共行为的预期环境影响等(不包括单纯享受类信息,仅指生存与发展意义上的环境信息)。公民应对公权机关拥有获知相应信息的“权利”与“自由”,原则上不应存在例外情形,以保障公民维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宪法性权益。换言之,国家或特定主体不得以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等为由拒绝公布相应信息,相应地免除公开协议对公民而言属于“无权力”范畴,不应产生类似效力。当然,公民理应寻求适当主体实施信息公开。若出现主体错误,原机关一方面享有不公布信息的“自由”,另一方面负有告知、传达、转送相应信息与材料的“义务”,以保证公民的环境信息权益实现。
对于管理类信息而言,主要包括环境合作计划、环境政策信息、环境法律规则、特定协议(如政府与企业的环境利用协议)、环境保护与利用战略及规划等。既有法律已经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的公众参与与信息公开环节实施了权责落实。分析其中理念,政府对公民不仅负有公开相应信息的“义务”,且负有认真对待信息申请、谨慎与清晰解释信息内涵等“义务”。若政府未能实施相应信息公开,可考虑赋予公民就特定开发行为或协议的效力排除“权力”(指向相应开发工程的停建、撤销及恢复原状,须经法定程序主张)。在救济权方面,无论是自然类信息还是管理类信息,除了涉及国家秘密或重大公共利益等少数情形外,国家应负有给予公民完善权益救济的“义务”。当然,公民在信息权益遭受侵犯、产生实际损害时,也拥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以实现权益的全面维护。
7.参与环境维护与管理的权益
与环境信息的获取与救济相对应,环境维护与管理的公众参与同样是环境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分为环境信息告知权、相关意见被咨询权与意见被慎重考量权。[20]408环境信息告知权已在前段详述,而相关意见被咨询权与意见被慎重考量权则体现为相关环境决策的全程深度参与。公民拥有对公权机关环境决策提出个人意见的“自由”与要求相关机关按照法定程度慎重对待与处理的“权利”,提出意见的环境权益对象不受到利害关联的限制,以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也符合环境利益多属于公有的特性。
相关意见的被咨询权重点体现为,公民提出意见的渠道与场所实现便捷化与丰富化、征求意见的主体广泛、征求意见的平台普遍、征求意见的频度足够、征求意见的流程清晰等要素。此外,公民不仅拥有法定内容的“权利”,在法律尚未规定的建议领域,也拥有要求公权机关谨慎考量的“权利”,以契合不断发展的复杂环境治理情况。意见被慎重考量权则在广度与深度上体现。广度而言,以环境影响评价为例,包括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在内的公众参与权,应以适当的程度与方式体现在项目审查、范围界定、编制草案、草案审查、编制报告书、后续跟踪与监督等完整环节。[20]406可采取法律规定或授权委托专门机构赋予“权力”等形式,实现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目标。深度而言,重点体现为相关意见的完整记录、体现与处理决定的理由阐释。在理论上,无论公民意见是否合理,公权机关均负有将相应意见记录并公示于相应文本的“义务”,尤其在拒绝采纳意见的情形中,公权机关负有详细阐明理由并接受公民复审的“义务”。
在公众参与的事后保障层面,一方面公民原则上对自身言论享有不受惩处与不利对待的“豁免”,公权机关就有效意见负有激励的“义务”或“自由”。除非相应主体恶意损害相应机关或人员的合法权益(如诋毁名誉),或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且造成实质损害(应由法律明文作穷尽性规定),此时公权机关有追究责任(重点为行政处罚)的“权利”与“义务”。受损害的主体自然也拥有追究不良行为的“权利”(以民事诉讼等方式实现)。另一方面,公民也拥有相应参与权受损的救济“权利”,且在特定情况下,拥有相应法律关系消灭或改变的“权力”(以法律授权为前提)。
8.保护环境质量与承担损害责任的义务
部分学者在论述环境权的性质时,认为其属于权利与义务的集成体。换言之,公民在享有环境利益时,也负有保护既有环境、承担相应损害等义务。然而,这种界定仍然局限于传统的权利义务二分法,并非严谨的逻辑推演。譬如,维护后代享受环境的利益便难以明确其权利与义务属性,也难以揭示环境权义务内容的特征,故有必要剖析公民的对应“义务”内容。
在维护环境质量方面,针对不同主体将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形式。首先,针对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权力量,存在多种可能。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特定的环境对象具有稀缺性、全民共享性、不可再生性等特征,公民负有维护其应有状态的“义务”。针对公权机关因行为不当造成的损害或风险,公民也自然拥有监督与救济的“权利”。在具有生态、经济等正面价值的私人环境对象上,公民相对拥有维护环境质量的“自由”,如对房前屋后的自种树木理论上拥有处置的“自由”。当然,这需确立在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如相邻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公民未能维护相应环境质量,也不承担法律责任,而是更多承受道德责难。在具有危害性、二次损害性等负面价值的环境对象上,公民在一定程度上负有拒绝维护乃至消除的“义务”。譬如,针对遭受化工厂污染的水源,面对潜在的生命健康等重大风险,工厂职员应负有及时隔绝污染源或拒绝继续排污的“义务”;对管理者而言,则转为要求其停止不当行为的“权利”。综上所述,保护的环境对象应是具备健康、清洁、自然等特性的理想环境。其次,针对私权主体,如非公有的经济资源、庭院环境等,则负有不得擅自损害的“义务”及维护相邻权益实现的“权利”。当然,在达成合法协议的情况下,也可通过“权力”的行使,产生消除相应义务的“豁免”与“自由”。最后,针对后代的潜在利益,理论上负有维护应然状态、保证后代必要生存与享受机会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义务”并没有法律“责任”对应,折射出霍菲尔德理论与传统义务观的区分。
在承担损害责任方面,公民针对私人致害负有恢复应然状态、赔偿损失的“义务”;针对公共致害(如温室气体排放致害),则不负有直接的法律“义务”,在特殊情况下,负有受到特定举措影响的“责任”,如公民受“双碳”战略的相应“减排”规则规制等。在特殊情况下,公民也负有承担替代责任的“责任”。例如,在紧急污染事件中,若责任主体难以直接承担恢复责任或难以即时联系,可由第三人承担替代责任,其间产生的“权力”促使第三人拥有向责任者诉求补偿的“权利”,责任者自然拥有补偿的“义务”,并负有承受相应法律关系约束的“责任”。某种程度上,这种“权力”离不开环境公益性与公共信托关系的实际影响。
9.维护代际利益的义务
代际利益的维护已经超出法律范畴,更多体现为道德、伦理乃至自然定律的作用。然而,这并不影响霍菲尔德理论在该领域的概念解构。这一方面源于霍菲尔德理论具备超越法律的普遍适用属性,另一方面也源于代际利益属于环境权的重要部分,离不开法律关系的规制支持。所谓代际利益的维护,实为当代人对后代人所负维持应然发展机会的“义务”。面对无法确定的法律主体及潜在利益,需摆脱传统法学理论生硬的权利义务严格对应习惯,创设出霍菲尔德理论的价值。
可以魏伊丝归纳的3个基本原则剖析代际“义务”的应然内容:一是各世代保证将来世代拥有环境选择权利的“义务”;二是各世代保证后世代享受与前世代相当的环境质量的“义务”;三是各世代保证过往继承的环境遗产能够被后世代所接近的“义务”。[20]492-493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这种“义务”并无明确的“责任”对应,即使当代人违背了前述“义务”,通常也不存在法律上的严格责任或法律关系影响,而更多存在道德与伦理责难或自然定律致使的物种灾难惩戒,显示出传统法律理论无法解决与容纳的阐释领域。二是将来世代的利益享有并非明确与静止的,事实具有期待与调整属性。在期待方面,这种利益包容的“自由”“权利”“权力”“豁免”需附加当代人遵循自然定律与社会经济规律、做出应有行动等条件,属于附条件的“权利”(作为一个总的权益实现诉求而存在),以阐释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在调整方面,这种利益并非等同于当代人的环境状态,实际应计入当代人正常生存与发展所产生的环境损耗。针对该种损耗,当代人既对后代人拥有行为“自由”,也拥有不受拘束的“豁免”。当然,当代人不享有针对想象主体的“权利”,以遵循客观事实与法定原则,这也是将后世代享受的环境质量水准解释为“相当”,进而只赋予其“接近”过往环境遗产权利的重要原因。至于这种代际利益能否得到法律救济,将有赖于相应权益是否足够明确、利益是否足够重要、主体是否可能代表等因素的作用,予以特定领域的适度正当化。
10.主张与保障集体环境与资源利益的职责
鉴于环境权的所涉利益往往属于普及范围不特定、难以量化与切分的对象,产生了主张与实现的团体性需求,有必要分析公民环境权实现的集体性利益的法律形式。
在环境团体的组成过程中,应分为两个层次考量。一是公民单纯行为层次,即公民组成环境团体以维护利益的行为分析,应属于“自由”,有关单位不拥有强制公民加入相应团体的“权力”与“权利”。二是公民利益的实现层次,即公民在法律上实现相应利益的条件应属于“权利”(以组成团体为条件)层次。若相关利益的司法救济只能由特定的环境团体提起诉讼,而不能由公民个人诉讼解决,则公民“权利”的实现需以组成符合法定条件的集体为前提。
在环境团体组成后,公民与团体间便产生特别的制约关系。在理论上,首先,在公民自愿加入环境团体后,代表性行为便产生影响公民法律利害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是由涉及组织建构法律的“权力”授予而来,形成双层结构。其次,公民拥有要求组织公正履职、不掺自我意志、平等对待等“权利”,而团体也对应拥有要求成员服从规定、接受拘束的“权利”,类似于协议关系。当然,与协议不同的是,这种制约在部分领域存在“涉他”可能。例如,在代表人诉讼方面,未参加该组织且未加入代表人诉讼的公民事后自行起诉的,可直接适用原有代表人诉讼的裁判结论。④尽管环境诉讼尚未完全适用该规定,但在代理救济日渐频繁的环境保护领域,这种现象的出现将逐渐常态化。最后,若组成团体的行为不当损害公民合法权益,则转化为侵权救济,对应产生相应的“权利”与“权力”等法律利益。而当团体公民的行为不当损害集体利益时,则产生“表面二分、实际一体”的救济格局。在实践上,集体组织自身与其他公民均享有要求不当行为者承担责任的“权利”,但因集体本就属于公民意志的体现,故集体只是其他公民的诉求代表人,不存在自身的救济人格,因而属于其他公民对行为者的单独主张。
(三)环境权的重要落实问题
在前述分析中,已经明确了环境权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下文将从生物权利的落实、环境空间利益的落实与环境权的救济3个方面分析环境权的落实问题,这3个方面分别代表了环境权落实的主体、类别与保障3个维度。
1.生物权利的落实
首先,对于人类与生物共同维权,美、日等国便存在以松树、鸟类与人类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的经历。以霍菲尔德理论分析,起诉人与生物作为原告整体,自然与被告及法院存在相应的“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等关联。然而,细究起诉主体与生物间的联系,存在法律解释的疑难。若个人与生物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够以法律规制,彼此间将必然存在相互影响的“权力”,而该“权力”显然难以由人为法律单一授予。毕竟,“权力”是源于人类利益的维护而非生物利益的规制。因此,至少在霍菲尔德理论的基础上,这种关系难以成立,进而动摇这种共同体存在与作用的基础。而且,彼此存在的不相互侵害的“权利”与“义务”也缺乏客观的实现条件。例如,个人要求生物不滥用其诉权的“权利”显然荒谬;而生物要求个人不滥用诉权的“权利”既缺乏保障救济,也难以实际主张,因为生物无法合理表达。综上所述,这种共同维权实际上是人类的自我意愿表示,所谓生物权利的维护并非生物本位的体现,某种意义上,是人类为保持生态系统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而采用的行为手段,并非目的,在法律上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约与理论基础。
其次,人类代理生物维权更显著突显了人类本位的实质。该代理难以在法律上产生任何实质的正当行为“义务”,属于一种道德约束。尽管霍菲尔德理论存在作用于伦理道德领域的空间,但难以满足权利的法律正当性与强制性要求。而相应“权力”的行使也实际属于人类的单方赋权,并非生物参与拟定与自由意志的表达,也难以正当阐释推定同意的缘由。综上所述,这种方式的维权难以定性为生物权利的存续。
最后,非生物享有权利是学界更为激进的观点,突出表现为生态利益的维护(如河流保护),其霍菲尔德关系结构同样面临着上述质疑。此外,非生物权利的法律阐释还将产生与物债关系的混淆冲突、与生物权利及人类权利的优劣评断、界定权利范围及种类的标准明晰、是否违背法律的强制性与可预知性等基本特性、是否动摇法律约束的权威与有效基础等一系列难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均难以成立。
2.环境空间利益的落实
环境权的内容不应局限于消耗环境容量与利用自然资源,还应包括对环境空间利益的占有。公民的安宁权便显著体现了这种空间利益,即享有某一特定的环境空间而不受外力不当干涉与限制的利益。这种利益往往附带于环境容量或自然资源的权利范畴。例如,在利用某特定的水域合法排污时,便客观占有了该水域的空间利益。由此,实际存在要求他人不得干涉这种空间利益占有的“权利”。而无论是现行法律还是多数协议,均未充分规定该种利益授予,进而阻碍了这种“权利”的法律认可。在理论上,缺乏“权力”的授予,该种空间利益难以独立存在与转让,现实中又存在安宁权、享受权、观光权、相邻权乃至居住权等一系列与空间利益密切相关,实质是这种利益分配与妥协的外在表现的权利形式,产生该种利益法治化、正当化的改革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利益与其他利益存在丰富的组合、影响空间。例如,当房屋所有者将房屋出租时,便附带了空间利益的转移可能,所涉情形相对复杂,若房屋所有者仅是将部分房间出租、自身仍居住时,相应的空间利益仅是个别转让,且不得干涉房主整体房屋的空间利益享有,从而存在空间利益的切分与彼此冲突的阐释可能,以霍菲尔德理论分析,租赁者既享有占有该空间利益的“自由”与要求房主不得随意干涉的“权利”,也负有不得侵占房屋整体空间利益的“义务”,此时,空间利益已事实超出环境法的部门或领域范畴,成为私法领域的重要利益组成部分;而当房屋所有者将房屋整体出租,自身在租赁期内不再居住时,该房屋的空间利益事实由租赁者完全占有,租赁者的前述“义务”得以消除,仅拥有相应的“自由”与“权利”。此时,前述的法律关系状态可因协议解除或变更的“权力”行使而产生相应变化。当然,这种“权力”同样需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最后,还需分析该种利益的转让限度问题。在理论上,空间利益权具有可转让性,如前述的租赁合同便可实现,但这种转让需附加不损害第三人空间利益及其他合法权益、法律明确授权、实际占有行为已经做出等要件(“权利”“自由”等实现条件)。现实中,该利益难以脱离行为人而“隔离”存在。换言之,即不宜在行为人未在某一空间存在时,便享有该份空间利益。
3.环境权的救济
在公民自主救济上,主要包括自力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等类型。鉴于已在前文加以论述,不再赘言。
在社会团体救济上,存在多层法律关系。在公k2X+c8W0Kri32qsXK5IoIw==民与社会团体之间,公民拥有是否选择团体救济的“自由”,社会团体则负有被按法定要求选择后接受相应委托、尽力勤勉的“义务”,形成了完整的保障体系。当然,公民在选择后,原则上负有社会团体正当行使“权力”的“责任”(特定情形下为“豁免”)与不得随意退出、保证环境救济稳定进行的“义务”。在公民与公权机关间,公民在社会团体不当行为时或在部分无法代理救济的情形中,拥有自主寻求公力救济的“自由”,公权机关理应负有接纳相应法定诉求的“义务”,并不可轻视对待。而在社会团体与公权机关间,法律关系类似于公民自主救济的公权类型。当然,二者均共同负有对公民保持信息公开、不得自行处分公民重大权益的“义务”,否则,对公民而言,不当处分行为是基于“无权力”状态下产生的“豁免”。
在公权机关救济上,现行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可作为代表。公权机关自然负有正当救济与履行职责的“义务”,而对应的“权利”主体应是民众集合体。在此,该民众集合体不仅包括可能影响的受害民众与受益者,也包括实施不当行为的主体。在理论上,公权机关同样对环境破坏者负有公正履职、落实程序与实体正义的“义务”,而这正是保障相关主体合法权益,实现环境治理与公正目标的关键。此外,根据现行法律,检察机关实际上并没有不受限制、主张公力救济的“自由”。一方面,在部分情况中,需由公民先行抉择,在不主张权益的前提下,方可实施相应诉讼行为。另一方面,救济的启动理论上并非“自由”,而应为“义务”。在公民不主张的情况下,属于附公民消极不作为条件的“义务”形式,主张公民中途不得随意自行诉讼的“权利”、对行为者等相对人的“权力”等均附此条件。当然,在某些只宜由公权机关救济的情形中,该条件调整为符合法定的程度与情形要求。
在国家救济上,主要是对某些普及全国的重大灾害或国际环境损害事件的救济。在国内,如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家对公民的某些补偿,便成为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当然,“义务”的产生也可能源于“权力”的行使,例如,针对大量进口至国内的具有高度传染危险的产品,相应协议便可借助“权力”的行使加以解除,进而产生损失补偿的“义务”问题。国际上,主要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环境损害补偿与风险分担问题。在此,需区分相应损害的缘由。若为国内诱因,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则可能负有救济受害国的“义务”;若为气候变暖产生的责任分担等普遍性问题,则更多依赖于主体自觉。在此,相应救济更接近于“自由”或附条件的“义务”。
四、环境权的前景展望
前述已全面解构了环境权的组成与实践,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将从整体意义上展望环境权是否独立存在、实现条件如何等问题。
(一)整体意义上的环境权发展
1.环境权构建的可能理由
根据已论证的环境权内容,其广泛分布于污染防治、自然资源、空间利用等环境法分支。此外,环境权在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领域也存在相应的实体与程序权益。显然,难以以单一的法律依据作为相应权利独立存在的论证基础,需从逻辑层面分析不同权能的共同特征。在此,尝试给出若干要点,以作为环境权构建的可能理由。一是不同种类的环境权益均以客观存在的环境为直接或间接的维护对象。值得一提的是,该类对象属于目的而非手段。二是相应的法律利益(“自由”“权力”“豁免”“权利”)与法律负担(“义务”“责任”“无权利”“无权力”)并非严格对应,普遍存在预期实现或附条件实现的关联空间。三是公民的权益实现离不开客观的环境损失依托。换言之,只有相应环境对象出现显著损失(包括预期或风险),公民方可主张环境权益;若未发生法律规定的环境损失,公民不可直接主张法律权益。综上所述,环境权的救济存在“环境损失—权利主体损失—诉请救济”的独特结构。申言之,整体意义的环境权均附有环境损失这一实现条件。四是环境权益内容存在主体的种族性拓展与适用的理论空间,如生物权利的拓展等,当然,这不代表法律规制的价值本位变动,而仅指方法意义上的拓展。若非环境权范畴的内容,如投资股票权利,则难以产生种族意义上的实质变动。
2.环境权可能包含的权能内容与结构
在识别出符合前述标准的环境权要素的基础上,还有必要讨论整体意义上的环境权可能包含的权能内容与结构。总结不同学者对环境权权能的内容主张,公民一方面拥有占有、利用或处置特定环境要素的有限实体权益,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实体权益的获取、落实与完满,有必要形成对应的程序性权益,共同组成环境权的整体。
分析前述解构的10项权责,存在强实体权益、弱实体权益、纯粹程序权益三大类别,究其界分标准,享有实质主张资格的“权利”型权益往往呈现较强的实体属性。与之相对,仅享有主张自由的“自由”型权益则以程序性利益为主,其实体利好并不明显。对于强实体权益而言,理想环境的生活权益当属典型。当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理想环境的享受权益、可持续利用的资源权益也会在“权利”属性占据主要的情况下归入强实体权益类别。与之对应,相应权益的程序利好更多是为了实现实体权益而服务,在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将会以实体权益的保障为优先,暂时牺牲部分程序要求,这在环境群体性纠纷中表现较为明显。对于弱实体权益而言,由于排除环境侵害、排除环境破坏等权益更多是以“自由”的形式存在,故相对注重程序救济的开展,关键在于保障特定主体的主张得到规范受理。除此以外,若理想环境的享受权益、可持续利用的资源权益等分支无法符合“权利”实现的条件,则也将以象征着程序救济的“自由”为主,归入弱实体权益的类别。对于纯粹程序权益而言,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维护与管理等权益内容由于并非直接针对环境要素进行索取,故本质上属于程序权,对应的实体利益仅是作为程序实现的效果反射。
除了上述3种类别外,维护代际利益的义务,保护环境质量、承担损害责任的义务,主张与保障集体环境与资源的职责3种内容,由于不属于权益性质,无法实施直接归类,但也可结合其中的实体与程序义务侧重,分析对应偏向。对于维护代际利益的义务而言,由于实体义务内容的确定需随着后代人的实际利益需求而做出即时估量,当代人更多只能根据预测形成不确定的内容规划,故不宜作为主要的保护对象,更多还是以代表诉讼的方式推进程序救济。以此观之,该类义务的属性应为强程序而弱实体。对于保护环境质量、承担损害责任的义务而言,需视对应主体是否拥有主张责任方承担义务的“权利”。若拥有对应资格,可归入强实体属性,若不拥有,则更多属于弱实体属性。对于主张与保障集体环境与资源的职责而言,需区分单数的人与复数的人。针对单数的人,其更多拥有要求团体规范行为的程序性权益,而不宜按其意思表示赋予实体性权益,以免限制CmWbR4woCZvSChOnU4/ngA==团体的活动或产生保护不当的现象;针对复数的人,即特定团体作为所代表或依托的广泛利益群体,此时,该类群体更多拥有要求特定团体及其相对方配合实现环境利好的实体性权益。与前述权益内容对应,环境团体也分别负有程序规范与实体目标达成的职责偏向。
综上所述,整体意义上的环境权可望包容实体或程序主导的权益分支群,并在合理的情况下辐射至对应的义务与职责内容,对应推行不同的优先落实目标。而在不同类别之间,本质上没有优先次序之分,更多是根据对应权益、职责、义务落实的成本与程序、实体内容的属性,决定分支要素的落实次序。考虑到中国环境法治的发展实际,整体意义上的环境权更多是发挥解释不同分支内容、证成对应分支内容保护的学理正当性作用,而非一并落实所有类别的要素功能。
环境权是否需要构建,关键在于整体意义上的环境权是否有利于维护相应的具体权益要素、实现不同权利内容的均衡发展、实现精简应用的目标。若改革者能以合理的法律规范容纳主要的环境权内容,则有利于实现精简应用的基本目标。而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可借助系统性优势,全面协调环境权与其他类别权利的冲突与分配,并为未来权利要素的拓展留出逻辑层面的阐释空间。当然,实践中的维护尚需依赖于完善的法律实现体系、足够的法治素养、严谨的法学理论研究、定期的法治审查等支持。就中国目前的法治现实而言,完整环境权的构建尚待基础夯实与理论证成。
(二)环境权整体实现的条件分析
在立法上,环境权的可能宪法依据主要为环境保护与部分人权条款,如宪法第9条、第10条、第22条、第26条,分别从容量利用、资源消耗、空间占用等角度予以深化。然而,宪法尚缺乏专门的环境权条款,因而阻碍了环境权的专门化。在法律层面,环境权的法律规定散见于环境法律及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关联规范,尚未形成彼此联系的协调脉络,进而反映至法律统摄的各下位规范中。可初步推断,在立法层面,环境权的落实尚只能以分散的权利要素实施个别保护,而难以整体主张。鉴于宪法的稳定性与不同类别法律“联动调整”的实际难度,在相当长的周期内,环境权的落实路径难以改变。当然,随着环境法典等综合性规范的出台,环境权的宏观依据或许能得到充实。[26]
在司法上,中国曾出现“某化妆用具公司被纪执岐等起诉大气污染案” [30]82-87 、“唐山市焦化厂被118人起诉大气污染环境侵权案” [30]122-135等涉及环境权主张的典型案例,显示出中国环境权诉讼的困境:一是法律依据不足,实践中难以顺利立案;二是裁判过程不公,举证责任倒置等特殊规定并未充分落实,难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三是诉讼形式难以契合实际。鉴于环境权的实际影响特征与原被告应诉与主张能力的差距,涉及环境权的诉讼往往以群体的形式呈现。然而,中国在群体诉讼及其纠纷解决上存在救济力度与范围等方面的不足,在环境权领域更呈现规制空白。此外,在涉及环境权利益的关联诉讼领域,中国亟待构建明晰属性、特别处理的鉴别机制,以免以其他部门法思维处分环境权利益,造成实际损害的弥补不足。例如,若将环境权视为物权处分,则在传统民法难以规制的代际利益、空间利益等领域,公民的“自由”“权利”等法律利益,往往转化为法律未曾保护的“无权利”甚至不得擅自行为或不得扰乱秩序的“义务”,从而违背实质正义。因而,未来有必要在环境权诉讼领域构建这种鉴别机制。
在执法上,环境权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属于公民自主行为的“自由”,公权机关不得随意干涉。然而,面对关联多数人利益的环境权案件,被动地接受公民主张难以实现环境质量的长久维持与公民权益的完善保障,也不符合行政效益与勤勉原则。因此,在诱发环境权维护的因子出现时,执法主体理应拥有法定的“权力”,以提前制止或调整相应行为,以免因信息匮乏、反应迟钝引发救济失位。值得一提的是,对法律尚未规定的环境权侵权情形,执法主体不应随意行为。此时,行为者享受对应“豁免”,事实也属于利用环境利益的环境权范畴。
在守法上,环境法尚未取得足够的社会认知与理解。公众往往将环境法认定为粗浅的环境保护管理政策或传统部门法的例外规定,而对于环境权等环境法的专属理论概念,则缺乏足够的了解与实践。鉴于环境权的主张历时周期长、诉讼流程曲折、易沦为补偿与协商的囫囵处置,因而也缺乏现实的行为自觉⑤,导致环境权落实的艰难与周期漫长。
五、结语
作为环境法领域的重大命题,无论是宏观环境权还是环境权的分支内容,均具备丰富的研究价值与理念构建需要。在既有法律规范与探讨成果的基础上,环境权内容的解析与再构建便成为该权利能否摆脱道德伦理范畴,成为逻辑意义上的实质法律权利的关键。以霍菲尔德理论审视,环境权主要内容的明晰可作为探讨其内在特征、决定是否具备完整权利要件的有利渠道。此外,作为方法论与跨法学属性的分析学说,霍菲尔德理论也将在该权利牵涉的环境伦理探讨、权利落实实践、发展前景预估等领域发挥出功效。
注释:
① 本文不带引号的权利、义务表述不同于霍菲尔德理论中的“权利”与“义务”,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内涵,自由、责任、权力等表述也是如此。
② “(+)”指作为的行为状态,“(-)”指不作为的行为状态。
③ 霍菲尔德理论中,存在附条件的法律关系实现形式,可以“权利(条件内容)”加以标记。
④ 参见《民事诉讼法》第54条。
⑤ 环境权的重点在于“权利”的实现,但没有“自由”层面的公民自觉主张,权益实现便缺乏根源。
参考文献:
[1] 王涌.寻找法律概念的“最小公分母”——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分析思想研究[J].比较法研究,1998(2):151-165.
[2] 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3] 刘杨.基本法律概念的构建与诠释——以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为重心[J].中国社会科学,2018(9):112-135.
[4] 张永健.物权的关系本质 基于德国民法概念体系的检讨[J].中外法学,2020,32(3):720-742.
[5] 雷磊.法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中国法学,2020(1):5-25.
[6] 纪格非,王约然.霍菲尔德法律概念的原点及其逻辑展开[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6(4):11-19.
[7] 金海,袁平鹏.语义网数据管理技术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
[8] 沈宗灵.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0(1):67-77.
[9] Glanville Williams. The Concept of Legal Liberty[J]. Columbia Law Review, 1956,56(8):1129-1150.
[10] 徐祥民.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04(4):125-138.
[11] 杨朝霞.论环境权的性质[J].中国法学,2020(2):280-303.
KcC8VX9UXaa2cSG4KYuVtFhK2Q7JMHFkrbMrCUXYOg0=[12] Carol M Rose. Joseph Sax and the Idea of the Public Trust[J]. Ecology Law Quarterly, 1998,25(3):351-362.
[13] 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2:77.
[14] 山村恒年,関根孝道.自然の権利[M].東京:信山社,1996.
[15] 爱蒂丝·布朗·魏伊丝.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与世代公平[M].汪劲,于方,王鑫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6] 王社坤.环境利用权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11.
[17] 蔡守秋.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J].现代法学,2013,35(6):3-21.
[18] 吕忠梅.沟通与协调之途: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1-349.
[19] 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J].法学研究,2000(6):129-139.
[20] 汪劲.环境法律的解释:问题与方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21] 朱谦.论环境权的法律属性[J].中国法学,2001(3):64-70.
[22] 蔡守秋.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84.
[23] 陈泉生.环境法学基本理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366-367.
[24] 周训芳.环境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6-229.
[25] 张震.民法典中环境权的规范构造——以宪法、民法以及环境法的协同为视角[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3):2-14.
[26] 刘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客观诉讼机制[J].法学研究,2018,40(3):39-50.
[27] 大须贺明.生存权论[M].林浩,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97.
[28] 杨登峰,韩兵.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地位和适用的例外[J].金陵法律评论,2009(1):23-29.
[29] 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M].朱岩,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63.
[30] 王灿发.中国环境诉讼典型案例与评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82-87.
责任编辑:代海燕、康雷闪
De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Hofields Theory of Legal Relations
ZHOU Xu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application tool of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Hofields theory of legal relations fits the ambiguous and controversial dilemma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terms of attributes, subjects, scopes of power, implementation and prospects with its rigorously critical nature. It is of great likelihood to formulate a complete logical system of existing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draw analytical conclusions from forward-looking issues such as the overall existence and overall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exploratory studies and aided by analyzing the following implementation problems. The existing acquired results include rights of ideal environment to live, ideal environment to enjoy, exclusion of environmental harm, exclusion of environmental damages, sustainable usage of resources, obtaining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bligation to protect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assumed liability for damages; whereas the implementation problems may cover as biological interests, environmental space benefits and relief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ights; Hofield; legal relations; implementation; prospect; reli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