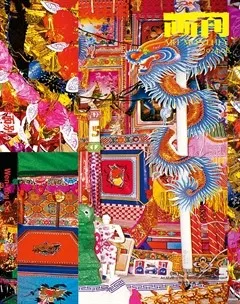绘画与图像诸问题:基于特稿文章的笔记
绘画与当代
围绕本次特稿“绘画、摄影、电影——如何思考今天的‘图像状态’”这一主题,展开而言,首先在当代艺术的领域,尤其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我们被大量的“图像性”绘画包围;这里的“图像性”指的是绘画对于某些具体的、具象的、扁平甚至商业化图像的生产,这一现象背后明显受到资本因素的左右。在艺术市场与社交网络中,即便复制甚至抄袭一个鲜明可辨的图像,也会易于被广泛流通和传播。另一方面,亦有来自波普艺术对于中国当代绘画的深远和直接影响。这样,在当代艺术的世界,绘画似乎依然被图像紧紧裹挟,绘画独立的创造性与处理历史的能力被图像性所挤压和扁平化,图像性的绘画既重新回到了古典艺术的逻辑闭环,也因其极强的商业属性而甘心成为全球流通的商品。就此而言,从事架上绘画的艺术家与研究当代艺术的理论家,用汪民安著作的题名来说,即主张“绘画反对图像”[1]。
另一方面,在图像性绘画不断投入市场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潮流的另一个方向,即架上创作中绘画性的显著回归:艺术家以绘画的笔触痕迹,以身体力行的工作过程,反对将这一复杂的事业简化为一个个直观的图像——这当然可作为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之中来自绘画的抵抗力量。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对于媒介特性与形式语言的强调,对于笔触、颜料与绘画性的怀恋,反而回到了“现代主义—形式主义”的滥觞,而早已进入教材的课本与博物馆的殿堂:我们是否在波普艺术与后现代之后的当代语境里,在图像与商业的重重藩篱中,又不得不退回到20世纪现代主义的保守境地?
在绘画的图像性与绘画性之间,在强调绘画性的道路是当代还是保守之间,福柯在论马奈时所创造的“实物—画”(the painting-object)[2]的概念颇具启发性(这一概念在李洋的文章中得到了详述)。在福柯看来,肇始自马奈的现代绘画,艺术家在画布之上对于媒介性与平面性的实验,当然首先突破了所有文艺复兴以来绘画的三维空间幻觉,使现代艺术在古典世界图像的崩塌处得以被发明。而与此同时,马奈的绘画既符合“现代主义—形式主义”的一贯主张,既凸显了笔触的未完成感与画布的平面性,也在这样的创作实践中,触及了绘画本身的物质性;也即,当绘画被“现代主义”地还原为一张平面画布时,绘画本身作为物的属性也得以被唤醒;或者说,是物的力量穿透了完美的形式,让绘画意外朝向了当代视野的“物的转向”,进入一种“物导向的本体论”。就此而言,我们既可以说马奈是现代绘画的开端,或也能在这样的作品中体会到某种当代性,“实物—画”由此超越了现代或当代的理论范畴与时代分野,为我们思考当代绘画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实际上,根据李洋的研究,早在古罗马时期的希腊哲学家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e)那里,便已有将绘画与物质造型相区分的意识:在古典艺术的世界里,绘画因其在二维平面营造视错觉的功能要求,因其专注于图像生产的社会任务,而忽略了绘画本身的物质特性,忽略了画布、颜料既是创作主体用以虚构一个视觉王国的工具,也本就是实实在在的物品——即便当现代主义绘画被纯化为一张空白的画布,画布自身也拥有其物质属性与纤维肌理。就此李洋通过对于西方古典与现代艺术史的回溯,通过伦勃朗、戈雅、透纳乃至印象派艺术家的工作,指明了物质性彰显于绘画之中的历史证据与多种可能,也在蒙德里安、德·库宁、罗斯科等现代艺术家的身上,揭示出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弊端与不足。这是在形式主义的经典理论之外、另一个版本的“现代绘画的兴起” ,同时也提醒我们反思在现代艺术史的语境之中,拉图尔所言“我们从未现代过”[3]的警示。
同样在艺术家的话语中,在当代绘画对于图像的反对里,杜尚早已明确表示要放弃一切有关“视网膜”的绘画,放弃可见的图像,让艺术回归观念与大脑、回归物与现成品。里希特在他的笔记里,同样称自己的绘画不是去描绘一个实物、一个客体,而是绘画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客体,本身就是与树木、水果、生活无异的东西;因此绘画可以没有内容的再现,没有象征的意义,没有任何理由、目的和功能,这是在里希特看来当下绘画的重要品质(里希特进一步补充说,即便如此,即便绘画可等同于物品,但作为艺术作品的绘画仍有好坏之分)[4]。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从物质性的研究方向上,在李洋看来,绘画便与当代艺术中的摄影、影像一起,甚至与雕塑、装置与行为表演一起,得以在同样的创作空间里、在同一的展览场域中,走向合作与融合。这既更新了我们理解现代绘画的理论路径,也明确了绘画来源其自身历史的合法的当代性。
当绘画成为一个实物、一个东西,它便首先告别了再现法则对于创作与观看的约束;换句话说,绘画不再仅仅致力于创造一个可见的图像,而可以透过可见性指向不可见的物质和力量。反过来讲,是规整的形式与世界的图像,让绘画的物质性在历史的发展中缄默不语,让绘画的力量服从于古典与现代的秩序管控;而在作为物的绘画中,在“物的转向”的视域下,绘画的物质性发挥出了自身的力量。绘画的媒介特性不再被形式所赋予的边框制约,它更加粗放、更加野性,也更加自由。它不满意于现代主义唯形式论的固有解释,也有力地打破了艺术史的时代分期与权威笼罩。释放这种物质性的力量,意味着绘画不仅从图像的世界中突围,意味着绘画不仅反对图像,它还在不断成为图像、消解图像与树立一个新的图像的动态过程中进行着自我批判:绘画在反对图像的同时也在反对自身,它在这样的反对中显示艺术的批判性与生命活力。这是一种格罗伊斯所说的“艺术力”[5],是绘画艺术在一个尼采式的力的世界而非图像的世界中的所作所为;它在艺术市场、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的各个自成体系的规则中,随时扮演搅局者的角色,随时准备声讨包括商业图像在内的任何一种总体性的统治。绘画的艺术力应该让我们看到力量的强度而非力量的消匿;看到多种力量关系的动态制衡而非自以为中心的稳定状态;看到绘画创作中有关图像与形式、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更多探索可能,而非对于已有视觉经验与思维模式的懒惰重复。
图像理论与技术哲学
实际上,如果来到图像理论与技术哲学,则在福柯的“实物—画”与格罗伊斯的“艺术力”之外,德勒兹也在与加塔利合著的《千高原》中,探讨了物质性力量对于形式的冲破。他在“物质—力量”的关系中,在物质性对于力量的纯粹表现里,提出了“图表”(diagram)的概念,认为“图表性”的思想运动,即是在形式的规范中释放物质的力量,在单一的图像里找寻另一种未知可能。而这样一种去除形式、席卷图像、凸显身体性的思想运动落脚到艺术中,便在弗兰西斯·培根的绘画里得到了相当直接与明显的呈现。在此一方面,正如培根与现代绘画大师们的紧密关系,在形式与图像的夹击下捕捉绘画力量的行为,实际上在马奈以来的“实物—画”中便已有所发展,这一线索隐秘地联结了现代绘画与当代艺术;而另一方面,德勒兹所言的“图表性”绘画正是对于图像俗套的反对,它将绘画拉入到对于图像、形式解域与辖域相结合的运动之中,让绘画成为一段生成运动的过程而非某一具体图像的结果,成为在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也在图像之确切的实现与虚拟的潜能之间的来回跳转。绘画对我们的视觉与触觉、眼睛与身体的器官进行重新联结,让我们的身体与艺术家一起成为“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
此外,“图表”的概念也极具理论的预见性和穿透力。在哲学史中,德勒兹经由康德的“图式”(schema)发展出“图表”,使得艺术与哲学均通过图表在中心式的总体系统中揭竿而起。而在今天,当我们面对人工智能技术,面对ChatGPT、Midjourney等应用工具,则可轻易地发现,AI技术所理解与创作的绘画,无非依据对已有数据库的拼接整合、对图像俗套的改头换面,也无非取决于对用户语言的描述要求。也即,AI绘画是典型的“图式性”绘画,它无法被任何一个从事当代绘画工作的严肃艺术家所认可,其图像的细腻、平滑与似曾相识,恰是发挥“图表性”绘画用武之地的所在。
在德勒兹那里,图表在破除与生成图像的运动之中,使其自身与绘画作品介于有形与无形、可见与不可见、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之间,就此,图像也便既是可见的,是稳固的视觉对象,亦可脱离物质性的载体而独立存在,可作为潜在的精神活动的一个环节而成为“精神—影像”。图像的这一特性无论在德勒兹《电影Ⅰ》《电影Ⅱ》的论述里,还是阿比·瓦尔堡寓于《记忆女神图集》的精神挣扎中,均可得到体察,即图像之内在性的欲力与情动。可以说,在福柯看来,马奈发现了在图像表皮之下绘画的物质性与不可见性;而在德勒兹处,则图像的崩形换来了物质—力量的觉醒。与此同时,图像也在分裂的运动中解放了自身,解放了视觉再现与物质媒介对于图像的长久束缚。由此我们看到,围绕视觉艺术图像的物质载体研究,业已成为西方艺术史由古典而至现代某种经典的讨论基础。相形之下,无迹可寻的精神图像,其路径复杂、隐秘甚至疯狂的运动,其从可见性与再现性之中挣脱的自我繁殖的拟像姿态,则既可画出抵抗已有研究共识的逃逸线,也朝向了联结今日数字时代虚拟影像的可能。
继而,这样的图像的精神性与无物质性,也令人联想到中国传统哲学与绘画之中的图像问题。以巫鸿著作《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介与再现》[6]的题名而言,在他对于中国绘画不同形态的广博讨论中,则绘画既是一种物质形态,也是对于图像的生产。也即,绘画既是一种媒介也是一种再现,它同时具有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这其中,绘画的物质性对应其媒介特性,也即图像的载体;而非物质性则对应图像本身,它是虚拟的再现建构,它可以超越物质性的限制而在不同媒介中变换和显现。媒介与再现在中国绘画的历史中呈现出互相的否定与对立的张力,呈现出另一种“绘画反对图像”。由此,绘画与图像的区分在中国绘画的语境中同样得到了剖析,同时也提示我们:围绕图像之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以及这一系列特性与绘画艺术本身的关联,无论在中西方艺术史与当代艺术中,还是在福柯、德勒兹的图像观与中国绘画的历史和当下中,均值得展开更进一步的比对研究。
实际上,与图像客观的物质属性相比,主观的无物质图像自始至终便存在于中国的绘画与书法艺术之中,存在于“有生于无”的古老哲思里面。在此,东方图像的本体论不再关乎物质,图像不再仅对外部的客观世界负责,不再依托物质媒介得以被看见;而显现为精神世界之中自在的运动,“无物之象”在中国艺术家对于气韵生动的意境追寻里,一度占据着主导与核心的地位。这样一种东西方围绕图像而展开的跨文化思想图景,便在2024年举办于法国里昂的第36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中,成为李洋作为分论坛主席的主旨议题。分论坛的研究以“无物之象”的自由流动,以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学者的图像研究,回应世界艺术史大会“物质与物质性”这一颇显西方中心主义的统一命题。在此之前,在2022年第12期的《画刊》特稿中,朱青生、李洋作为特稿策划人,亦以“中国图像理论与中国图像的研究”为题,对此提供了充分的讨论根基。本期特稿作为一次尝试的回响,也作为一次具体的延伸,便希望在此基础之上,从“绘画、摄影、电影”的不同形态中继续思考东与西、古与今、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图像状态”。
那么,围绕图像的理论和实践,我们也从乔泓凯的特稿文章里惊异地发现,现代图像研究在第一时间便与摄影技术相结合,而浮现出“作为摄影师的瓦尔堡”的形象。我们知道,在现代图像理论奠基人瓦尔堡那里,其迷人的“记忆女神图集”工作,与他的人类学考察密切相关。而在瓦尔堡那次著名的北美印第安之行中,他便携带相机留下了大量的摄影照片。在这里,首先,身为业余摄影家的瓦尔堡,其所拍摄的照片多有技术失误的失焦;而有意思的是,通过蔡子璇的研究,失焦这一摄影图像的独特视觉表征,便与技术哲学紧密捆绑。通过瓦尔堡之外的摄影艺术案例,蔡子璇既从失焦中引申出相当复杂的运动影像与时间影像问题,同时发现了隐含在摄影图像之中内在性的情感张力与迷狂体验。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瓦尔堡迷恋摄影的原因,解释了摄影缘何在艺术史、技术史与图像理论之中如此重要。
进一步地,瓦尔堡的业余摄影也提醒我们:自摄影术诞生以来,摄影便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中促进了绘画对于图像的剥离,由外部推动了艺术之再现模式的解体;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图像理论与艺术史的书写。具体而言,便是瓦尔堡用他自己即时抓拍的快照,所展布的(在迪迪-于贝尔曼看来)“错时的艺术史”对于传统研究与历史叙事的打破,包括对于现代文明与工具理性的反思,更不用说那些展示在瓦尔堡未竟图集中的摄影照片,以及图集的“记忆女神”之名本身所潜藏的能量的痕迹与记忆的灼痛。
非人的图像
在迪迪-于贝尔曼那里,飘荡在瓦尔堡《记忆女神图集》黑色图版之上的摄影照片,成了一种“遗存的图像”,它拥有自身的生命——即使是死后生命——它期待在每一个历史的时刻如幽灵般复活。它并不依赖艺术史家的归纳总结,亦不诉诸艺术家的理性思考与观看者的眼睛;也即,当绘画回到它的物质性时,图像也同样抛弃了载体、超越了视觉。我们发现,图像也可拥有身体与触觉,拥有情感和欲望,它可以成为历史之中新的行动主体,成为瓦解人类中心主义的“非人的图像”。
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影像艺术中,杨国柱为我们展现了这种非人的图像及其可能的动向。事实上,在电影里,我们似乎更容易接近一种非人的图像:在电影历史的开端,“持摄影机的人”已有可能被机器之眼所取代。在电影发展的现实,我们亦可想象一场无人的午夜影院中只有放映机孤独地闪烁;而在电影未来的愿景,则人们早已疯狂地构想如何穿越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图像”而发射出“宇宙电影”。在今天,Sora足以通过对技术影像的编织而自称导演,网络空间的鬼畜视频也可平替一场影像艺术的展览。我们在数码与算法的海洋里忘记了原创者的存在,而非人的影像仍能在“爱,死亡和机器人”的荒芜未来继续死后生命的遗存。
这样,无论绘画、摄影还是电影,无论艺术家对于图像的反对还是影像所承载的记忆和情感,无论图像是否能够在物质世界与精神领域中带来主客体的新一轮统一,“图像状态”最终都指向了围绕人之主体的问题思考,图像史与艺术史也在历史的主体处交汇。图像的非人状态虽然激进,虽然足够点燃我们的想象力,但正如在影响了于贝尔曼的德勒兹那里,感觉的逻辑与情动的力量,既是超越主体的非人存在,也在充满变化的运动中不断生成为新的主体。毋宁说,在图像之中的艺术所针对的是曾经启蒙与“我思”的主体,它以各种各样的连接线路冲破一切固定的关系与划分边界的企图,它以各种各样的运转方式呼唤一切运动的可能;它通过一种去主体化的运动重复着主体的塑造过程,通过自我的反射、批判与质疑来思考那些未被感知、未被思考之物。这样,在图像的理论与艺术的创作里,我们需要觉察其中的两种方向,两种围绕主体性的不同态度与图像状态:一种是图像的幽灵对于人之主体的全然扬弃,一种则在对于主体的反思中试探非人的生成;一种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拨乱反正中嘲讽主体的自大,一种则在人类纪与技术哲学中试图再度联结使用者与对象间的关联;一种在物的转向背景下表露出零度的冷漠,一种则仍然相信藏身于主体化运动之中情感的充盈与革命的力量。
我们看到,包括莫霍利-纳吉“绘画、摄影、电影”在内的历史先锋实验,以及今日“图像状态”所折射的新讨论、新议题,均落脚到图像与人的问题,落脚到作为创造者的主体,在不同的艺术实践的行动中所留下的身体痕迹。或如拉图尔所说,在今天这样的物的世界里,在容纳了绘画、艺术与图像的广阔领域中,既存在“准客体”也存在“准主体”。图像技术在无限增生的同时也在发明新的创作者与观看者,主体性在艺术的生成运动中不断遭遇消解并迎来新的建构,“主体”在此由名词变为动词,“人”再次成为尼采意义上的“桥梁”。或借用另一相当老套的说法,虽然图像占据了我们的世界和感官,艺术终究让人成为人——如特稿中诸位作者所言,即便这最后之人已是“非人”,其所显现的图像已是历史的“无脸者”。
注释:
[1] 汪民安:《绘画反对图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
[2] [法]米歇尔·福柯:《马奈的绘画》,谢强、马月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3] [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4] [德]格哈特·里希特的笔记,1984年。
[5] [德]鲍里斯·格洛伊斯:《艺术力》,杜可柯、胡新宇译,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
[6] [美]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介与再现》,文丹译,黄小峰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注:张晨,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孟 尧 蒋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