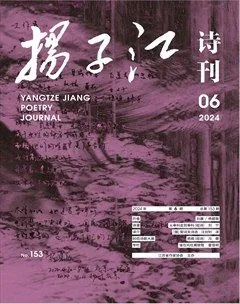扎赉诺尔预言
一首情感饱满的诗歌,是诗人对应许之地的心灵贴伏。正如阿尔贝·加缪在《没有历史的城市小引》一文中所言:“如果你是面对大海却依然热爱柴草的人,那么,在那边等待着您的,便是一团烈火。”所谓应许之地,通常不是一个人的故乡,它也不是一个泛化的存在,它具有预言的光泽——信仰即如地平线,你每向前一步,都是抵达。
我们夏天的呼伦贝尔环线行是从海拉尔出发,经额尔古纳、莫日格勒河、室韦,到满洲里的。这非一次精心设计的旅行,我们不愿囿于规划好的路线被导游掌控,在当地雇用两个熟悉草原的司机,就开始畅快地撒欢儿了。但我想,我们是在追寻着预言前行的,在某一时刻,我们会获得诗歌。果然,在途中,程永新写了《月光下的室韦》,我写了《室韦的鹰》。在结束草原旅行后不到百日,永新又写了《满洲里的太阳》:
霞光初现,悄悄爬上窗帘的晨曦
将短暂长夜的缝隙填满
凭窗远眺,霞光鲜红欲滴。如果在内心强化祖国这一温暖的概念,这里就是情感和地理的边疆了。永新诗歌面向语言之壁的楔入,绝对来源于他对自然世界和周边环境的观望和倾听,他的诗歌语言,在从容舒缓的表象下,有苍云翻卷、大地回声、神思逶迤,湖沉月光星子,鹰飞天堂圣境。他是那种一再沉淀感觉的人,我在上面所议的,是说他在写作时对待一首诗歌的态度,在“观望和倾听”之后,他不是有意延宕,他的思考会在一首诗歌的旅途上多次往返,直到被核心灵感准确击中。
如果你去过八月的满洲里,恰逢晴日,你在楼房的窗前看见突然喷射出来的霞光,你的灵魂就会被深深震撼。的确,就一个瞬间,“悄悄爬上窗帘的晨曦”,就会“将短暂长夜的缝隙填满”。我们活在无所不在的神启中,在“长夜的缝隙”里,我们或安睡,或秉烛夜游,或促膝深谈。当黎明到来,光芒填满交错的沟壑,我们离开“缝隙”,即使那时入睡,我们也会在相对的高处,那里有晨曦。
永新的诗歌,从他依稀听到某种声音,看到某种画面开始,到他动手写作,到他一改再改,像一个少年双手握住魔方,一直到他看到最满意的组合;这个过程,“声音”和“画面”始终都在他的脑际。我们评价一首诗歌的优劣,除了诗人的语言,还要透过语言,看这个诗人是否心怀诚挚。
永新的诗歌,是被他用心剔除了锋芒的,那些画面多姿的、被他一再斟酌的诗歌语言,让嗜酒的我想到经年纯酿,品了养眼养心。在极个别情况下,比如我们和其他朋友同行一地,我会像征询兄长意见那样,希望他能再写一首诗歌。这首《满洲里的太阳》就是这样,我记得,这个约定是在滨海小城霞浦完成的。
赤裸的镜面映射伊甸园的幻象
大片绛红色的圆屋顶碎银点点
上面引出的两行诗歌,也是对我们一同亲历的景象的刻画,是诗歌对时间和自然亲切的回望。至少,永新写作这首诗歌时所依托的,是我熟悉的故乡草原;在往昔,那里是我的祖先用心与爱守护的营地。在辽阔的呼伦贝尔,你目光所及,都可形容为“赤裸的镜面”,当你面对草原大湖的时候,此种感觉尤为强烈。不仅如此,行走草原,无论你面朝哪个方向,你真的都会看见“赤裸的镜面映射伊甸园的幻象”,这种幻想非常真实,若你在其中,你就会理解一个诗人为什么这样歌唱。
永新诗歌的跳跃性,比如从上一行到“大片绛红色的圆屋顶碎银点点”,他的感官体验也就从草原回到边城了。满洲里颇具俄罗斯风情的建筑,那些风格独特的圆屋顶,在八月之晨的霞光里闪着银光。阅读至此,在皖中合肥,我的思绪瞬间就飞回了八月的满洲里——我们草原之行的分别之地。一首优美的诗歌为何令我们感动?我的回答是,它能让我们在新的时间、新的环境中,对往日里美好的事物心存珍重。再看永新的诗歌,就如往昔重现:
松鼠穿越的光河在飞檐间流窜
一夜无眠的北湖激情澎湃毫无倦色
满洲里的太阳啊你为何姗姗来迟
如同神启如同久远的呼喊
在我记忆的天幕下,流淌着额尔古纳河,我们走在林间,顺着台阶去看湿地,精灵般的松鼠会不时出现在路边,有的在树上,它移动的速度很快,在它小小的眼睛里,有纯粹的光。永新的形容,他诗中的那条“光河”曾经见证我们到来,我们在奇幻彩云的舞动中离去。
从“松鼠穿越的光河”到达“北湖”,是又一天了,我们和自然都无倦意。就要告别呼伦贝尔了!永新对满洲里太阳的问询,在凝望里回到内心,他也在问自己,山河仁慈,我们能将什么留下或带走?
还有“神启”和“久远的呼喊”,这是领悟后的声音在诗歌中回传。在我的记忆里,满洲里的那个早晨,除了神一样的太阳,就是可以感知的高原天籁了,那是天空里的声音,会送我们很远很远,有朝一日,它会把我们接回呼伦贝尔草原。
人有三种无法抗拒的旅途,第一是物理意义上的旅途,那可能是许多重叠交叉的道路,无论哪一条路都会伸向前方,前方还有前方;第二是心理意义上的旅途,每个人都会心怀理想之地,向往越久,神思越近,就连梦境里都会出现圣山、草原、河流;第三是生理意义上的旅途,一个本来活生生的人走了,生者为逝者送行,前者悲戚,后者永远消失在现实世界,去了往生净土。诗歌就不一样了,一个诗人,即便是在描述亡失,诗歌中的怀念也不失美丽。活着,相见与告别就很美丽,这种感觉,在永新的诗歌里,变为诗意的品味:
相见恨晚呀相见恨苦
每一次相聚都像是告别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只有爱,才是至高无上的永恒。”爱,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它的正面和纵深所展现的无尽,是视觉里的信仰。在诗歌语言构建的空间中,安居着人。这就具体了,第一缕诗歌光辉的指向,一定是醒着的梦乡。
被永新在意识中选定的叙述对象,那个“相见恨晚”“相见恨苦”的对象,可以是一片天地、一栋建筑、一个国度、一群人、一个人、一个季节、一个火热真实的年代……我们说,一行诗歌就可以点亮整片夜空,好的诗歌是预言,也就是神谕,通过诗人给了人与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爱的阐释,集合了他对世间深重苦难的认知。我的这些突发的联想,是被永新两行诗歌调动起来的、对一位伟大先哲的怀念。这就是诗歌的魅力所在,流淌在诗歌里的爱,让我想到陀翁先哲的另一句话:“爱,是最高道德。”
衍生于爱之天宇下的一切,其中与人类须臾不离不弃的,无不依附遵从于这最高道德。永新的诗歌“每一次相聚都像是告别”,是在与自然和人挥别后,以心灵回归的形态再一次穿越,心灵跟随着诗歌,诗歌引领着心灵,在再生之地,至少会有两行诗歌相遇,发出金子般的声音。
相遇于旧地,相拥于诗歌之光辉映下的、持续的怀想中,相对于高原或海滨之夜,相思于寂静或沸腾深处,相知于彤云的启示,相距于目光之河,相认于经年,相连于山脉一样起伏的岁月,相劝于必然分离的苦楚,相动于牧歌唤醒的夏天。不止这一首《满洲里的太阳》,我在永新诗歌中发现的,是在他儒雅的、绅士一样的言行和笑容里,存在一个蓬勃的夏季,它始终停留在固定的时区:那里河流清澈,月光如银,太阳火红,新朋老友情深。
永新的诗歌写作,一如他职业化的阅读和取舍,显得游刃有余,从容舒缓。一个诗人的诗歌,无不体现出这个诗人的个性。作为誉满文坛的编辑家,永新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投身于文字海洋,他能够敏锐地感觉到美丽岛屿的所在。这是他的优势,在进入诗歌写作状态之后,这样的优势也给他增加了某种难度,他对诗歌语言的精雕细琢,他对诗歌结构的要求,他对诗歌从起始之句到结尾之句的一再斟酌,已经接近于对一块玉石的精雕细刻;另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他的诗歌写作就如造船,被他最为看重的,是船体的取材、结构的设计、水手的选择、桅杆的高度、船帆的展翼,最后才是离港远航的时间。
这需要等待。在某一个时刻,我们在永新诗歌《满洲里的太阳》的航程中听到了这样的心声:
欢愉被柔情融化呻吟被心跳掩埋
迷醉总是与时间相对论错位
这个航程是心灵之旅对现实之地的重返,诗歌坐标永远也不会出现偏差和位移。诗人的另一种态度是,要竭尽所能,让感觉的波涛重现优美的曲线,那种起伏被源流推动,人在其间,或在形而上的“岸边”,会屏息谛听,那仿佛是从远方到来的、神赐的“欢愉”,紧紧贴伏在时间的肌体上,那是最美的飞翔,你永远也不能看见它的翅羽。
诗歌行到这里,永新的凝视点已经脱离满洲里和那个早晨。当具象的描述隐去,诗歌语言回到内心,诗人所言的“柔情”徐徐上升,俯瞰入夜后万家灯火,在每一扇光明流泻的窗内,都是人间生活。
我们融化在这样的意境中,清风如絮语,如天地呻吟。你要承认,在时间的连接处,总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护佑着我们,我们敏感的心,情愿被它的氤氲无声“掩埋”。读永新的诗歌,在他的诗歌语言的虚实之间,我无需辨识,我清楚他诗歌里的路径,在通达之地一定有音乐之声。他是一个动情极深的人,他写诗的手法时而白描,时而幻化,进退有序,留白之处有足音。
那里,是被永新用诗歌语言含蓄所指的令人“迷醉”的境地。川端康成在他的《雪国》里有过诗意的描述:
……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象,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世界。
关于时间,我们感觉短暂的,抑或是相对漫长的,被我们无意虚度的,或惜时如金的,它都保持无形和公正。如果不通过水的波纹和时节色彩的变化,我们就无法想象它的纹理。时间,它究竟有没有故乡?它有无归宿?这需要诗意的解答。诗歌中成长的信仰是,有一种巨大的荣誉存在于未知领域,它真的在那里了,我们常常迷醉于远行,就是渴望解开“时间相对论错位”出现的诱因。而信仰,始终都是我们寻求的支撑,它的存在不容置疑。
一首诗歌就是一个宇宙。诗人不是创造了这个宇宙的人,诗人是敬奉者,他们进入,他们以神的口吻对这个宇宙之外的人们,传递出净水一样的声音。这样的诗人,懂得精心打磨语言,用一个一个意象铺就通向高处的诗歌之途。我阅读《满洲里的太阳》,心中幻化的就是那个宇宙。
我常常在诗歌里紧随一个独行踽踽的人,我知道他不会回头,他不会对我说话;我还知道,我穷尽一生也不能走在他的前头,他也不会消失。我有一种错觉,我们根本就不在一个平行线上,永新诗歌中的“时间相对论错位”,在一个宏大的背景里,或许就是宿命。
面对浩渺,你在夜里冥想,在生命之中,最容易被我们感知的,那个宏大的背景是什么?那是人的心灵。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你再想,闭目而思,一生里最令我们迷醉的是什么?那是人与人心灵的相融——一瞬可知山河万里,一刻抵万金,感慨万端,美不胜收。如果身临其境,身心所获值得用未来珍视,是可以问询山河的,请看永新的诗:
命数可不可以置换可不可以重来
传说中的猛犸飞驰在细雨中
有一个预言是,你要服从自己的视线,对遥远保持心灵的供奉。你为此默念的、祝祷的、恳求的、许愿的,无不历经焚烧。活着,就是与火焰相伴的过程,我们因此而认识了寒冷。诗歌的呈现有多种形态,比如燃烧、奔流、起舞、逶迤、平阔。不要将诗歌理解为交流的工具,不是的,诗歌是一个活体,它无形,它看似飘渺,事实是,在你内心深处翻涌的、诸多难以表达的心绪,和你曾经拥有的很多理想一样,都是诗歌。
永新的诗歌是对一条幸福之路的回馈,他在诗歌中的设问,说明他对某一种生命状态的思考已经成熟。他不说结论,他将答案揉入诗里,在那样一个独特的空间里,他与自然交谈,那条漫长的道路,静卧在诗歌中。
可以这样说,从童年开始,我们就对自然与事物产生了不同的设问——仰望星空,我们问无尽;倾听大河,我们问流程;置身寒冷,我们问西风;感觉神秘,我们问流萤。设问,这种极为寻常的修辞手法,其本身就充满了磁性,我们为何会不停地设问?“命数可不可以置换可不可以重来”?永新的设问,背倚他的半生路,他不是不相信各种体验,他如此表达,首先顺应了诗意,然后,他以这种方式将我们带入了哲学之境。在这里,你可以回答,也可以沉默,但诗歌空间已经展现。
一首诗歌有一首诗歌的命运,我们阅读,从中也会发现自己的命运。那么,“命数可不可以置换可不可以重来”,面对诗歌的设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如果诗歌的设问能够把你引入圣境,一切也就释然了。随之,我们在永新的诗歌中就看到了“传说中的猛犸飞驰在细雨中”。此为高妙的导入,也称之为诗歌的跳跃,传说、猛犸、飞驰、细雨……这些意象也在自然界成长,它们绝非固化的,如水泥高墙那样的存在,这些意象的生动性,已经完美解答了诗歌中的设问。反复读永新的《满洲里的太阳》,使我想起荷尔德林的《秋天》:
大自然的闪光是更高处的显像,
那时日以诸多的欢乐终结的地方,
是这样的年岁,辉煌圆满,
那果实融入高光的地方。
我引出荷尔德林《秋天》一诗中的四行,与永新的《满洲里的太阳》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八月,我们曾经融入的呼伦贝尔,如今进入了苍茫的雪季,那是另一种美丽意境了。读诗,我们即刻就能回到八月——八月的海拉尔、额尔古纳、莫日格勒河、室韦、满洲里。此刻,我依然能够感觉到满洲里八月之晨的太阳,迷醉仍在,那种鲜红与温暖,就如我们的记忆,在永新的诗歌中伸展:
额尔古纳河长袖善舞
弯弯曲曲的绸带飘向大草原
写作诗歌并非永新的主业,若排序,他是编辑家、小说家、诗人。他在使用语言(指写作诗歌)时,特别注重色彩与声音,色彩是画面,声音是旋律。他编辑过一些杰出作家的很多小说,他对语言的敏锐觉察,已经近乎本能——这是由视觉、听觉、嗅觉结合而成的功力,是长时间的累积和修为。是被他精准把握的语言,在一个必然的过程中进入了他的诗歌,而非他的诗歌限定了语言。
“传说中的猛犸飞驰在细雨中”,这行诗歌里至少有三个画面:猛犸、飞驰、细雨,三个画面在传说中,人的命数在前定中,诗人的怀想在旅程中——在接下来更美的画面里,“额尔古纳河长袖善舞/弯弯曲曲的绸带飘向大草原”。这两行诗歌中有六个画面,和谐有序,组合精密,浑然天成。
我的这种想象来源于永新诗歌的启示,我意在表达,人在不同的环境里,心中都会装着圣地。诞生诗歌的所在,就是诗人的圣地。
我们的旅途在陆地上,在我们心心念念的地方,有我们的栖息地。总有这样的联想,我们到来,是在寻找一个遥远的心愿,这个心愿曾经出现在梦里,我们在熟睡后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推动起来,在陌生的地域中学会了飞翔。
永新进入诗歌的方式极为独特,从切入画面开始,到自然界色彩的飞升弥漫,寥寥数行即营造出一个美丽的诗歌空间。他对陌生之地是敏感的,可他不动声色,始终保持沉稳和平和;观察自然与事物就是阅读,每个人获取的信息都有差异性。永新的诗歌,通常是在他告别某地一段时间后才会写就。他仿佛是在践行诺言,他以诗为札,娓娓道来,面对远方倾情叙述。
以满洲里为核心意象,永新在诗歌中回味旅程。在呼伦贝尔,我们又一次行走了一个圆,这就是顺应天意和预言吧?当额尔古纳河出现在永新诗歌《满洲里的太阳》中的时候,河面在阳光下闪着光芒,我们望着它流向天边,那“弯弯曲曲的绸带飘向大草原”,看“长袖善舞”,我们的旅途缓慢消失在天光纵深处;阅读下去,更多的画面叠加而来,层次分明。在那个大背景下,长风送来呼麦的声音,一个从不惧怕孤寂的高原歌者沿河牧羊,他守着悠久的习俗和亲人……在这种回首中,永新的诗歌过渡到歌声之谷,情深一往:
我的爱因此像汹涌的波涛
沿途所至水草丰沛牛羊成群
在一首诗歌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往昔,也可以看到未来。活在诗歌中的我们,不会老去。永新在诗歌里倾注的激情是澎湃的,赞美自然,他不惜言。诗歌,是一个诗人心中最清澈的、永生不竭的蓝湖。关于投身自6d56a0e75f8cd156e6b1c955c7ffe961然之怀,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是这样说的:
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
扎赉诺尔是呼伦贝尔市下辖的一个区,这个地名的由来即与湖相关。在蒙古语中,呼伦湖叫达赉诺尔,意为像海洋一样的湖。扎赉诺尔与满洲里同在呼伦贝尔西北部,就如一对孪生姐妹。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家乡的很多地名都如传奇一样迷人,并让我如痴神往,比如海拉尔、满洲里、牙克石、达赉诺尔、室韦、额尔古纳,我曾感觉,这些地方有神,哪里都有众神的居所。
永新诗歌中阳光一样的语言,发自他的肺腑。因为我们一路同行,我确信,当他在上海写作《满洲里的太阳》这首诗歌时,他的心贴着远东大地。留在诗歌中的记忆最为可信,那是被重现的、经过提炼的、真实入境的、萦绕于心的归属,但不是别辞。诚挚的诗人都会铭记,写作诗歌是与神会意,忌用妄语。永新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激发出我的诸多联想,根本的原因是,他的诗歌忠实于他涉足的美丽山河,反过来讲,他也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的爱因此像汹涌的波涛/沿途所至水草丰沛牛羊成群”,在永新的倾述里,蒙古高原东南部草原,由贡格尔起,经过巴林、科尔沁、乌兰毛都,到呼伦贝尔,这是蒙古高原史诗中最多姿多彩的章节。从克什克腾到室韦,自驾距离接近一千七百公里,你完全可以想象这片大地的辽阔。在三十多年时间里,我们从西向东,直到室韦,这期间的旅程诗意满满,天赐相随。
被永新在诗歌中浓缩的,就是这片大地上最真实迷人的景观,这个地域遍布河流湖泊高山草原,整片大地宛若一块翡翠。或许,这才是旅途的意义,诗歌诞生,象征着圆满。我的兄弟姐妹们,永新的诗歌,的确写出了我们的心声:
“多想从此做个骑手一路歌唱
灵魂在歌声中片片飞翔”
作者单位:现代诗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