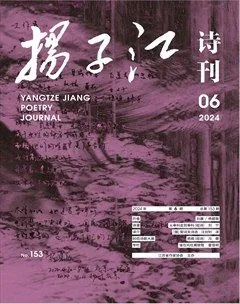非典型“中青年写作”:文学共性与诗歌文本的探索掘进
问题1 目前,围绕着诗歌写作,有不少热门话题,如新诗破圈、人工智能等。反倒是“中年写作”“青年写作”这两个概念,似乎没那么喧闹,却一直存在于新诗内部。与热门话题相比,这两个概念其实更直接地指向新诗本体。那么,你如何理解中年写作与青年写作?
刘康:首先说句题外话,按世卫组织(WHO)的年龄划分标准,青年的年龄区间是18—44岁,中年的年龄区间是45—59岁,“青年”的区间略长于“中年”。这是世卫的划分标准,不能代表中国(不同国家的年龄结构也不尽相同),更不能代表庞杂的写作群体。为什么要引申这个“标准”?我想,“青年写作”和“中年写作”,与之相关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代际”。
“写作代际”不完全依年龄划分,从心理、经验、感知,到对未来写作的预判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青年写作”和“中年写作”这两个标签,在无形中将青年和中年的“写作代际”进一步明朗化、清晰化。这并没有什么问题,回避或尚未意识到写作也有“代际”这一概念的作家们,并不代表他们就能抹除或绕过这条横亘在写作道路上的“界线”。“青年写作”这一话题近年来被广泛提及,当它作为一个专题出现在文学杂志,是否就意味着其标签化或概念化得到了广泛认可?以《扬子江文学评论》为例,2023年第1期头条推出“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专题,李敬泽、何平、杨庆祥等评论家围绕青年写作相关问题展开了圆桌式讨论,从“写作屏障”“写作症候”“自身转变”等多角度分析,其中不乏关于“青年——中年过渡期”的思考,值得青年写作群体一阅。而“中年写作”概KUHqBxbk52z9OhrIdfHrzw==念的提出为时更早,引张光昕教授《蛇的腰身有多长?——中年写作新探》(《文艺争鸣》2023年第10期)中的观点,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萧开愚一篇文章引出中年时期写作困境,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年写作”的探究和思考。可见,青年和中年两个时段的写作境况及变化早已被我们的前辈放置到了当下的文学现场。
从青年走向中年,除了年龄、心理层次的变化,我们对时间、环境的共处和各自面对,都对个体的写作带来极大不确定性,我将之归结为作家的“自证”“异他”与“时代经验”的冲突与融合。“一个时代不是一小撮杰出人物,也不是单纯的一批大众,它代表的是社会主体的一种新的整合形式,是群体与个体之间的一种动态折中。”(奥特加·伊·加塞特《我们时代的主题》)这段属于哲学、历史学范畴的概论同样适用于文学写作,同样适用于“青年”与“中年”的写作境况。当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自我与自我之间发生嬗变或冲突之时,时代经验的调和作用就潜移默化地生发在字里行间。因此,按“青年”与“中年”的标签将写作进行概念性划分确有必要。青年的莽突、创造、奇崛与“破圈式”审美,中年的转折、矛盾、奔突与“回落式”写作,两种既关联又迥异的写作生态正悄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这是我所切身感受到的。
杨碧薇:在新诗写作中,这两个概念常被提及,但说实话,我之前并没有特别关注。我最近在《诗建设》发表了一篇文章《危机之下的声音诗学及历史想象力》,其实是去年的旧文,谈的是高春林的长诗《苏轼记》。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高春林现阶段的写作就属于典型的“中年写作”。
我对“青年写作”的理解,首先来自于“中年写作”。说到中年写作,就不得不提上世纪90年代。那一时期,萧开愚、欧阳江河等诗人提出了中年写作的概念。现在,这一概念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不仅诗歌,小说等其他文体也在用。在(当前的)一般语境下,所谓中年写作,似乎表征着成熟,至少是走向成熟,正如郁葱在《磬声钟声:河北诗歌的中年写作》里说:“经历丰富,心智趋于成熟,对世界的认知和判断趋于理性,艺术上有了相对丰厚的积淀。”
然而,如果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会清晰地看到,中年写作的提出,首先包含着一种历史意识。虽然时间的流淌是线性的,中间是自然承接,延续不断,但上世纪90年代确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既与80年代不同,又与21世纪初的00年代不同。尤其是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从上世纪80年代走向90年代的过程,是存在着某种“断裂”的。这一“断裂”,使上世纪90年代显现出了与80年代截然不同的特征;似乎时间的“线性”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悬置”。西渡很早便观察到了这一点,并说:“这种迅速增长的历史意识,使90年代的诗歌写作产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历史意识与90年代诗歌写作》)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解放个性的时代,年轻一代的诗人们能在诗歌园地中充分发展、发扬自己的个性,那么,到了90年代,随着中年写作的提出,对个性的强调又重新让位于对共性的呼求。这个共性并非指人们在性格上的相同之处,而是指向对历史/经验的感知/总结/判断,指向对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尽管这个“命运共同体”里也混杂着诸多想象成分——在“断裂”的事实上,一代人更容易从个性纷争中走出来,认领某种共同身份,并感受到共同的危机。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年写作的提倡者和参与者,正好从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期走向中年。个体的年龄危机、境遇危机、写作危机,都成了中年写作的催化剂。所以,中年写作又是包含着危机意识的。
综上所述,上世纪90年代的中年写作,首先具有历史意识与危机意识的双螺旋结构,其次还有知识分子写作的特征。后者不是我现在要讲的重点,因为青年人也可以是知识分子,而青年写作未必包含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意识与危机意识。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二者的不同。
问题2 刘康刚才说,“两种既关联又迥异的写作生态正悄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杨碧薇亦认为,回到特定的历史现场,能更清晰地辨识出青年写作与中年写作的不同。在二位看来,这两个概念首先是有区别的。那么,二者是否又存在相似性呢?
刘康:“青年”的标签化、符号化为时更早且有据可循,其实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伊始,“新青年”这个概念就已被提出,不说《新青年》杂志,单说概念,其时涵盖的不单单是文艺、文化,它有更高层面(家国理想)的指向,这也与上一个问题中提到的“时代经验”相关。而“中年”的概念更为普遍化,如果不与写作挂钩,它甚至可能就是一个人外在形态、内在心态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但又无法准确说出“中年”的界定标准,似乎在不知不觉甚至后知后觉中,“中年”就降临到了我们身上。
回到写作范畴,“青年写作”与“中年写作”的区别除了上文提到的几点个人感受,我想更多的还是应该放置到大文学环境及社会学的框架中。一个是因背景异化和圈层变化而产生的“错置感”,从青年到中年,绝大部分作家会经历人生的几个重要阶段,包括但不限于婚姻、谋生等必由之路,纯文学领域的“青年式”写作,也与其个人的生活背景、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等息息相关,多样化的职业及教育背景,让青年作家在打开局面之后拥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广阔的平台和驰骋的想象力,这些优势归集起来可以概括为“创造力”。这种“创造力”随着原有的“优势”背景及圈层变化也在悄然生变,或因生活原因、个人经历等,创造力的“侵略性”在逐渐内敛,这也导致了中青年写作中“错置感”愈加增强。第二个是因天赋乏力和无效经验而产生的“挫败感”,我们不得不承认“天赋”的存在,当然,后天的写作训练和“有效经验”也能进行一定的补充,但青年作家的“高开低走”也并不少见。从青年到中年的跨度里,因才华的“磨损”和未能形成有效的写作训练(经验)而泯然众人的作家比比皆是,这种“挫败感”甚至“无力感”轻易就能击溃一个作家的写作信心。因此,我们在区分“青年写作”和“中年写作”两个概念的同时,也要审慎对之,以足够的警惕心理及时修正自身的写作。
杨碧薇:刘康对“青年”概念的补充很有必要。确实,回到新文学发生的场域中去看,“青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普遍关心青年的成长,鲁迅先生曾有名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今天,我们谈“青年写作”,往往是将上世纪90年代或当前语境下的“中年写作”作为参照系,实际上,“青年”话题与现代中国有更深的渊源。再往前一些,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算是呼唤“青年(少年)”的先声,写下这篇文章时,梁启超正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时年27岁。在现代中国,“青年”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常常看到以“青年”为名的各种杂志,却不见有哪本杂志叫《中年文学》《中年研究》等。许多杂志还会开设青年专栏、设立青年奖项、开展青年活动,为青年写作者提供更充分的平台保障。这些机会,都是明显向年轻人倾斜的,但正如刘康所言,在文学领域,从青年到中年的过程中,高开低走、江郎才尽的例子比比皆是。毕竟文学的终极评价标准就是文学性,写到最后,靠的还是作品质量,不会因为年龄优势、身份地位就给你大开方便之门。
在上一个回答中,我已简要谈了二者的不同,其实也只是选了一个角度,即回到“中年写作”概念提出的历史现场去辨析。至于二者是否存在相似性,那也是肯定的,只要是在诗歌写作的范畴里,就必定会包含一些人类的共性,以及情感上的、判断上的相似性。
另外,我觉得,在这里空讲概念,其实没什么意义。如果我们严格地界定中年写作与青年写作的概念,在固定的框架、范围内去写作,那么,无异于能指空转,为写作戴上不必要的镣铐。写作者最重要的是写,是自由创造,而不是空谈,不是自我设限。当然,厘清一些概念、知识,深入了解其来龙去脉,掌握其背景与前景,对写作来说是有益的,只要别被概念绑架、陷入里面出不来就行。
问题3 是的,空讲概念不如举例。你们能否举出一两个例子,如具体的诗人、具体的作品,来进一步阐明对这两个概念的看法?
刘康:碧薇在引申“中年写作”概念时提到了欧阳江河,如果要谈论写作的“青年性”“中年性”甚至“晚年性”话题,的确在上世纪90年代由欧阳江河等人提倡过“中年写作”,甚至欧阳江河曾一度提及萨义德的“晚期风格”,这与诗人的个人思考、写作版图关系非常密切。考虑到此次对谈的主题及例举的多样性,我想撷取一位外国诗人不同时期的写作特点谈一些看法,当然,一切源自我个人的阅读偏好和熟悉程度。
例举谢默斯·希尼,原因有三,其一是他所经历的时代背景与我们重合度较低,其二是他个人的境遇充满传奇性及历史性,其三希尼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杰出的诗学专家。这里有一点要说明下,国外诗人群体中很少谈及“青年”“中年”写作的概念,他们甚至可以一度认为永远保持着青年写作的态势。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不同阶段写作变化的观察和分析。希尼的写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72年以前,1972年—1991年,1991年后。这样的分段或许并不准确,但对青年、中年写作的变化仍可窥一二。1972年前,也就是青年时期的希尼陆续出版了《一个博物学家的死亡》(又名《一位自然主义者之死》)《通向黑暗之门》等诗集,主体是对爱尔兰农耕生活的叙述和抒情,如“我总是感到想哭/一罐罐可爱的果实全都有腐味/实在不公平/每年我都希望它们能保鲜/明知它们不会”,这首《摘黑莓》(黄灿然译)选自《一位自然主义者之死》,明显带有青年写作的情绪特征,与诗人中后期作品的差异尤为明显。为什么要以1972年作为界定线?这一年,诗人因爱尔兰宗教动乱被迫迁居都柏林,并在同年出版了诗集《在外过冬》。“晨光中/薄荷被剪下被珍爱/我最后注意到的将会最先失去/然后让所有幸存之物获得自由”(《薄荷》,贾勤译)“与她面对的是一种教育/就像跨过一道结实的栅栏/横在两根刷白的支柱之间”(《视野》,贾勤译),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诗人心境及创作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诗人的个人境遇及写作自觉,即沉潜式、融入式的时代性写作。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希尼移居英国、美国,陆续出版了《全神贯注》《舌头的统辖》《写作的位置》《诗歌的纠正》等一系列诗论集,因篇幅原因,这里不再赘述,但对希尼中后期作品的阅读及深度理解有着较强辅助作用,包括诗人对“诗歌的作用”“诗歌与地缘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在我个人的阅读认知里,希尼算是一位“纯粹度”“完整性”都较高的诗人,从青年、中年再到晚年,数十年间用自身的写作反复印证诗歌的功用、构建诗歌的信心,并以自身为引树立起了世人对诗歌力量的信心。
杨碧薇:刘康引希尼为证,因为希尼的时代背景与我们重合度较低,其个人的境遇也充满传奇性及历史性,在我看来,这正好包含着我们在阅读上所期待的异质性。那我就说个中国诗人吧。我还是想到了穆旦。如果说在希尼身上我们感受到另一种语言的异质性,那么,穆旦则是在汉语内部创造了新的异质性,这一创造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在时间长河中,它经受住了从异质到正统的考验,最终构成今天的一个新诗小传统。
穆旦青年时期的诗歌,充溢着挡都挡不住的青春气,算是较为典型的青年写作。如果让我来甄选他三十岁之前较为重要的作品,至少会有《赞美》《诗八首》《森林之魅》《隐现》等。这些诗里有个体的探寻、爱情的烦恼,也有家国的忧思。提到家国忧思,穆旦这方面的诗还不少,在《赞美》《森林之魅》之外,《哀国难》《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中国在哪里》等,也都不可忽视。这一写作偏好固然与时代有关,但不应忽略的是诗人本身的敏锐性。因为,即使在内忧外患的时代,也未必是人人都关心国家、关心政治。而“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王佐良语)的穆旦,在诗歌写作上十分“非中国”(王佐良语)的穆旦,却在二十四岁时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参军。这其实是个很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的选择。九死一生的戎马生涯,对穆旦的人生遭际和诗歌创作来说都至关重要,尽管对此他并没有留下太多文字。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就不会有《隐现》,也未必会有他晚年的绝唱“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冥想》)。
在关注现实这一点上,穆旦青年时期的创作又大大地溢出了狭义的青年写作的边界,表现出积极的介入性与强烈的实践性。他的自我意识的成长、个体生命的觉醒,始终是在现实的挤压下,在家国忧思之中。十多年前,我二十岁出头就在阅读同代人的作品,现在,还会读一些年轻诗人的作品。这么多年来,整体的感觉基本不变:在青年的诗歌书写中,关于自我、个体的部分多,比如爱情,年轻人写爱情再正常不过了;而关于家国、现实、社会、历史的部分少——在一些青年诗人笔下,甚至从未出现过“我”之外的题材。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在评价校园青年诗人的作品时,常使用一个词汇——“学生腔”。我们对这样的规劝不会陌生——“要试着除去你作品里的学生腔”。其实,穆旦早期的诗歌,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颇“学生腔”的。但我似乎没听到谁用这个词来评价他早期的作品。我想,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对现实的关注与介入,这种行动力,放在今天的青年诗人里,也是少有的;原因之二,是因为他校园时期的创作,已经有清晰的语言意识,勇敢地追求新的、不一样的表达。语言上的探索,帮助他构建起不一样的诗歌面貌,这在很大程度上覆盖了他语气、语调里的学生腔、校园气。由此,人们对他早期诗歌的判断更多地是指向“前沿”“先锋”,而不是指向“学生腔”“学生气”“不成熟”。
穆旦晚年的一批诗歌,集中呈现出个体生命的厚度,是诗人创造力的最后爆发。除了刚才提到的《冥想》,还有《智慧之歌》《冬》《诗》《神的变形》等也都令人喟叹。1977年,穆旦去世,年仅59岁。他这批作品与其说是“中年写作”,倒不如说是“晚期风格”。对此,耿占春也说,“对穆旦来说,写作确已进入晚期。然而穆旦的晚期更像是一个重新写作的开端,就其诗歌所涉及的多重主题和多重灵感来说,穆旦的这一时期更像是诗人写作生涯的一个中期,如果不是翌年初到来的死亡打断了这一过程的话”(耿占春《穆旦的晚期风格》)。穆旦有过“中年写作”吗?他在去世前不久写的诗,除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一批,还有其他的吗?或许有,只不过没留下来,或者未公开。刘义曾与我分享巫宁坤的一篇文章《诗人穆旦的生与死》,文中就提到,穆旦还有一首叙事长诗《父与女》,至今未收入《穆旦诗全集》。说到底,对一位好诗人来说,并不需要“青年写作”“中年写作”这样的标签,因为他在写作上所抵达的已经远远超出了概念的限定。
问题4 无论是否被贴上标签,希尼和穆旦在不同时期的写作都有变化。从“青年”到“中年”是否意味着写作的进步?
刘康:写作的精进与年龄层级向来无必然关系,同样,不同作家的才华展露也会体现在不同时段。如果单纯以年龄、时间来划分或者评估写作水准是有失偏颇的。这里例举正反两个例证,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生平及历史背景不再赘述,45岁出版《罪与罚》即引起轰动,因写作起步较晚,我们将他的“45岁”划归青年范畴,但在14年后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才是真正奠定他在俄国甚至世界文学史上地位的著作。随着年龄及写作经验的增长,有些“成长型”作家会在长期的写作中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修正,这种修正是多年写作经验、人生经验的积累和嬗变,也是个体与群体、个人与时代磨合、分离的结果呈现。另一个要举的例证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一时代的小仲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小仲马极早就已展现出非凡的文学才华,除了广为人知的《茶花女》,他的其他作品的文学成就同样出类拔萃,至少在我青年时代的阅读中,小仲马的《私生子》远比其父的大部分作品深邃悠远。无一例外,小仲马的优秀作品几乎都生发于其青年时代,而中年境遇及生活经历让这种璀璨的才华过早消耗,或许表述并不准确,但客观事实就是如此。
对年龄圈层与写作技艺的进步与否的质疑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从青年到中年,是一个写作者以自身为蓝本,不断倾注经验、阅读和实践的惯性结果。而从浸入到提升,是一个思考者不断摒弃、剔除和剥离的艰难过程。文学创作让我们得以将所有的天马行空、不切实际都诉诸文字,让一切因敏感和多疑所产生的思考都注入文本,反过来说,是文学创作让这些想法拥有了成立的可能。回到诗歌,因文体、结构和体量所限,其所要求的语言能力、技巧处理、情感收放更为严苛,这种严苛体现在分行的承接、气息等方方面面,不论青年写作或是中年写作,进步与否的判断标准仍是一眼可辨。当然,每一位诗人都有独属自己的写作自觉,这种自觉即是对自身写作的预判机制,在不同诗人的写作经验里,时常会因为一个细微谬误而产生新的想法,直至画上句号,事实上,这些因谬误而生出的判断往往会印证于文本,这是每一个诗人都需面对的问题。
杨碧薇:在写作中,“进步”并不是一个线性的概念,我们肯定不能简单地来看待并判断“进步”。我必须再强调一下:从生理年龄上来划分青年写作和中年写作是最靠不住的。如刘康所言,有人起步早,可能在二十多岁时就写得颇为成熟;有人起步晚,可能四五十岁了还写得十分稚嫩。这种情况,如何来论证“进步”呢?再比如,有人认为“中年写作”一定比“青年写作”好,那穆旦写于24岁的《诗八首》展现的是典型的青年心境,整个的语调、语言状态也是年轻化的,你能说不好吗?还有兰波,年纪轻轻就走到创作巅峰,随后封笔。这种情况,你又如何归类、如何解释呢?
盲目地拿“青年”与“中年”对比,是不科学的,无可比性的。最有可比性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写作: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什么时候开始“悟”,从什么时候开始,较之前有明显突破……当我回头检视自己的写作时,能看清许多问题,同时亦能找到解决方法。对我而言,这种比较是有可行性的,也很有效的。
当然,我有时也会比较,前辈们在我这个年纪时在写什么、已经写出了什么。而我现在还能写什么、能怎么写。这样的比较,会凸显时间和历史的脉络,从而强化我的某种写作使命感,甚至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我常常想,我们这一代还能做什么。这样想时,难免会感到前路漫漫。但我也深知,我不能代表我这一代人,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很难形成共识的单子化时代,我首先能做的无非是顾好自己。
问题5 你们俩年纪差不多,不仅是同一届“青春诗会”的同学,还一起参加了首届国际“青春诗会”。在诗学趣味上,你们既有差异,也有诸多共同点。比如,你们都有文体自觉,写过异域题材,在语言上追求个人风格,阅读上则有“向外”的眼光。那么,你们认为自己目前的写作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更接近“青年”还是“中年”?下一步有何写作计划?
刘康:我的写作一直都是绵延式、掘进式的,拥有一定的写作自觉。换种方式表述可能更容易理解,因为工作原因,我的写作和阅读大部分都集中在夜晚甚至深夜,一天中属于自己的时间有限,因此,合理运用好这些时间尤为重要。于我个人而言,诗歌写作更注重写作气息的承接及其连贯性,也就是在既定的时间段内将这种连贯的写作保持下去,这是一种绵延。至于掘进,是基于多年自我训练后对自身写作的一个判断和期望,试图在变化中寻求突破,也期待在更深层次的思考中实现提升。
关于写作计划,我更偏向于直觉化的一面,诗歌写作不急于烙印标签,相反,“风格”“派别”的圈定可能会适得其反。一首诗的诞生存在着诸多可能,譬如林间漫步而偶有所得,又如悲欣交集后的瞬间释放,这些都不是用“一个标签”可以定论的。我始终觉得在不同年龄段的个体感知决定了写作大部分的走向,博尔赫斯在目盲后依旧能够准确地从书架上找出自己想要的书籍,这种精准,来源于对语言和文字的敏锐直觉,也得益于挣脱束缚后的自在自如。诗歌写作也同样如此,它源自于对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的捕捉和提取,当然也有灵光乍现的时候,但迸发式的写作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也就是阅读、思考、感知和持续的练习。下阶段,我想更多的还是要将精力倾注于阅读思考、对生活经验的提炼以及寻找置身于当下的在场感。
杨碧薇:我一直都在探索的状态中。我不满足于待在写作的舒适区,探索让我体验到无可替代的快乐。回望自己这些年的写作,我好像从来没有在某一种套路上停留过。这种状态,你定义它是青年也好,中年也好,都与我无关,我只关心书写、创造、持续追问写作的意义,我能做的无非是这么多。
至于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我暂时没有。今年春天,我萌生了写《十二个房间》的想法。我想通过这组诗来探讨当代城市女性的生存空间、精神世界、权利和身份等问题。在诗的布局上,我选择了母婴室、衣帽间、健身房等更为“当代”、与当下生活关联更密切的“房间”,有意识地避开了“厨房”等承载着某种性别刻板印象的“房间”。从四月到八月,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来写这组诗。现在刚写完,我想暂时停顿一下,待充好了电再继续。当然也很有可能,这篇对谈发表时,我又找到新的题材并已开始动笔了。